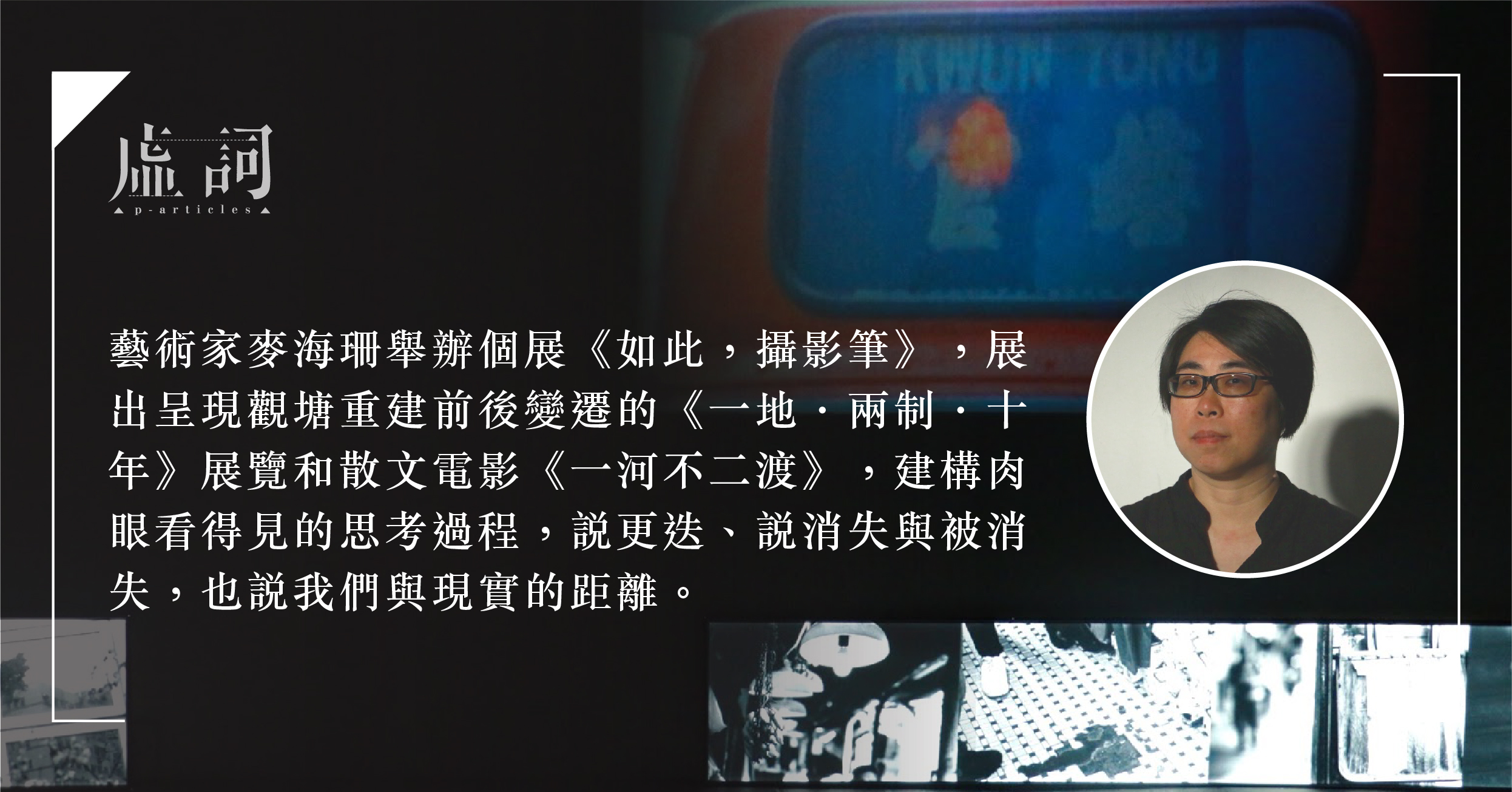【《如此,攝影筆》個展】專訪麥海珊──掌握消失,探出時間的關節
「今天和明天總是不一樣,這是當然——而我們能不能夠掌握每一刻的自己在幹甚麼、我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幹甚麼,這是箇中的意義。」
人無法踏進同一條河兩次,這是赫拉克利特的名言,卻並不是麥海珊僅想在《一河不二渡》裡說的話。事物固然每一秒都在變化,但麥認為「一般人不習慣看變化」,面對習慣的風景和人事,總是只見千里之堤,不見蟻穴,直至事物分崩離析的那一瞬間才恍然。因此她希望以「影像上的大消失」,來引導人們去思考生活中「微細的消失」。
藝術家麥海珊舉辦個展《如此,攝影筆》,展出呈現觀塘重建前後變遷的《一地.兩制.十年》展覽和散文電影《一河不二渡》,建構肉眼看得見的思考過程,說更迭、說消失與被消失,也說我們與現實的距離。
心是前設,紀錄是後話
《一地.兩制.十年》展覽場地被黑布包圍,影像在黑暗中顯得更為清晰,三組超八米厘電影(下稱超八)影像並置一側,上下好幾列黑白電影菲林照,與之相對的是三個獨立燈箱,分別展示三幅樹木盤根的黑白照。
超八裡的觀塘攝於2006至2009年,時值該區重建之初,鏡頭投以街頭休憩公園、巴士總站和巷仔,人們在紅A燈下促狹、轉過頭又在屋邨的粉牆前等車。片段間沒有過渡,沒有對話,如回憶般零碎而沉寂。
記錄時代是這一切的創作動機嗎?其實更多是疑惑,還有純粹的衝動。得悉重建計劃即將落實,麥海珊看著龐大的規劃圖,感到無法想像。「這麼大的地方,裡面又有那麼多的人與事,究竟會變成點?」在觀塘度過童年的她,在拍下這些片段的時候,已有二十年沒有真正重遊故地。麥當時並沒想過要將這些片段作何用途,只是在三年間不斷落區,和街坊聊天,跟一些上了年紀的婆婆談在工廠裡工作的情況。
「當然也有記錄成分,但如果你想要全面的紀錄,這些並不是。我的目的並不是要詳細地告訴別人觀塘從前是怎樣的。」麥毫不諱言,展覽裡的作品,不論是活動影像或是靜止影像,都僅是以她的個人角度出發。「我並不是要客觀的紀錄,而僅僅是拍下我喜歡的事物。」她舉例,「你就這樣看這幅照片,並不會知道整個公園是長怎樣的。因為一切都很主觀,是我面對變化的感覺。」作品裡,麥的存在感強烈,亦無意遠去,彷彿她的眼就是觀者的眼,彷彿我們只要看得夠細,就能有讀日記般的感受。
《一地.兩制.十年》展覽。版權屬麥海珊所有。
觀眾是透過她的眼來看觀塘;她就是觀眾和現實的距離。這種截取的現實、詩化的表達不但體現於拍攝手法,也體現於媒介的運用。麥選擇使用超八是因為喜歡其粗微粒、色彩濃烈的質感。「我們現在用的電子攝錄器材多數已達4K解像度,其實是很接近我們肉眼看到的,目的就是不要失真,有時候甚至比肉眼更厲害。」而使用超八這種和真實影像更有距離的媒介,則更能呈現「一個被記錄的現實」。
超八如是,黑白菲林照亦如是。麥在2016年再次回到觀塘,豈料已面目全非,以前的銀都戲院、寶聲戲院、仁愛圍、兩個小販市場全變成一個大窿,只得一塊平地、地盤,影像上非常震撼。她陸續回想起很多人和事,看著眼前的大窿,突然便覺得「不如影下相」。
夾超八而行的一連串照片皆以孖叉菲林Kodak Double-X (5222) 拍成。孖叉菲林本身是電影菲林,但也可以用來拍照。拍好以後,麥把照片重新拼湊起來,將它們重組成一卷放佛等待放映的電影菲林,又剪成《一河不二渡》的尾聲,以最快一秒七幀的速度轉放,只是一格格影像已不是連貫的動作或場面,而是不同角落所拼湊而成的急速世界。
影行如散文︰消失、來去與純真
察覺消失是認真生活的第一步,但這並不足夠,也要體會自己在當中的位置。當我們摸到時間的關節,捕捉到微小的消失時,須臾間,一切都變得如此清晰;我們又能否將自己從纏綿的時間裡分辨出來,認清自己在投入甚麼?
《一河不二渡》截圖。版權屬麥海珊所有。
《一河不二渡》分五章,穿梭於iPhone錄像裡的印度和超八香港之間——乾涸的尼連禪河、已不復見的洛奇廣告牌、恆河的沙丘、銀都戲院、觀塘小巷裡的騎牆舖,一切交織成麥對消失、與這個世界相處的多種想法和情緒。當中的超八電影片段雖有收音,卻不時突然消聲,令觀眾更聚焦影像,「而且好像突然間抽離現實,去想,其實我和這件事物的關係是怎樣?」
「我自己很喜歡做散文電影,個人情緒可以很詩化,但又不像概念藝術那樣含蓄。這是一種很隨意、很個人化的創作。」《一河不二渡》的片段式敘事為她提供了空間,以探討碎片式的感受,並構成一種整體的情緒。
例如是純真:恆河的沙島上,無風,但小孩還是奮力和風箏角力,從遠處不見風箏的線,看起來就像在和自行飛翔的風箏跳舞。「那是一個很簡單的遊戲,那種純真讓我很著迷,」也讓她想起以前在觀塘的感覺。又例如是去來:一個小機場的跑道上,一架飛機正徐徐移動。「那個機場每天只有一班飛機,而且都是在同一個時間起飛。當時我正要離開這個地方,但拍完以後再回看,卻不知道飛機是來還是走,所以才想到『一切顯像就是心』這句說話。」
若說「來去」,那就是香港近年的主旋律;電影的結尾也提及到近日《逃犯條例》的修訂。未來的無數香港人也許就是另一種「一河不二渡」的結局,有去無回。對於《逃犯條例》,麥海珊大嘆「真是好大鑊」,對從事各種創作行業的人士來說尤甚;應亮導演也可能要遠赴他鄉,林榮基亦無奈奔走,香港人將無一倖免。為此,麥亦經過一番內心掙扎。「我的伴侶在荷蘭,所以這兩年我是兩邊走,也有想過是不是應該去荷蘭。但其實我都唔願走,我想留下。」而離去或回來皆不是答案,只是心的顯現,「因為恐懼所以想走,但離開並不等於沒有了恐懼,回來也可能只有混亂的情緒。」
《一地.兩制.十年》展覽。版權屬麥海珊所有。
《一河不二渡》以2019年的黑白觀塘作結,巷尾踟躕的老人、被棚架捅破的天空、招牌、樹枝、梯口的圓凸鏡等一個緊接著一個地閃現,時而飛快,時而減緩,背景是仁愛圍後一家洋服店裡工作的老人在玩潮州音樂。一種不安感油然而生,令人想起Chris Marker同樣觸及過去與未來、以靜止影像組成的黑白電影《堤》,時空彷彿忽然扭曲,耳邊響起那經典的一句——「你根本無法將回憶從一般的時刻裡分辨出來。總得過一陣子,當它們的傷疤浮現時,那些時刻才會變成回憶。」(Nothing sorts out memories from ordinary moments. It is only later that they claim remembrance, when they show their scars.)
她一直在回應世界,溫而不慍地
對於《一河不二渡》所屬的創作類型,麥自己也顯得猶疑。多年以來她「乜都做」,讀電影出身,也做錄像藝術,也做《我們來自工廈》這類研究形項目,也做觀塘互動地圖的網絡項目(web-based project),也做聲音藝術,各種媒介糅合在一起,有時也難以為錄像藝術和電影畫上硬邊界。
雖然創作形式多樣,但將她一切創作貫穿起來的,似乎都是一股不得不做的衝勁,和對於這個地方純粹的由衷喜愛。這於她在樂隊Amk的創作中早有跡可尋。她和其他團員寫的歌,很多時都是衝著社會議題而來。「我成日覺得一個人怎可能離開政治,慘就慘在香港人在英殖管治下那種去政治化的心態已根深蒂固,人人揾食至上。但問題是,揾極食都冇得食呀嘛而家。」她哭笑不得地說,溫和卻不乏堅定。「我們這代人經歷過六四,所以會覺得政治怎麼會不關我事,很多事情,我們不得不回應。」
溫和卻不乏堅定——這是麥海珊予人的第一感覺,這種深沉亦反映於她的信仰。作為佛教徒,她卻不願多談佛學,始終認為自己仍是一個學資尚淺的修行者。但她的信仰自然和觀察世界的方式絲絲相扣,亦在她的藝術創作中處處隱約透露。「有很多人覺得佛教徒就是避世,而這個某程度上是事實——但重點在於,我們在作出評論時,目的到底為何?如果動機只是要謾罵,那這對社會和自己都沒有太大幫助。但如果係出發點是希望大家都能少一點痛苦,希望大家、希望香港人能平等地生活,那麼這就不同。」不過,她還是慎重作結,「但當然我們只是修行人,(信佛對我來說,)重點是調心。」
艾森斯坦曾言,電影的目的在於,要令藝術處理過的影像能夠在觀眾心目中喚起作者所希望引起的抽象觀念;而抽象和具體、政治和藝術,皆能同時存在。這就是《如此,攝影筆》的狀態,歷史確切,情緒莫名——但變幻絕非永恆,多時是,我們失去的才是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