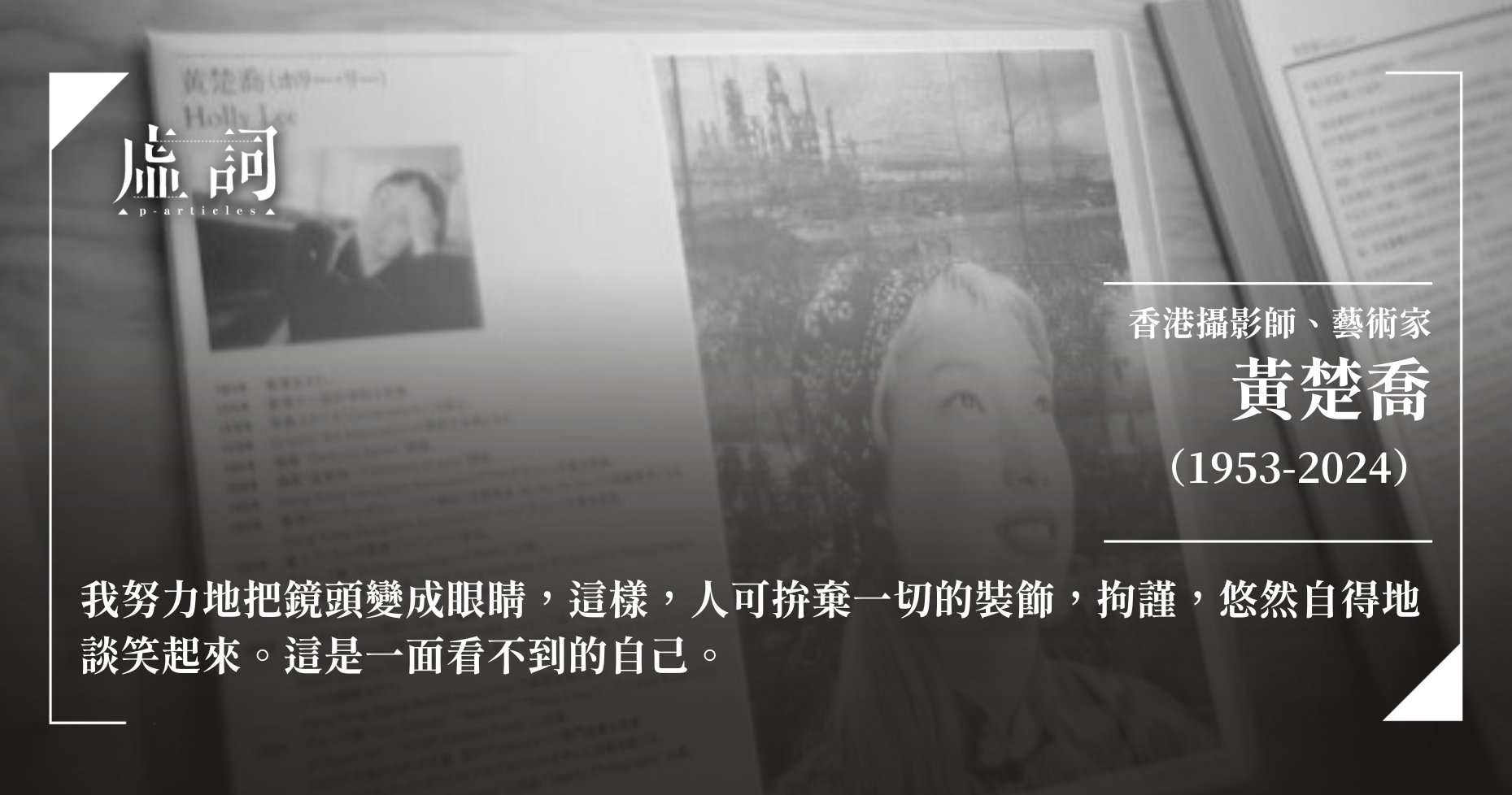香港國際詩歌之夜十五週年——母語的邊界 諾貝爾文學獎熱門詩人阿多尼斯與俄羅斯詩人奧爾嘉 · 謝達科娃作嘉賓 以叮叮車作詩歌節的移動藝術舞台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4-09-14
2024年將迎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十五週年,主題為「母語的邊界」。詩歌節於9月28日在中國會開幕,隨後在中環大館及多所高校舉辦系列活動,包括專題討論會、朗誦及音樂表演。活動匯聚來自全球的十七位詩人,如阿多尼斯、奧爾嘉·謝達科娃等,探討母語與世界語言的互動。特別出版物《母語的邊界》將於9月出版,集結詩人作品的中英譯本。香港電車將成為移動藝術舞台,觀眾可在城市中體驗詩歌的魅力。活動免費向公眾開放,詳情可參考官方網站。 (閱讀更多)
【附完整名單】台灣第48屆金鼎獎頒獎典禮圓滿結束 梁莉姿觸動落淚: 願所有人都能保有免於恐懼的創作自由 廖偉棠:希望詩能帶給孤獨求索的人一個擁抱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4-09-13
中華民國文化部主辦「第48屆金鼎獎頒獎典禮」於前日(11日)於南港展覽館舉行,當中榮獲文學圖書類獎共有4位得主,分別為楊莉敏的《濃霧特報》、馬尼尼為的《今生好好愛動物— 寶島收容所採訪錄》,以及香港作家廖偉棠的詩集《劫後書》和梁莉姿的小說《樹的憂鬱》;《雄獅美術》月刊的發行人李賢文則獲特別貢獻獎。 (閱讀更多)
《小丑:雙瘋》即將上映 回顧二十年來Joker面貌如何轉變
其他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4-09-12
《小丑:雙瘋》將於今年10月3日在香港上映,正好呼應前作《小丑 Joker》的五週年紀念。兩作皆由Joaquin Phoenix主演,第一作描繪了Joker的起源和心理掙扎,展現了他在社會壓迫下的墮落與變化。相對於Heath Ledger在《蝙蝠俠:夜神起義》中神秘且混亂的Joker,Phoenix的角色更具人性和背景,使觀眾能同理其痛苦與憤怒。續集《小丑:雙瘋》將探索Joker與小丑女Harley Quinn的關係,題目延續對邊緣人物的關懷,期待在複雜的人性層面上將為Joker帶來怎樣的探討。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