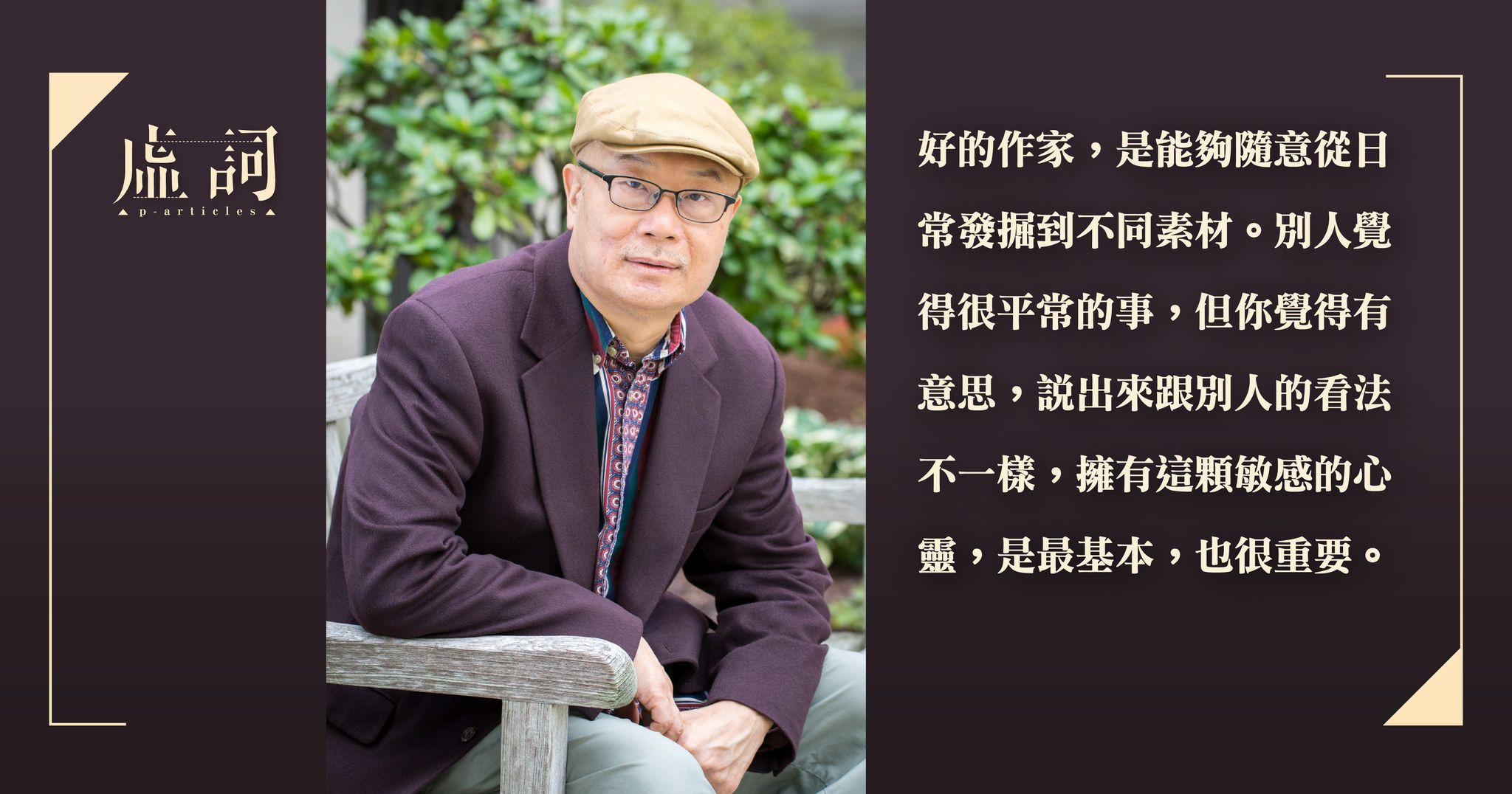訪作家哈金——以敏感的心靈,探尋邊緣寫作的意義
曾獲美國國家圖書獎、福克納獎、海明威獎等榮譽的美籍華裔作家哈金,月前應浸大文學院邀請,擔任「2021年度卓越華語作家」,舉行講座並與學生進行交流。趁著參與活動的空檔,哈金接受了「虛詞編輯部」的視像訪問,談及今年出版的華文散文集《湖台夜話》,也談自己對香港的持續關注。移居海外多年,帶著一顆敏感的心靈,以英語寫作筆耕多年,過程中不斷探尋寫作的意義。從一開始為了物質上的生存,到精神層面上得到滿足,哈金說,「繼續將有意義的事情做好,這是最重要的。」
「家是自己的,而家鄉則是祖先的」
原名金雪飛的哈金,自從1989年後再無踏足中國大陸,移居美國生活三十多年,都以英語寫作,並在當地大學教授文學。無論是因為其身分,抑或所寫的題材,外界對哈金的印象也是個「邊緣作家」。提及這種「邊緣」的屬性,哈金說自己創作的小說故事,角色設定很多時候也是邊緣人物,經常以海外華人男性作為主角,亦帶有自己移居外地的一些投射。「美國文化對亞裔女性比較容納,我認識一個韓裔作家,父親是德國人,寫過一個回憶錄《Memories of My Ghost Brother》,快將出版前,出版商逼他改成小說,理由是沒有人會讀亞裔男性的回憶錄,於是他改成了長篇(小說)。其實我也沒有特別想過,要為華人男性在美國的地位發聲,純粹自己比較了解這種人物的心態。」
是次受邀參與浸大文學院的活動,哈金亦以「邊緣寫作:兩個語言的穿梭與重構」為題,與香港學生進行交流。談及對香港的印象,哈金說2008年曾經來港,感覺這裡很乾淨、有秩序,以往亦曾有過來港任教的機會,但礙於家庭原因才擱置。對於香港近年的動盪,哈金說自己一直有留意事態發展,這次期待與香港學生隔空見面之餘,也對城內的現況多了一份痛心。「與浸大學生的交流,跟在美國的英語環境不同,在華語環境之下,談的問題與角度都不一樣,對我來說比較刺激,也很期待。這幾年(香港)的社會動盪,看到真正的人才都離開了,也很痛心。在我而言沒甚麼顧慮,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但不想給主辦方帶來麻煩,這是我的考慮,移民者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亦是我寫作的主題。」面對現實的社會環境,今時今日的香港,寫作與言論難免受到限制。問到哈金在這種環境下,香港寫作人該如何繼續書寫,他說「只能按照自己想法心願去寫,不能因為政治環境變,就改方向,否則一輩子就完了」。然而,在這個離散的年代,無可避免要面對人才流失,但留美多年的哈金卻認為,從文學的層面來看,對作者來說並不一定是損失。「對某些專業與行業來說,可能會是損失,但從文學來看,真正優秀的作家,能夠寫出甚麼東西來,都是一個過程,當那些人才流亡或移民之後,未來會否有大作家的出現,也很難講。」
三十多年來,直到哈金的雙親離世,其回鄉探親的要求一直被中國禁止。目前除了少量詩集,以及近年出版的《通天之路:李白傳》外,哈金的著作在國內多被下架,作品翻譯成華語亦屢次被禁,即使在台灣出版後慢慢反攻簡體字市場,但不同翻譯版本的差異,讓哈金覺得有些神髓,始終無法好好詮釋。「不管哪一本書,出版是出版了,但很多細節都被拿掉,就像寫文章沒有了牙齒,是不鋒利的。」今年出版的最新散文集《湖台夜話》,無須歷經翻譯的過程,哈金寫下對家園、文學以及小說的思索,更是他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裡,第一本全由華文書寫的結集,並以這段話歸納了全書的中心思想:「家是自己的,而家鄉則是祖先的。我們長大成人離開家鄉是為了在別處建立自己的家。」個人與國家的矛盾,從來都是哈金作品的重要命題,在他的其他不少著作,核心內容也是圍繞主角遷移他鄉後,重新開始生活的各種衝突。離開中國的出生地多年,三十多年來自我「流亡」,對於「家」與「家鄉」,哈金認為有必要將它們分得清楚。「家鄉是父母祖先所在的地方,並非個人的家,離開家鄉建立自己的家園,家人在哪就是家,是種精神的存在,正如文學也是我的家。」
「一定要用第一語言來寫作」
以英語寫作成名,在海外文壇闖出一片天,先後憑《好兵》、《光天化日》、《等待》、《戰廢品》,屢獲國際性的重要書獎。然而,哈金在二十一歲前,其實都沒跟說英語的人交流過,因此他在克服語言困難方面,自然下過不少苦功,長期以英文寫作,亦是他賴以生存的需要。「那時候不能上網,所以用了很笨的方法,就是買了很多聖經,讀過很多不同版本的聖經來學習英語。一開始以英文寫作,是物質上的生存需要,慢慢精神上的(生存需要)表現得更多更明顯。當我不斷地寫,知道得愈多,進入到藝術,參照系統變得愈來愈大,超越國家甚至超越語言,在這裡頭也找到自己的方向。」以外來作家的身分,開闢了相對成功的寫作道路,從當初是為了生存而必須懂得英語,到後來愈漸成熟掌握這種語言,哈金卻說自己從不追求標準的英語,這亦是外來者所獨有的英語貢獻。「這種不同的聲音與養分是需要的,純正英語誰都會寫,所以我故意把外來的成分收錄到英語當中,否則跟當地作者就沒有區別。當我聽著故事人物的對話,他們基本都在說漢語,這也是外來者寫作的好處。我寫《李白傳》時,內容是很直接了當的,慢慢我意識到根本不是英語好不好的問題,而是寫文學的話,文字上必須得有自己的風格。」
雖然哈金用英語寫作多年,但至今他仍視漢語為他的第一語言,給予寫作人的建議,亦強調「一定要用第一語言來寫作」。「第一語言跟母語是兩碼子的事,能以最熟悉的語景來表達,這是最重要的。當然,每個人情況不一樣,語言也是在變動的,例如香港的年輕人,如果將來到英國跟外國人結婚,英語慢慢也就成為其第一語言。」談及自己以非第一語言書寫,在海外取得成功的幾個因素,除了來自個人努力與運氣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哈金認為是「自己在關鍵地方沒有做錯」,並由此談到另一位他甚為欣賞、曾三獲英國文壇最高榮譽「布克獎」提名(Booker Prize)的作家毛翔青(Timothy Mo)。「香港擁有另一種文化,例如現代作家董啟章就很優秀,另一位作家Timothy Mo也很優秀,其母親是英國人、父親是廣東人,論才華,是很了不起的作家,亦是香港很獨特以英語書寫的重要作家,但他之後跟出版社鬧翻,其他人漸漸不知道這位作者。其實他的英文行文寫得很好,小說《Sour Sweet》也是跟移民有關,可惜一步走錯對自己傷害很大。」
超越國家語言的參照系統
筆耕數十載,對於寫作的意義,哈金在過往的訪問說過:「寫作就是受苦,從中為自己的存在尋找意義。」隨著年歲增長,閱歷與眼界更廣闊,寫作這刻對哈金來說,精神上的意義變得更加重要。「一開始我常用的詞語是『生存』,那是包括物質上與精神上的。我們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但憑自己能力進入領域,看到一個比國家大得多的參照系統,可以繼續將有意義的事情做好,這是最重要的,我也慢慢意識到,自己能在這個系統找到生存的空間。」
身為移民海外的作家,哈金笑言自己的寫作生活,並不如村上春樹般,可以無間斷地跑步、寫作、跑步、寫作,原因在於移民者想要好好生存,凡事都只得靠自己。「村上春樹比較幸運,在日語的大環境之下,其作品的英語翻譯,是非一般的優秀。我在這裡的情況不太一樣,移民只得靠自己去生存,平日的幹活比較多,近年太太患病,我也必須在家裡待著。」日常也許枯燥,靈感卻如泉湧,如何寫得出小說的細膩情感,哈金認為擁有一顆敏感的心,是達至好作家的其中一個重要條件。「好的作家,是能夠隨意從日常發掘到不同素材。別人覺得很平常的事,但你覺得有意思,說出來跟別人的看法不一樣,擁有這顆敏感的心靈,是最基本,也很重要。」然而,一個人畢竟無法完全體驗世間萬物,除了敏感的心思之外,哈金說,很多東西都是源於想像。「一個人能有多少一手經驗?真實是一種虛幻的感覺,作家的關鍵,是要創作出這種感覺,很難,卻是基本功,像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也是將爺爺那代的經驗轉化,讀起來卻像是他第一手的體驗。中國現代史上的兩位優秀作家,魯迅與汪曾祺都曾想過,要寫關於唐朝的長篇,但當他們在不同時期到訪西安看過遺跡,回來後就決定不寫了,因為躲在書房裡可以想像到一片唐朝,不過當看過盛唐的遺跡,這些想像就沒有了。」
談及自己的寫作計劃,哈金表示繼今年的《湖台夜話》後,將來也許再有機會出版華文作品,然而當前「手頭上幾本書已做不完」,其中一本新作,預計最快將於明年年初面世。作為早已享負盛名的作家,哈金說自己在寫作方面仍有追求,亦坦言每本新書的出版與誕生,對他來說也是挑戰。「每本書最後能不能寫完,是不知道的,能不能出版,也是不知道的,但我在寫作方面追求的,是要跟自己對上一本作品相比,做出一些不同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