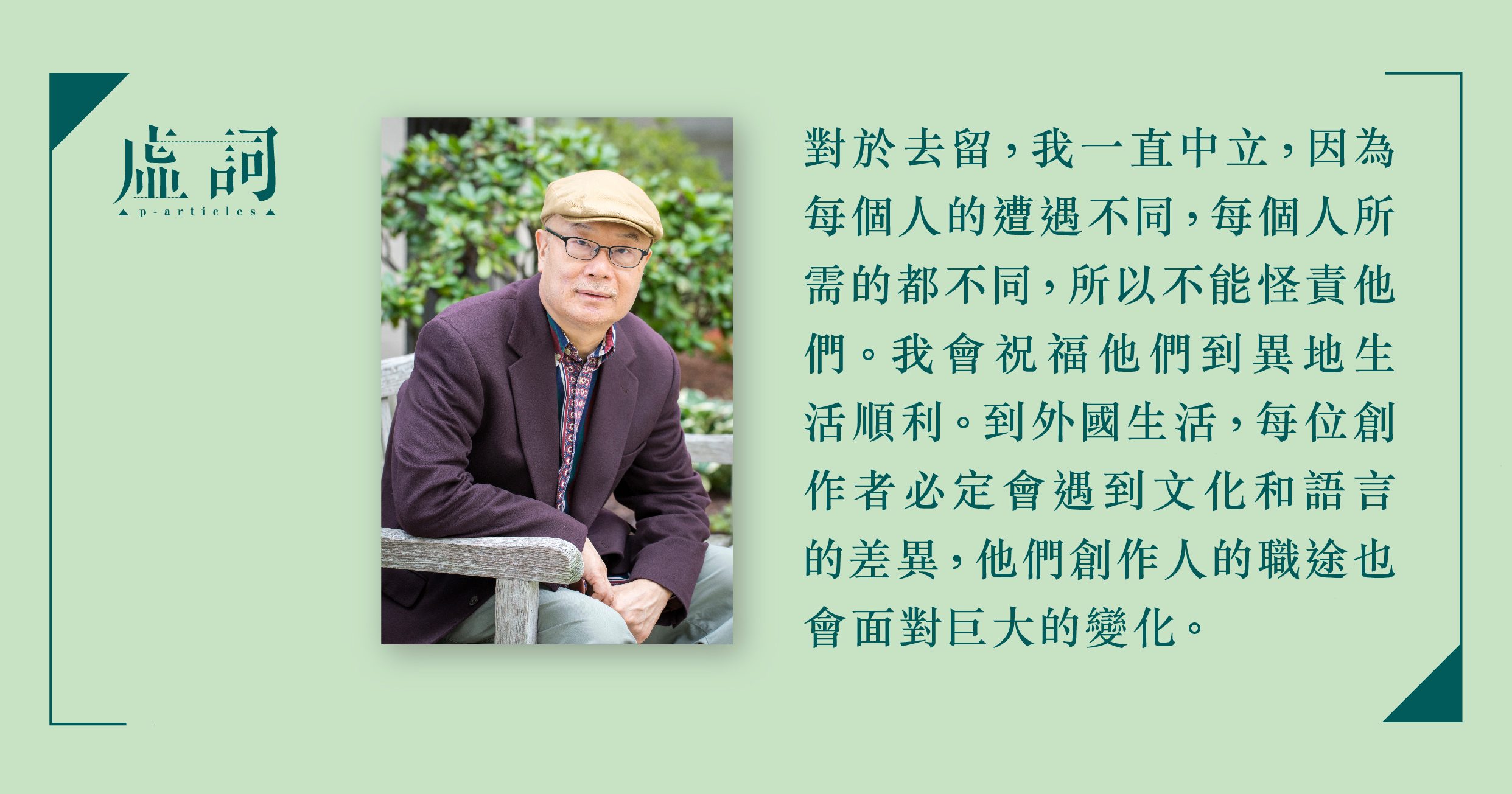在美國寫作的「邊緣人」——哈金
散文 | by 楓柴 | 2022-03-14
出生於中國的哈金在1985年赴美修讀研究課程及博士學位,期間他一直運用英語及漢語寫作,一共有20多部著作。他在美國期間榮獲多項文學獎。因此,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華語作家創作坊選定哈金為「2021年度卓越華語作家」,並於2021年9月28-29日邀請他舉行線上講座及大師寫作班,主題為「邊緣寫作」。我有幸被推薦成為本學年的華語作家創作坊學生大使。參加活動後,受活動內容有所啓發,同時作為時下社會的一位年輕創作人,對於現時社會狀況下創作人的定位有所感受,因而寫下此文章。
兩年前的初夏,這片森林開始被外來者強制作大幅規劃。動物們相討政策的會議室首當其衝的被鐵球車砸成廢墟,其次便是畫廊、書店、電影院被砸到破爛不堪。
這些畫廊、書店、電影院的範圍都被外來者用粉筆畫下了紅色的圓圈,令螞蟻們迷失在這紅圈內。每隻螞蟻都煩惱如何在這紅圈內生存。外來者的舉手投足不時掀起粉筆灰,令圈內彌漫紅塵,令螞蟻都看不清前方。過後粉筆灰都向內飄散,邊界也向螞蟻們愈逼愈近。螞蟻們起初都會為住這遍森林的同伴發聲,但它們眼見同伴一個一個,一批一批地被外來者裝進玻璃罐,它們也逐漸沉默了。
平安生存是每種生物的本能。而大家近年都煩惱着、擔憂着如何繼續在這片森林中平安生存,甚至有些同伴寧願往另一片森林走去。
當然,為了平安生存可以很簡單,但這樣真的有意思嗎?
一隻螞蟻看似渺小,但集合起來可以纏死一頭大象。螞蟻,除了是刻苦耐勞,更是有骨氣的。
創作人同樣。
一位創作人應該是有風骨。身為一位創作人,時刻在任何地方都要問自己一條問題—「我的責任是甚麼?」這是每位創作者都必須思考的基本問題。創作人是必須回應時代,令讀者閱讀作品後有所思考或得著,甚至是改變,哪怕是丁點兒也好,否則與一部打字機沒有分別。哈金在講座中提到:「作家不可以活在過去,要回應當下,要跟上時代進步。」尤其生活在這世界,每一天睡醒,外界也在轉變,發生着一件又一件突如其來的事。儘管我們個人回應時代的力量有限,但文字的力量是無限的。口耳相傳可能會以訛傳訛,但文字、藝術和電影並不會。一位創作人的位置是本土對外界的一座橋樑,我們透過作品去記錄當下的歷史,記錄那些歷史上沒被記載的事情,透過作品傳揚開去,至全城、至全國、至全球。這不但是為創作者自身而發聲,更是為社會受壓迫、面對不公平的群體發聲。哈金的《在他鄉寫作》中提到:「這裡需要的是一名藝術家,站在當下的社會需要之上,創作一部真實的文學作品,將受迫害之人保存在記憶之中。是的,保存是文學的關鍵功能,以抵抗歷史失憶症,以保存必須不受時間侵犯的文學作品的自主性和完整性為前提。」假如一名創作人整天只創作一些與現實世界一點也沒關係的作品,他也稱不上一位真正的創作人。
如今,這裏已不是個適合創作的地方,原本利落的紅圈現都被風愈吹愈散,變得模糊。於是有一批創作人選擇離開。對於去留,我一直中立,因為每個人的遭遇不同,每個人所需的都不同,所以不能怪責他們。我會祝福他們到異地生活順利。到外國生活,每位創作者必定會遇到文化和語言的差異,他們創作人的職途也會面對巨大的變化。
每位到外國的創作人,在當地都是「邊緣人」,據哈金在活動對「邊緣」的解釋,它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別人把你從主流邊緣化,二是指自己無法融入或不願融入主流,而主流中心則是指當地傳統和保守的文化。作為一個當地的外來者,難免會有文化差異,甚至抵觸。所寫出的作品也難以讓當地讀者引起共鳴,從而創作人的道路也變得崎嶇。哈金講述自身昔日於美國面對相似的情況時,他認為受到限制下,不應因為政治環境變而改變自身所寫,應按自身的心寫作,並改變調整價值和內在系統。可見,即使離開這片土地的創作人,移居外國仍然可以繼續書寫原本地方所發生的問題,透過作品記錄並揭示這土地的不公不義,不能因為生活變得安逸而忘記了「家」。在這情況下,創作人需要以邊緣人的角度書寫,寫關於「家」的社會問題、「家」的文化。儘管外來文化為題材的作品未必受當地人的青睞,但只要創作人能運用一些技巧加以修飾作品,把「家」的社會問題包裝及無痕地融入故事中,於外國也可以有屬於自身的位置。以哈金榮獲1999年美國國家書卷獎、2000年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的《等待》為例,小說背景是寫哈金老師的家鄉—中國,人物角色是中國人,側面反映的亦是中國於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社會問題及重大事件,但令這書成功受外國人歡迎的原因是它講述了不同角色在這段三角關係中的等待歷程,而這是有普遍性,能引起讀者共鳴的同時,也能向世界帶出中國當時沒被記載的社會問題。哈金也一直以「邊緣人」的身分於美國寫作,能夠把「家」的社會問題帶向世界,這不正是身處邊緣的優勢嗎?
語言也是另一個移民創作人必定會遇到的問題。在本地和華語地區,華語文學是主流,但到了歐美,英語文學才是主流。假設一位華語文學創作人移民到歐美地區,他不就廢了筆嗎?當然不是,哈金在活動中提及,即使移居外地,亦要用第一語言寫作,不要輕易因環境改變。在這提及的「第一語言」非直指母語,而是創作人最擅長、心中用作思考的語言。個人來看,以第一語言寫作,是最能夠帶出自身感受,當中於作品注入的情懷和建構的靈魂是第二、三語言無法取替的。我在大學修讀雙語創意及專業寫作,作為以中文為自己第一語言的創作人,每當要為英文寫作課寫文章時,我總是覺得作品是差一點東西,相比中文寫作好像沒有強大靈魂與讀者建構關係,就只是為交功課而已。相反為中文寫作課所寫的文章,作品靈魂是常在,它會自然地牽引着我寫下去,不知不覺間內心的情懷也因而被激起。寫作語言是很個人的,因為每種語言都有其獨特性,每個人都有一種最順心他的語言,而這就是影響作品靈魂的因素之一,儘管華語創作者移民到歐美國家創作,讀者群會縮小,但也不能因為讀者群而輕易改變寫作的語言。華語人民群體是廣大,每個歐美地方也會有一部分的華語讀者,任憑這個讀者群相對狹小,但只要作品寫得優秀,作品便會有其位置,甚至會吸引書商為此翻譯。文學是有普遍性,終有一天,優秀的作品會得到世界讀者的青睞。
在這紅圈內,我們這些創作人將來的命運到底是怎樣、文藝界再會有怎樣的轉變,我真的不知道。但我只知道,本地文壇正在衰落,我們這些留下來的螞蟻須堅持自身的信念,盡做身為創作人的責任,以保存僅餘的文壇。而離開了的創作人,他們面對的問題和困難絕對不比我們少,但無可否認他們的創作自由度更大,亦有「邊緣」的優勢,更好的把「家」的文化與社會問題傳揚出去。只願他們勿忘家園,發揮文字的力量,告訴世人下沉中的浮城的故事。
最後也願每位屬於這片土地的創作人,無論身處何處都一切平安。
(標題為編輯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