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作家創作坊】「離」留的創作人們 ——賀淑芳
如是我聞 | by 楓柴 | 2022-08-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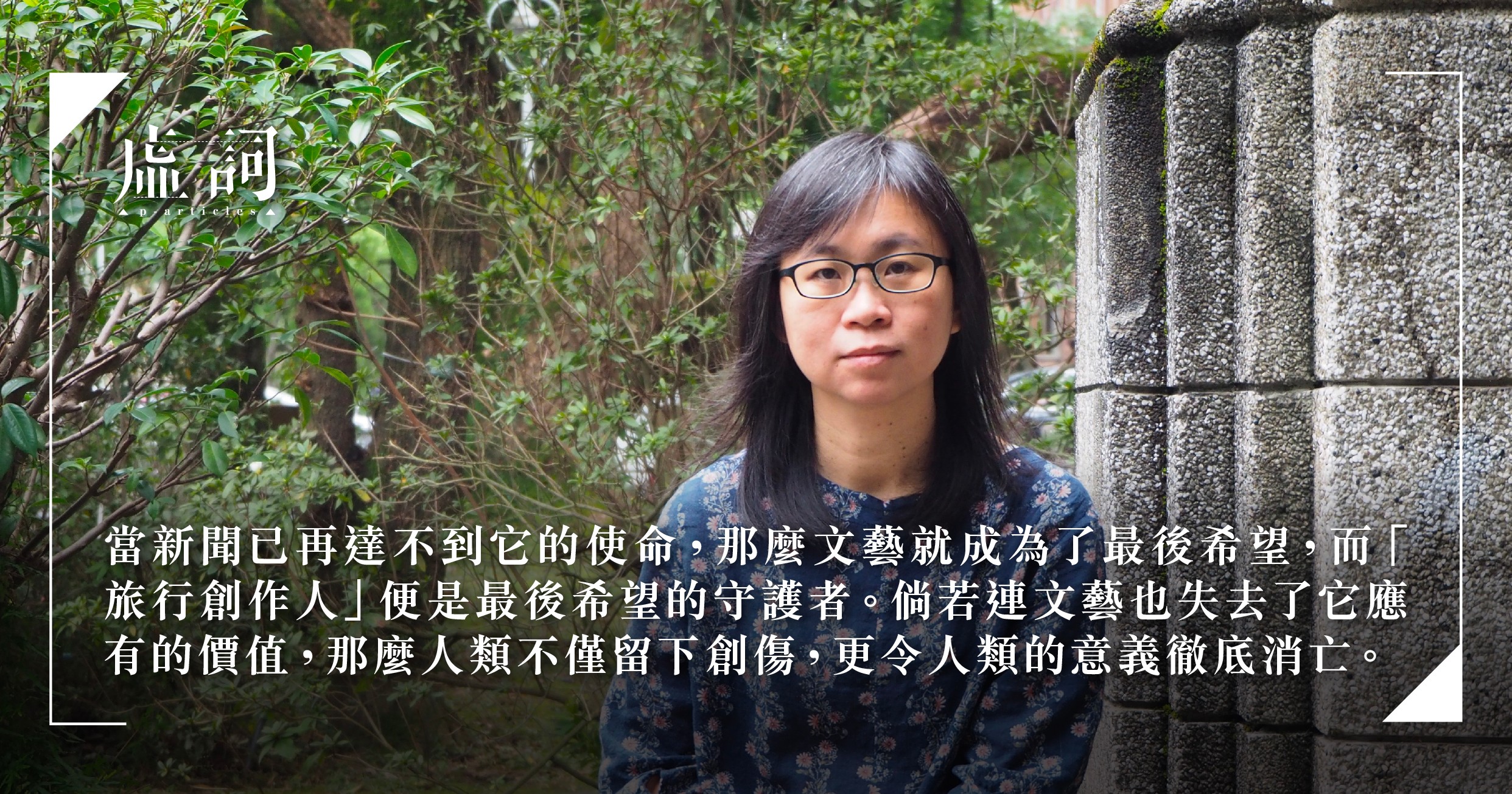
299000582_756520988737367_9016291530983183546_n.jpg
香港浸會大學學院華語作家創作坊於本年3月7日至4月7日邀請馬來西亞作家賀淑芳女士擔任本屆創作坊的其中一位「華語駐校作家」,並舉行線上公開講座,主題為「何以需要講故事?棲居地方,或如旅人」,以及一共三課的寫作班。我作為本學年的華語作家創作坊學生大使,參加活動後,受活動內容有所啓發,同時作為一位年輕創作人,對於創作人的位置有所感受,因而寫下此文章。
社會是由各種職業推動的,而每種職業都有屬於它的使命,譬如記者就是反映事實及監察擁權者、工程師就是用科學技術來解決實際問題。但創作人呢?
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下,文藝只剩下宣傳、娛樂之用,一個有閒階級的標準,它的價值只僅用金錢來衡量。文藝作品則能影響社會過百年,這源於人文價值,一種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價值。
在文學範疇上,要作品達到有人文價值的條件是在於能與現實建一道橋樑。
文學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種,不論是虛構或是非虛構,但它們最核心的作用是帶出社會的問題或某些人所受的遭遇。賀女士在講座中提到:「新聞只是帶出事情局部,資本主義下,傳媒只會保留能吸引眼球的部份,把有關人的部份篩走,所以小說作為虛構世界就能夠透過文本去補充被抹去的部份。」當新聞無法而把當中最深層次的事情和問題挖出來時,這時便需要文學。據艾布拉斯姆(H. M. Abrams)的《鏡與燈》,不少理論家把文學視為反映現實的鏡子,但這種反映並非無所選擇,例如亞里士多德便認為文學並非描述「已發生的事」,而是「可能發生的事」,那些事情的普遍形式和邏輯。我認為文學中的補寫世界正正是寫出可能會發情的事情,創作人就是透過文學參與事件,把虛構世界延伸到相關議題,並從中呈現社會問題和某些人所受的遭遇,藉此達到間離效果,把批判的作用留給讀者。倘若是失去了能理性批判的文學,這種文學大概就只是一部宣傳之用的擴音器。
處於這個敏感的時代,人們動輒就被扣上有違國安法的罪名,它就像一把鋒利的刀,架在創作人的手上。因此,當創作人想透過文學來反映這片土地的現況,在這寫作環境下,有些創作人對此選擇直接離開,但無論如何,離開家鄉並不是代表結束,而是一種延續。
不知道是天意還是怎樣,恰好我擔任學生大使所參加的兩次講座都是由「旅行作家」作嘉賓(哈金與賀女士),他們都有着異地寫作的經驗,這彷彿在告訴我異地寫作是對創作者自身更好的。除了更好的把自己家鄉的社會問題帶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創作人能豐富閱歷,豐富世界觀。賀女士在講座曾提到:「每個人都是世界的旅行者;創作人離開,他們的故事也會跟着離開,而到了新地方又會加入新故事。」出走外闖是創作人不可或缺的創作元素,故事是基於創作人的經驗建構而成。他們到外地不應看作是一種逃避,反而是看作以另一個角度看自己,看家鄉。只要人到哪,便到哪繼續書寫,那麼離開就不是一個句號。
我還記得賀女士於講座最後引出了阿甘本《幼件與歷史:經驗的毁滅》的一句:「每個社會成員都會承受著因為沉默而潛在的集體創傷。」當新聞已再達不到它的使命,那麼文藝就成為了最後希望,而「旅行創作人」便是最後希望的守護者。倘若連文藝也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那麼人類不僅留下創傷,更令人類的意義徹底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