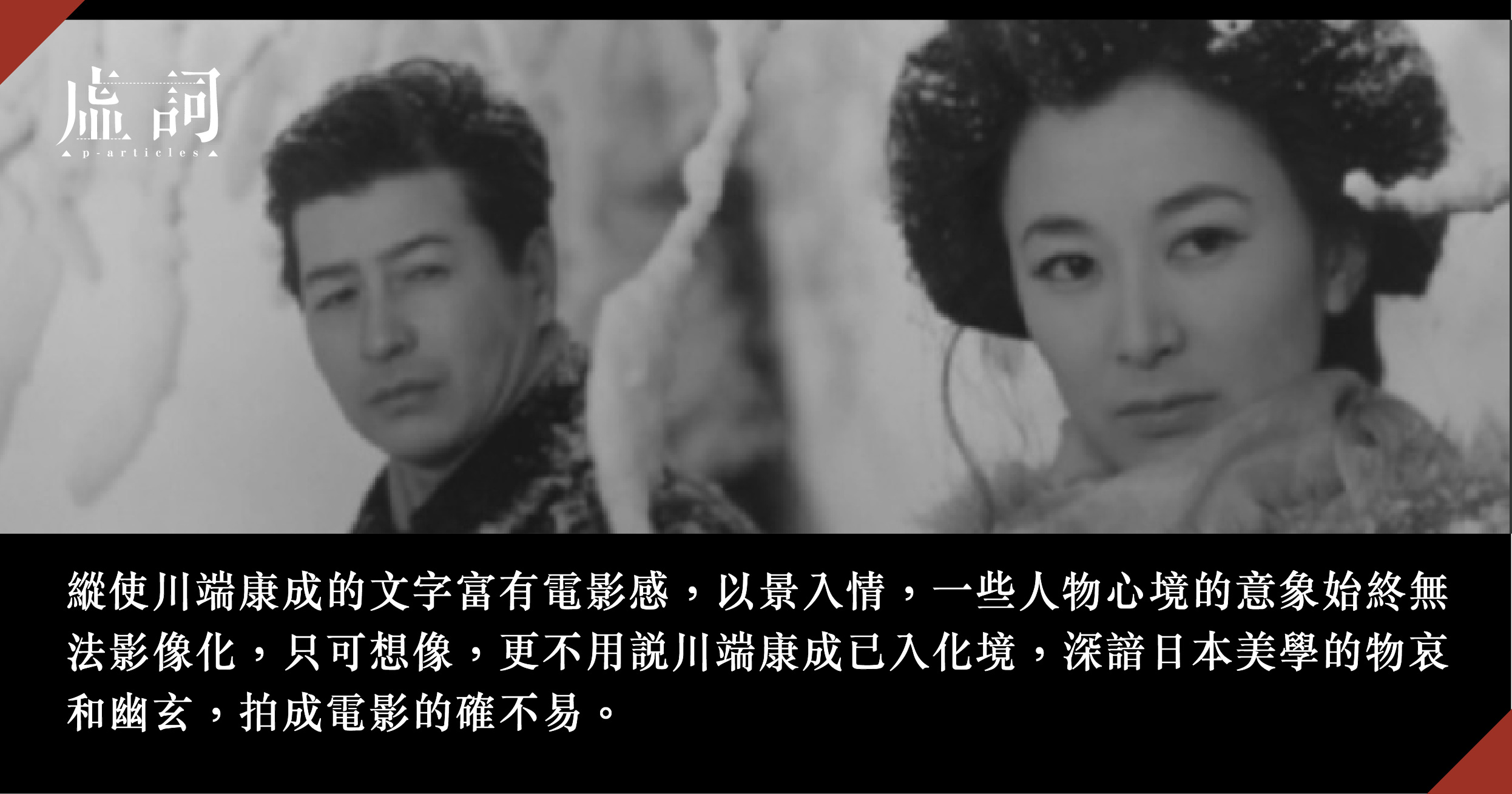隧道盡頭的唯美與虛渺——川端康成《雪國》
「穿過縣界長長的隧道,便是雪國。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車在信號所前停了下來。」非常巧合,今年迎來韓國電影百年,3月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李滄東導演,1999),同時適逢日本文豪川端康成120歲冥誕,電影節發燒友於4、5月放映九部文學映畫,當中包括《雪國》(Snow Country,豐田四郎導演,1957),兩部電影都以列車駛出隧道的長鏡頭作為開場,相映成趣。
《薄荷糖》的鏡頭實為倒帶,列車是在駛入隧道,呼應倒敍結構,引領觀眾回溯殘酷和悲哀的政治現實。《雪國》的鏡頭不是倒帶,但在我看來乃是另一種駛入,以實為虛,走進了淒美和虛渺。然而,縱使川端康成的文字富有電影感,以景入情,一些人物心境的意象始終無法影像化,只可想像,更不用說川端康成已入化境,深諳日本美學的物哀和幽玄,拍成電影的確不易。豐田四郎的處理手法其實很聰明,但某程度上也避重就輕。
雪和火︰物哀與幽玄
電影既是聲和畫的媒介,又是節奏和結構的媒介。導演透過場次調整和細節增減令節奏更加明快,結構更加理順。最成功的例子莫過於逐鳥祭一段,原作本來對此兒童節慶輕描淡寫,主要交代島村(池部良飾演)爽約,令駒子(岸惠子飾演)空歡喜一場,也不肯定能否再見,直到數個月後重逢,不過導演加以著墨以烘托駒子苦等島村的煎熬,也放葉子(八千草薰飾演)和弟弟的團聚進去,好安排葉子到火車站為弟弟送行,從而遇上駒子,兩人遂為島村爭執,以她們的互動勾勒三人瓜葛。
此外,導演大幅刻畫駒子旁觀一眾兒童穿著草鞋、手執火把,在雪地齊聲高唱逐鳥歌到天亮的景象,既側寫駒子的孤寂,又把兩大元素突顯——雪、火,為結局的大火作隱藏的鋪墊,是相當高明的編劇技巧,而雪和火作為大自然的元素,更體現了原作的物哀和幽玄。後來葉子向島村轉交駒子的字條,字條是捲著並放在小草鞋玩具內的,島村說小草鞋可愛,她給一雙小草鞋讓島村把玩,然後二人展開對話,這個小設計令角色的互動更有生活感。
另一方面,影像語言亦見心思。鏡頭運動靈活多變,左右、前後、上下、固定、推軌、伸縮皆按導演對劇本的理解出現。鏡頭隨著演員的走動穿過或掠過一扇又一扇門(在旅館內),一幢又一幢建築物,一棵又一棵樹,一座又一座山(在旅館外),附以分鏡、構圖、燈光提高影像的縱深感,觀眾的視點也一直流動。再者,人物不時見於門縫,不然就是黑影突出,於是狀態更形虛無。導演的場面掌控力亦高,藝伎娛賓、繭倉失火人數眾多,前景、後景卻仍設計得宜,鏡頭組合有條不紊。
除令觀影體驗更流暢外,一些主要場景的確拍出原作神髓。島村揩了揩列車完全被水蒸氣瀰漫的玻璃窗後驚見葉子,鏡面虛像(葉子倒影)和鏡後實物(窗外風景)交疊並晃動一場,不知菲林有否特別處理,但畫面構圖和光線是精準的。駒子在候車室窗口望向鐵路,等待著葉子和行男到埗一場,導演拍了她在窗口上的倒影,令兩個女人的關係顯得微妙。島村跟駒子第二次見面、駒子奏三味線兩場電影語言優雅,由遠至近、動靜結合,前者有一個鏡頭拍島村伸出食指,駒子用嘴貼著,他用嘴叼著她數絲頭髮後指頭髮好冷,在畫面上比她把臉抵在他掌上更簡約。
然而,即使整體效果簡潔流暢,但導演有時太進取,令片子過猶不及而失去餘韻。我不認為導演炫技,鏡頭運動花樣繁多,但考量是建基於人物心境和觀眾跟人物的距離,只是有時為節奏令鏡頭運動過於急速,剪接太多,令人難以靜下心來。影片亦缺乏空鏡頭,原作好些展現角色心理的景物描寫都因影像化的困難、不夠敍事效能而省略,陽光、河流、山巒、樹木、花朵、飛蛾、蟲子、鐵壺的遠景或特寫鏡頭實在太少,令情感跟季節的融合減弱了。我想陪島村凝視死去的蟲子,感受八疊大榻榻米有多寬廣。
角色崩壞 唯美不再
形式的省略抵消了時空的物哀和幽玄,內容的濃縮亦簡化了人物的心理活動。雖然列車玻璃窗一場的質感仍在,但劇本刪掉島村動著左手食指和凝眸注視,不然觀眾看著他和駒子的情慾互動時,會有更強烈的感受。駒子為島村送行,不隨葉子見行男一場,導演增添駒子目送和走近火車的情節,卻也捨棄島村看一對素未謀面的男女談話和告別的情節,保留了一去可能不返的憂愁,卻展現不出稍縱即逝的遺憾。原作中川端康成大幅形容葉子的聲音,葉子唱歌的情節竟然在電影中消失了。
導演也許認為西洋舞蹈評論家不夠電影感,故把島村的身份改為抽象派畫家,當然抽象派可切合他紈絝子弟的形象,但抽象派也是門派,原作中他只憑藉書籍、印刷品、文字、圖片描寫根本自己未親眼見過的西洋舞蹈,任意想像,欣賞、陶醉在自己空想的舞蹈幻影之中,如同他一直憧憬著那不曾見過的愛情,也跟駒子在日記裡談論電影如出一轍,不只是頹廢和逃避,況且導演也不拍他在東京的生活,只以數句台詞輕輕談及他的職業。他的人物形象略嫌被標籤了,他和駒子的徒勞也被淡化了。
不過,問題最嚴重的莫過於結局的處理,技術雖見功架,文本卻偏離原作的精神。原作中島村坐在車子裡,駒子飛撲上前,二人對話期間聽到繭倉失火,在星空下跑上坡道尋找葉子,銀河的美麗和深邃攫住島村,火災的亂象彷佛是一種反襯。葉子的死是一瞬間,垂直地掉落下來的,本來僵硬的身體遂變得柔軟,令島村總覺得葉子並沒有死。「她內在的生命在變形,變成另一種東西。」「駒子彷彿抱著自己的犧牲和罪孽一樣。」「待島村站穩了腳跟,抬頭望去,銀河好像嘩啦一聲,向他的心坎上傾瀉而下。」
電影中銀河不見了,雪地的車轍不見了。葉子的墮地沒有拍出來,「噗」一聲也沒有。駒子沒有抱著葉子,瘋狂地叫喊「這孩子瘋了」,而是疑惑葉子死去未嘗不是好事,遂見救護人員抬著一些擔架。島村沒有抬頭仰視上空,而是撇下駒子離開。他一走出畫框,影片就跌入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唯美不再,虛幻不再。更甚的是葉子未有死去,生不如死,駒子決定孤身前往東京,離開雪國。大雪紛飛中的孤影固然有畫面感,角色卻已崩壞。幻滅的不是角色的心境(戲劇效果),是角色的形象(戲劇設定)。
幸好影片選角是合適的,演出不因劇本缺陷失色。岸惠子比我想像中的駒子強勢(內在氣場)和嫵媚(外在神態),但演活駒子堅毅的個性和徒勞的處境。池部良的拿捏準確,島村放蕩卻又儒雅,身上亦散發一股性魅力,但不顯得猥瑣。八千草薰的聲線跟葉子吻合,樣貌清純,可跟成熟的岸惠子形成對比,令人信服。一篇文章指出駒子是「真」的履行者,葉子是「善」的給予者,島村是「美」的追求者,這幾位演員做到了。本片為了雅俗共賞未竟全功,卻始終有探索唯美與虛幻在電影中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