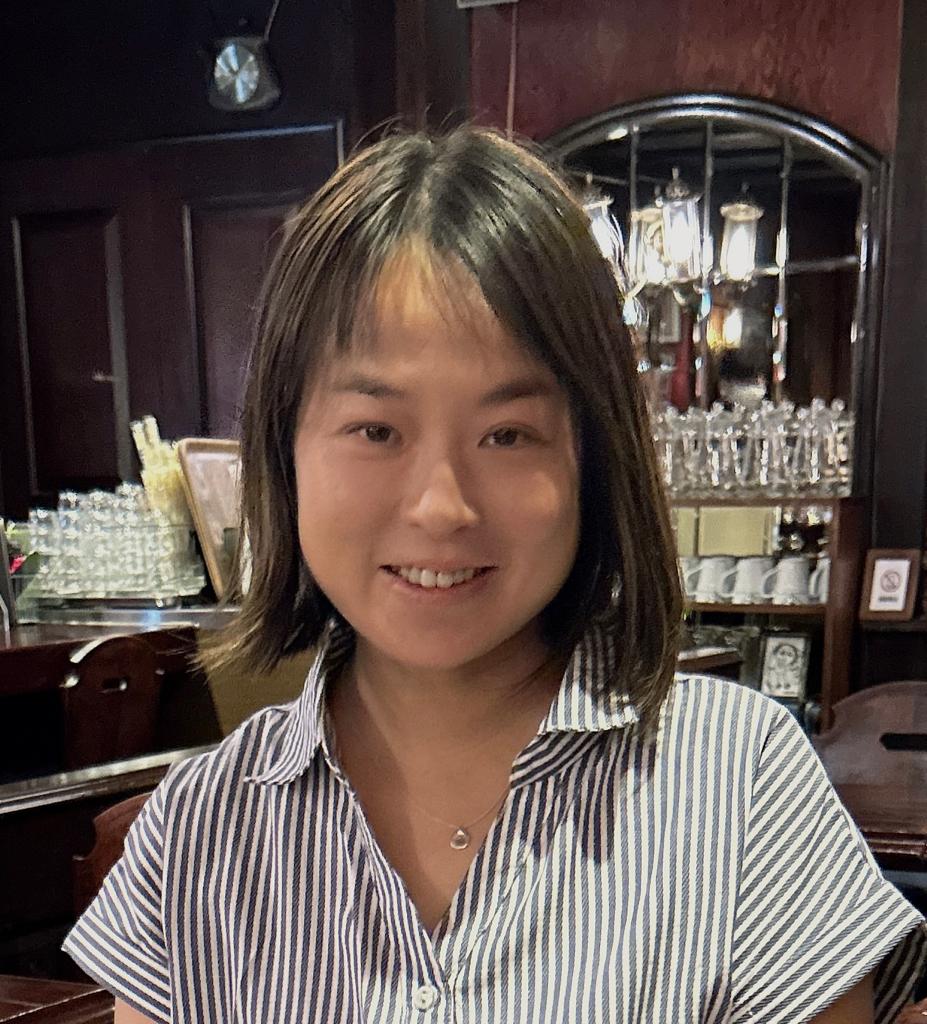《背脊向天》書評:我們在看動物的時候,其實在看什麼?
童年時,誰沒有深深地被動物吸引?無論是商店玻璃牆裡被困的茶色貓,還是那些帶著敵意和憂鬱的流浪狗,堆疊一起的小龜、甚至是突然衝過來擋住視線的白鴿、黏在膠紙上的蟑螂,或是不小心被爺爺奶奶吃掉的小黃雞。這些動物記憶曾經如此鮮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講求快速和功利的城市,除了偶爾想起,我們似乎不再刻意記住它們。
除非我們養寵物吧。養寵物的人,就是在創造寵物的生活環境,這個生活環境、人為規範某就成了寵物的「命途」了。
徐焯賢寫的《養龍》的一位老闆/父親,就像他養的那條霸氣的龍鬚魚。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要養那麼醜陋、霸氣的魚,卻只能給它一個永遠都不夠大的魚缸?魚似乎承擔著一間公司的風水、興衰使命。小說有趣的地方在於,明明是老闆養的魚,魚的命運竟與自身緊密相連,甚至影響了兒子「我」。
小說中,父親變成人魚的隱藏情節也讓人意想不到。小時候養魚的人,最終也會再次養魚,這點我非常相信。養魚彷彿是一種教養,在小說中甚至暗示成一種傳承,它與釣魚、在水族箱中觀魚,一脈相承但又有所不同。就如世事,「死左就買過」,要「東山再起」,這就是我們的意志,也就是為什麼龍鬚魚的表情永遠要一臉權威,卻又隱藏憂鬱。大魚吃小魚的寓意自不必說,但太多小魚卻嚇著大魚,這是多麼真實。
動物的命運往往揭示了人類的命運。「背脊向天」的動物,難道就只能低頭嗎?這本書雖然寫的是動物,當然也不會放過對人類處境的思考。
葉曉文寫的故事,描繪的「牛妹」是唯一寫在漸近自然生態之中的動物。牛妹與一個城市年青女子阿艾的相遇,構成了這個故事感人的主軸。相對來說女子在城市環境中的跌宕,反而是略寫。「以體力勞動工作為主的農務工作反而更輕鬆。」就算是愛情甚或婚姻那情感的質量,還不如與鄉間一隻牛的感通那道心有靈犀。
城市生活中有太多的破落關係,來龍去脈,千絲萬縷,無從說起。因此,故事從田間的義工生活寫起,田間並不是為了美化城市而存在,田野間也有汗水與辛苦勞作。但那腳踏實地的氣質也連結到真實生活,其實也是作者心心念念的「策展工作」-照顧的意思。小說的結尾讓人驚艷。大自然才沒有那麼多兩忘煙水的感慨,春去秋來實事求是本來就會生生不息。
因此,書中的每一種動物,其實都在反映著「生存狀態」,我們從更弱勢的動物中看到「暗號」。張婉雯所寫的《螞蟻》-我們的生活有時苦澀卑微,卻迫成強大運行的意志。如日常生活一樣,總是不斷陷入各種麻木的小陷阱,這些微小的痛苦或不快不會又未至於讓我們墮入萬丈深淵,於是很多時候,我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忽略了;但長期下來,這種忽略漸漸組成了全然的、不自知的麻木。當麻木變成日常,一些物種要捏死另一種也是輕而易舉的事。小說中作者的生活不斷被螞蟻打斷,這正是最真實的「反麻木」,甚至是由此為生活打一個逗號,一串省略號。偶然抬頭提醒我們,煞停沒有必要的小感傷,為思考掀開枝頭,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生活仍在繼續。
以動物作為寓言的寫法實在太多,許多作品已經成為經典。然而,作為肉食者的人類,若還是食肉,我們便只能從人類的視角出發。「肉食者鄙」,這在李日康《換骨》中有出色的描繪,能夠殘暴對待動物的人往往也是輕率地處理自己和他人的命運,墜入「惡」的輪迴之中而不自知,直至有了「善」識。有趣的是在小說結尾中覺醒的,是對主角來說可能無關痛癢的一介婦孺, 她究竟是在何時開始覺醒的?那個拐點到底在哪裏?
動物與我們一樣,同在地球生存著,雖然許多人視而不見。有時,吸引人的反而是已經滅絕的恐龍。可洛《絕種》的取材很特別-在我們身邊總有一個的屋邨商場-哪個不是寄托了小孩子微小灼熱的慾望?街坊街里日久生情的相處、平實但是溫暖的生計?小孩子總仰慕龐大的事物,例如早已滅絕的恐龍,這也是憑藉想像力而得到的力量。小說側寫城市的變遷,無論是疫情還是生態,原來時間才是最大的恐龍,可是恐龍最終不過成為已不太受歡迎的小脆餅。恐龍最終變成一隻小貓?可幸的是這隻小貓悠然地穿梭在輪迴重生的舊商場之中,仍然依賴小情小景怡然自得的生活著。
唐睿的《家守》則從幾個視角出發,以此來探討親情、愛情、工作與友情的不同介面,反覆描繪在重重欺騙和說辭之中的異象困境,尤其是作者在與母親的關係中,已經分不清誰是根源。小說用了或者作為「家守」的壁虎比喻各種關係︰壁虎能夠自斷其尾這件事很神奇,斷尾又能重生則很有力量。小說中的女兒、母親、情人、繼妹、仇人都果斷斷尾以脫離危險,然後又能夠再生出肢體,就是為了在艱難的處境求存,這時失落的母體(偶爾相信的信念)甚至變成一個用以「慶生」的蛋糕。然而已經斷尾的人往往不自願地公告天下,在生活中斷掉尾巴雖說是為了生存但是也足以讓大家公審。然而壁虎也靠著自己的皮重生了。也許,除了自己也沒有人知道那已經斷掉的尾巴究竟流落到哪裏了。
這本書引領我們從動物的視角中,找出與我們生存相呼應的啟示。許多故事不約而同地展現了一種平衡感,動物與人互相對視,彼此觀照,這正是我認為這本書特別耐讀的地方。
2024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