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驢子伊艾奧》——動物和人類知道了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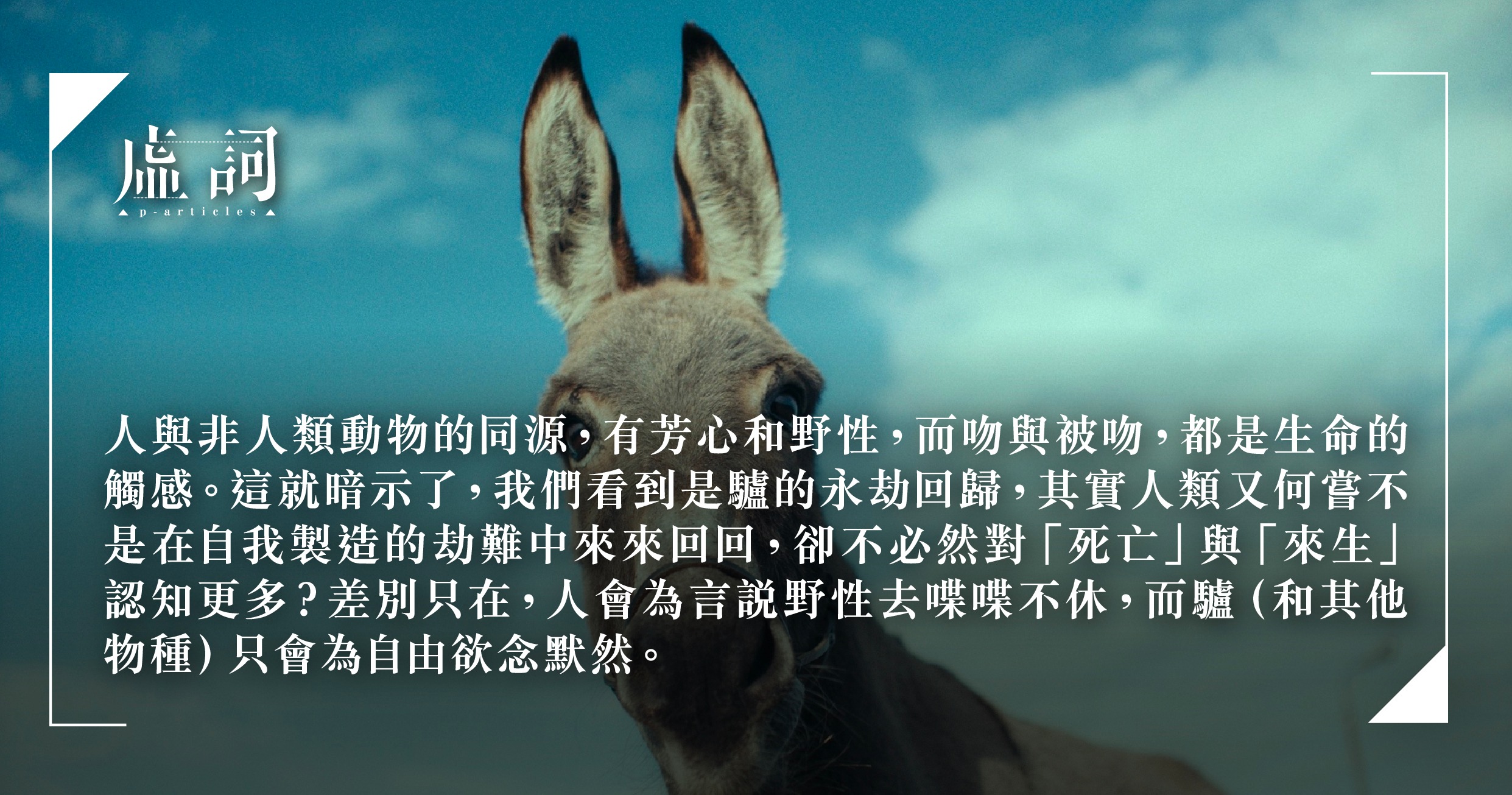
318481027_686991756374556_1418831579879352505_n.jpg
牠在最後跟隨牛群,走入倉庫;對觀眾來說,相信是牠命不久矣,因為那個黑暗環境,似預示走入屠場前,動物會被昏迷處理。
說的是波蘭導演傑西史考利莫斯基(Jerzy Skolimowski)作品《驢子伊艾奧》的尾聲,那頭再次流浪的驢,或瀕臨死亡。這幕死亡的預示,尤其逼迫筆者多想英文片名《EO》的台譯——《如果驢知道》,而EO是牠的名字,卻被譯成如同詰問的茫然,因為這個詰問沒有主體:如果有甚麼必需要驢知道,那究竟會是甚麼?
電影的尾聲,卻像提供答案:驢子伊艾奧命不久矣?又或,驢子伊艾奧沒有來生?都是逆向思考:難道牠知道將會死亡/沒有來生,就會走回頭?更甚者,是難道牠(作為驢/動物)會知道人類對於「死亡」與「來生」的認知?
當然不會。而即便會,卻不必然是人類的認知了。然而提出以上詰問,是要說明,導演志不在如坊間說法所云,僅為拍出驢的一生;相反,戲中的那頭驢根本就在經歷輪迴,而要觀眾想到,那不是純粹向法國導演羅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1966年作品《驢子巴達薩》(Au Hasard Balthazar)的致敬電影,卻是再思「生態電影(Ecocinema)」的上乘大作。
永劫輪迴的不同角色
為甚麼說這頭名叫EO的驢,根本就在經歷輪迴?因為導演有意讓牠的生命,在不同「角色」裡轉化。比如順著電影情節去細數,甫開場牠是戲班的展演動物(Performing Animal),之後戲班破產,牠成了工作動物(Working Animal)而為人甚至為馬搬運勞役。但後來又因為在收容所寄住,療養小孩,成了聖所動物(Sanctuary Animal);可是當牠再遇少女主人,就破欄而出,像踏上「尋親」之旅,卻是流浪動物(Stray Animal)。往後牠走入森林、城市,誤入球賽,再被虐打斷腳,一直都在不歸途上。
不同的角色,就像是永劫輪迴,尤其自牠幼時與少女主人分別之後,就不被善待(即便在收容所也只是為小孩服務,而被虐待得到治療後,雖然重新站起卻要為「動物醫護場」做運送工作)。這四頭飾演EO的驢子,最佳演譯,就是木納神色,應對生死蒼茫;也順理成章地被安插在不同的生命角色裡——雖說是一頭驢的故事,卻已涉及所有動物倫理命題。
主觀視點的血紅母體
但值得追問的,卻並非這頭驢是否可憐,抑或要牠工作再對牠痛擊,是否等於虐待。反而,值得深思的,是導演以怎樣的景觀,要人想到輪迴?又為何會是輪迴?
「輪迴」是佛學的宗教想像,相對西方信仰未免格格不入。但導演必定深明「輪迴」之說,而要觀眾進入主觀鏡,從驢的視覺,看那血紅一般的外在世界——暗紅場面極多,有模擬驢的視點(可是生物學對哺乳類動物如何看到顏色,眾說紛紜),也有現實場景的紅色天花燈,又或車廂中與酒館內的迷幻色調。
但驢子眼中的紅,是不停打轉的周邊物事——有少女主角演出時的舞蹈,也有馬匹的圓形練跑場,更有轉動的風車。不過那也像哺乳類生命脫離母體的子宮管道,所以由馬糟走向聖所(更有蝙蝠逆向飛行),再從聖所到流浪,經過森林(有狼與獵人的野性呼喚),都在鏡頭下呈現EO走出一次又一次的「通道」,暗紅色調間歇浮現,如脫離母體的往生,卻是下一回生命的苦難。
對照布列松,致敬與走前
無論是有心或無意,苦厄再臨,讓《驢子伊艾奧》比布列松的《驢子巴達薩》走得更前——當然我們並不會要求後者拍於1966年的電影,會涉及豐富的動物倫理想像,然而布列松其實是以驢子巴達薩作為側寫,卻是人的故事,說女主角同樣幼年與驢交心,長大後因為親父生意折損,失去了驢,也同時被少年流氓和中年農人對她的身體虎視眈眈。故事結局,是她被凌辱後的生命消亡,以及流氓帶同驢子逃走,讓牠無辜中槍,而命盡於羊群裡。
布列松也有用上驢子主觀鏡的時候,但主要是牠被收於動物的籠牢旁,如旁觀牠物的痛苦;對應到《驢子伊艾奧》的EO,看到馬群中的馬被善待,而在醫護場內其他動物受困,都由木納神情去反襯哀傷,算是同出一轍。不過《驢子巴達薩》說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無情故事,而驢子只是配置與象徵;相反《驢子伊艾奧》雖有致敬之意,但走得更前的,是以驢子為本,去說非人類動物根本走不出人類的不仁現世。
逆向觀照生態電影
這種不仁,有人為的直接凌虐(如戲中的虐打);但也有間接的無力現實,比如EO終於因為重遇少女主人,從聖所出走而誤入城市,口渴難奈,在水族店櫥窗外看到一大魚缸的水,卻飲水不得;更諷刺是隨後來了一輛消防車,也是整車的水,卻與驢絕緣。這兩幕的安排,都對應到電影尾聲,EO在逃到農場前行經水壩大橋的一段,教觀眾相信牠同樣口渴,而被水壩強勁流水包圍,可水都是飲不得,哀感更甚。
話已至此,就正是「生態電影」學究的一場觀照。「生態電影」可以是商業大片,也可以是小眾作品、紀錄片,而只要涉及生態、自然、動植物,更能延伸我們對生命的既定理解,以至對物種多樣性提出深思,都可作此類電影討論。說法是正面的,因為能夠為生靈深思,而看到動植物不只單一想像,或都能增強觀者對生態的認知與愛護。
不過《驢子伊艾奧》是一次逆向展示,即驢子EO真的如同經歷輪迴,當上了前述的多元角色,但牠的「多重生命」,只是一場又一場的哀感交織,如同經過水源卻是與水絕緣。也就是說,多元,不必然指著正向思維,但更能逼迫觀眾思考生命何價,那就是電影之為上乘的地方。
神來之筆,是電影尾聲出現浪子少年的角色,與姑母在廚房爭論(這段近乎是電影裡最長的人物對話),暗示少年的野性難馴,卻又忽然見他手撫姑母頭髮,迎頭親吻對方。下一段就剪接上EO的主觀回憶,是少女主角吻向牠的臉。如此部分若教觀眾茫無頭緒,不妨可以多想人與非人類動物的同源,有芳心和野性,而吻與被吻,都是生命的觸感。這就暗示了,我們看到是驢的永劫回歸,其實人類又何嘗不是在自我製造的劫難中來來回回,卻不必然對「死亡」與「來生」認知更多?差別只在,人會為言說野性去喋喋不休,而驢(和其他物種)只會為自由欲念默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