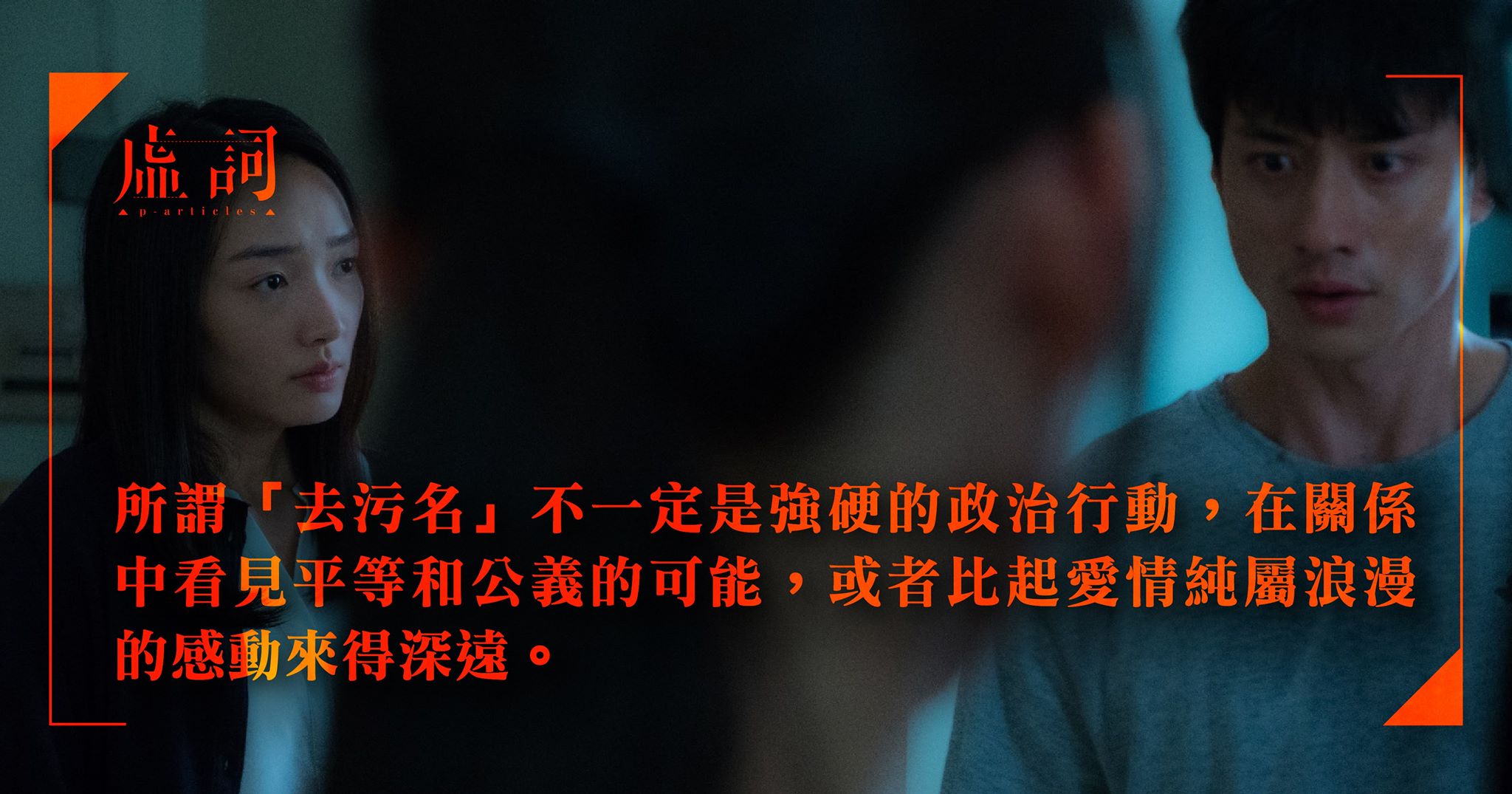《幻愛》的倫理困局——未曾去污名,愛情亦何用?
我相信,電影《幻愛》的出發點的確包括對精神病患的關懷,譬如「食藥唔等於好返」的說法 [1],跟前作《樓上傳來的歌聲》同步的邊緣處境;電影至少不滿足於生物醫學的治療角度,嘗試透過描述精神病患跟社會、跟他人、跟自我的互動,把故事開展出來。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good sex,bad sex/好男人,壞女人
作為《幻愛》的原型,周冠威的短片《樓上傳來的歌聲》至少可被視作電影的「初衷」。《樓上》在短短三十分鐘裡,交代了加諸精神病患的歧視目光、病患與社會的互動以及自我貶損等細節,主要角色還是李志樂和欣欣,但精神病患的生活處境同樣凸出。
《樓上》基本上就是《幻愛》開首二、三十分鐘的情節。《幻愛》的改編,或跟其出發點漸行漸遠的關鍵要素,說來,大部分都繫於葉嵐這個女性角色的增添與設定裡。
我們可以先想想葉嵐是怎樣的一個角色。除了電影未能清楚交代而顯得含糊的「母親問題」,葉嵐跟李志樂一樣具有不被主流價值所接納的「缺陷」,即以性換取利益,有豐富性經驗,更甚顯得「隨便」的行為。[2] 反過來看,李志樂則完全是葉嵐的相反,他是處男,對親密關係有堅貞且專一的態度,也有健康的性慾表現,因為他「有睇日本個啲」。
葉嵐和李志樂在設定上的相反,我們可以看到兩人、兩種性別是如何被安置在性階層(sexual hierarchy)的兩端。這是美國性別理論學者 Gayle Rubin 在文章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裡的說法,即社會對不同的性行為有一套階層的價值觀,有「好的性」(good sex)也有「壞的性」(bad sex),前者包括婚內性行為、異性戀、免費的性等,後者包括非婚性行為、同性戀、要錢的性等。[3] 當然,性階層會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而移位,譬如手淫曾經是邪淫的,現在則是健康的性慾表現;但,這套性階層仍然是決定人們道德價值的重要指標。
從性階層的角度看《幻愛》,葉嵐其實早已身處比任何角色都要底層的位置上,即便她有高學歷、獨居、有賺取收入的能力等等等等,也不像李志樂般得承受作為精神病患的歧視;她還是得被這套性的道德規範給拉下去,在跟「純潔的」李志樂的對比中給拉下去。可以說,在角色設定上,無論最後是不是蕩婦羞辱(slut-shaming),這個「好男人、壞女人」的結構早已內置,並且是葉嵐身上的核心衝突。
女性愛慾的自主或審判
觀眾在觀影的過程中,未必會把葉嵐視作底層或弱勢,至少她在學業或輔導的表現上都顯得強勢和主動,某程度上亦一直誘導李志樂成為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事實的確如此,意思是,葉嵐在整個故事裡並非沒有選擇的餘地,但我們要留意這些選擇換來的後果,以及哪些選擇最後不被允許。
譬如,在葉嵐跟 Dr. Simon 的性/利益關係中,如果不只從男性佔有權力位置而女性只得從中攢取利益的角度理解,我們也可以視之為女性能動性的展現,女性在這套權力層階裡嘗試角力、嘗試競爭的表現。葉嵐的強勢,至少在這一層面上,並不滿足於被動的位置。可是,隨後葉嵐因為跟李志樂的感情而跟 Dr. Simon「攤牌」,Dr. Simon 以「你都唔想尷尬」為由回收葉嵐的研究助理工作,葉嵐的沉默竟令人覺得無奈。她沒有多說甚麼,也似乎放棄再解釋這個決定到底是不是出於「尷尬」。而「尷尬」所指的,恰好就是電影背後所展示的性階層,即以性換取利益,到底是令人「尷尬」的背德行為,而非甚麼角力或競爭,這一部分的價值取向亦見於葉嵐的自我厭惡上。
更令人不解,或根本矛盾的,是當葉嵐主動表示自己有跟李志樂相處的心理準備後,她的老師 Dr. Fung 只以一句「男女關係一直是妳的弱點」為由,要她及早放棄這個念頭。意思是,無論葉嵐如何聲稱自己擁有行動的能力和勇氣,以及願意負起責任,代表權威的聲音仍然希望否定她走出陰霾、面對性格弱點的掙扎,理由也根本不成理由。這又談何療癒,談何自主?
在多重壓力下,李志樂的愛及接納,似乎是葉嵐唯一可以抵達的溫柔鄉。相信這也是文本希望指向的路線。但這樣的接納,並未為葉嵐身處的位置提供任何解套的出路,正如網民「公仔生猛」說:「『唔介意』係計算結果,係道德高地,而唔係愛情。」[4] 也如 Kate Millett 在《性政治》中說:「對浪漫愛情的認可於雙方都有利,因為這往往是女性克服加於其身的更為強有力的性壓制的惟一條件。」[5] 浪漫愛情的甜蜜包裝,始終未能更好地調解、更好地回應葉嵐的內心衝突,即社會的性道德規範;即使「我唔介意」,李志樂的想法仍然包括「妳唔係自願」,以及尾聲衝突中禁不住的「妳好污糟」,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加諸於葉嵐身上的道德審判到底依然有效,這或許是令人感到不適的其中一個原因。
精神病論述的自相矛盾
大部分關於《幻愛》的評論都集中在性別意識的批判上(包括本文),電影另一個核心元素「精神病患」則較少人談及,這或許直接反映了精神病議題在香港的言論場域仍然屬於邊緣少數。筆者希望談及一點電影裡的精神病論述,這有助我們理解為何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正如文首提及,《幻愛》的出發點包含對精神病患的關懷,相信電影的用意也是使觀眾明白病患的生活處境以及情感需要,尤其是對愛的需求。這一部分的取態,我們也可以在前作《樓上傳來的歌聲》中看到。可是,電影在操弄精神病患跟輔導之間的權力關係時,或許是太急於滑入李志樂跟葉嵐之間的感情發展(這恰恰是葉嵐在電影中犯下的錯誤),「真/假」的分辨,最後竟重新回到「醫學模式」的狹窄理解中。
最容易明白的一個例子,正正是葉嵐在輔導中強勢要求李志樂分辨欣欣的真假,並立即以銷毀的形式「告別」幻覺,就連她的老師都覺得危險的行為。在輔導的過程中,李志樂不會質疑葉嵐的指導,這是最清楚的權力關係;而葉嵐以病理學的角度看待幻覺,甚至在尾聲衝突中仍然以「真假」的框架來勸服李志樂,依靠的仍然是精神病學的矯正政治(the politics of coercion)——相信幻覺是瘋癲的病徵,忽視了幻覺對於病患的「意義」,也就無從梳解其中的糾結。
我嘗試以另一個文本來提出另一種可能。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角色應思聰也是思覺失調患者,在第十集的病發情節中,精神科社工宋喬平並未要求思聰當場分辨真假,而是讓思聰訴說他的幻覺,嘗試一步一步梳理他的內心糾結,尋找根植的痛苦。這種方法蠻符合批判傳統精神醫療的「後精神醫療」(postpsychiatry)理論,強調病患的充權,而非「醫學模式」的象徵暴力和支配關係。[6]
不是說《幻愛》沒有這一理解的意圖,我相信電影的出發點也是希望打開這個空間,讓他人能夠理解精神病患的痛苦。然而,或許是為了成全兩人的愛情,或愛情的昇華感覺,電影最後依然粗暴地沿用這個「真假」的框架。所謂的「理解」,就如電影一再提到的「母親問題」一樣,只能默默歸於含糊,這才是真正可惜的部分。

愛情如何救贖?
說回短片《樓上傳來的歌聲》。筆者蠻喜歡《樓上》的原因,在於故事給予李志樂很多跟社會大眾互動的空間,包括凍檬茶的情節、阿玲在街上的病發、酒樓的工作等等,這些空間除了為劇情發展服務,也側面描寫了精神病患所身處的社會處境,或構成障礙的社會要素。跟社會邊緣有關的文本,無可避免要觸及這些部分,藉此重認他們自覺不被愛、不能愛的具體困難。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幻愛》是一部都市愛情片,它希望聚焦浪漫愛情,為李志樂和葉嵐兩個有「缺陷」的人提供可能的出路,或撫慰傷口的機會。但我們亦必須意識到,當一部電影分別以兩個社會邊緣(精神病患及慾女)作為框架,並以他們面對的困難交織成故事,電影就必須應對這些困難背後的倫理問題,也即是說,電影文本無可避免正參與社會意義的建構,或互動。
也因此,愛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為兩人的處境帶來改變和救贖(而不僅僅是高舉愛情本身的救贖性質),如何透過親密關係打開介入社會的空間,仍然值得我們追問。更有意思的是,李志樂和葉嵐兩個角色本來存在一種倫理的親近性,意思是,兩人同樣擁有、同樣身處一個邊緣的位置,這個位置容讓他們以一個不同的目光看待社會制度,就如葉嵐以質問的態度面對心理輔導體制一樣。所謂「去污名」不一定是強硬的政治行動,在關係中看見平等和公義的可能,或者比起愛情純屬浪漫的感動來得深遠。
未能思考個體如何再次跟社會互動和競爭,一種互相撫慰、「不介意」的浪漫愛情,到底,也不過是封閉的想像。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早前在網絡引起熱論的「的士司機幫緊你」影片 [7],隨之而來的揶揄及取笑,或許已從側面引證,我們對精神病患的共情和理解,仍然遙遠。這才是我們——所有觀賞電影的觀眾——需要共同面對的倫理困局。
***
[1] 「當欲望成為病徵,他質疑是否『就咁俾粒藥佢』便是方法」,這是周冠威在一個訪問裡的說法,見陳子雲〈輕鐵如夢,屯門浪漫 專訪《幻愛》導演周冠威〉,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548.html。
[2] 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陳穎的〈《幻愛》中的仇恨之母與高學歷慾女〉,https://www.cinezen.hk/?p=9277。
[3]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arole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Also reprinted in many other collections, including Abelove, H.; Barale, M. A.; Halperin, D. M.),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4] https://www.facebook.com/2014mangaworld/photos/a.1472286309655382/2492437027640300/。
[5] 宋文偉譯,Kate Millett著:《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江蘇人民出版社。頁46。
[6] 這部分的討論可參考另一篇文章〈《我們與惡的距離》:讓「精神病患」說話〉,https://p-articles.com/critics/815.html。
[7] https://youtu.be/6B7YL5mbQC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