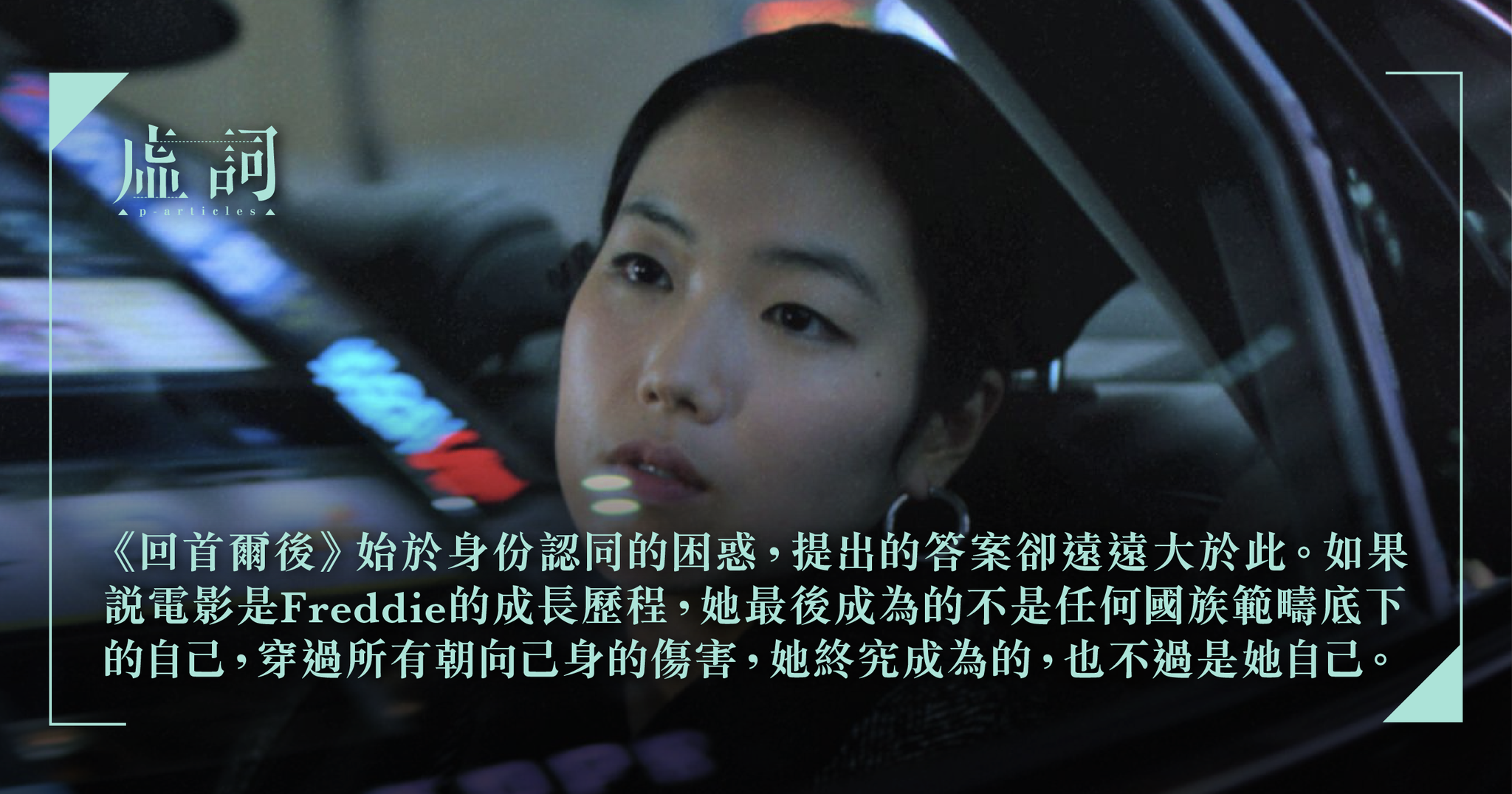《回首爾後》:國界是一道不會綻放的傷痕
電影《回首爾後》(Return to Seoul)有一個在我看來非常準確的中文譯名。
你的確可以把它看成一部「尋根電影」,正如英文名稱意指的,一個韓裔法籍年輕女子意外回到她的出生地,暗自打開了追尋生父母和原生家庭的內心煎熬,「回到」是其關鍵所在。但電影很快就讓我們看到她回到出生地後的重認或錯認,國族和語言的藩籬,生父的追悔和錯愛,標記著「尋根」過程中的種種錯摸和迷茫,像是突然掉進一個始料不及的傷口裡,看著沒能迴避。
事實上,相比「回到」,「後」可能才是電影的真正關鍵。看著主角Freddie橫渡八年的成長歷程,時間跳接,不同的造型和妝容,不同的身旁伴侶,歸根究底,所謂「根」不是指國族或家族上的認同,而是她如何攜著身軀穿過一切,最後回到自己身上。相比尋根電影,它可能更似一部超越國界的成長電影(coming-of-age movie)。
無法跨越的
作為一部跨國和跨文化的尋根電影,《回首爾後》牽涉一個當代政治環境裡或許頗具重量的議題──身份認同。
電影主角Freddie出生在韓戰爆發後經濟蕭條的年代,因為家裡貧窮(生父母後來甚至離婚了,但未有說明原因),年少被領養到法國生活,直到電影開首二十多歲才首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韓國。電影沒有讓我們看到Freddie在法國的成長片段,但從她「看來完全是傳統韓國人」(電影中韓國友人的形容)的樣貌,不難想像她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遇上的困難。明明在法國成長,卻被當成異鄉人對待,加上歐亞之間的差異,相信柬埔寨裔的法籍導演Davy Chou明白箇中感受,才會拍下這部電影。
所謂「身份認同」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你是誰」的一個問題。然而,以國族和國界為基礎的身份政治,必然會引申一個可能更加含糊的困境,無論是成長地抑或出生地,你都無法真正認同和體現自我。就像Freddie重返韓國後被多番提醒韓國人應有的禮儀舉止,甚至被形容為韓國人,無論出於國族抑或文化上的規訓,電影在Freddie身上多次呈現抗拒和不適感,也透過她的目光看到韓國社會的性別樣態,呈現一種跨文化的對照與差異。Freddie這趟跨國的尋根之旅,卻遇上更多的無法跨越,而非一個穩固的認同。
重認與錯認
由此可見,《回首爾後》並不打算讓我們回到二元對立的身份認同,反而在這趟「重認」的旅程中,處處凸顯當中的錯認和錯摸,回到出生地,終究只讓傷口再次淌血。
譬如Freddie重遇生父和其家人,卻只是打開了一個埋伏和追悔多年的家族傷痕,進一步使生父沉溺於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圖補救,錯愛和酗酒當中,這段情節看著令人心痛(也多少帶點韓國中年男人的滑稽),說來也是錯認的核心所在。它不是一個失鄉女子最終回到家鄉的線性歷程,也不是阿飛的「冇腳雀仔」象徵某種必然來臨的悲劇結果,而是讓「尋根」成真,卻最終釀成無可挽回的失誤,到頭來發現最初想得到的原來不是自己想要的,那意欲之物──無論是原生家庭抑或國族想像──可能早已不復存在,或只會令你失望而回。
Freddie這段遭遇,到底說明了這些在跨文化背景下成長的人,如何在國界與國界之間苦苦掙扎,一再追尋自我,最終卻可能一無所獲,或被國界再一次絆倒。沿著國界蔓生的身份認同政治,在此處顯得如此軟弱無力,也是《回首爾後》執意凸顯的問題。電影的確更著意呈現「後來」多於「回到」,意欲追尋的原鄉或家庭早已今非昔比,在時空的變化中,國族身份無法承載的一切生命就這樣流淌於國界的傷痕裡,儼如原地流放,也沒能回到最初。在Freddie身上,同時是一道成長的瘀傷,內裡沒能療癒。
國界作為傷痕
在《回首爾後》,把人們牢牢困住的所謂界線,除了國族和言語之外,其實還有孤兒院裡提到一年只能三次嘗試聯絡生父母的法規等等。這是電影令人嘆息的大背景,即人無處不在枷鎖中的現實。
話說回來,導致Freddie的生父母把她送往孤兒院的年代背景,即是韓戰及後來的蕭條本身,某程度上也是國族及國界的割裂所致,亦牽涉遠大於兩國的全球冷戰局勢。意思是,這道裂在Freddie身上的傷痕及其後遺,遠遠不只是關於她的尋根和失落,能否與家人及自己和解的成長歷程,也是人活在廣闊的歷史時空裡,被時代割傷的無可奈何。因此,無論Freddie或觀眾都無法完全討厭那個沉溺又酗酒的父親,他不過也是為時代所傷,在現代化過程中被迫放棄捕魚本業轉行修理空調的中年男人。這是電影另一個巧妙之處,究其實,沒有一個真正壞人。
而在電影裡,有甚麼別於柔弱的人們,可以輕易跨過國界不為其所傷?諷刺地,就只有買賣軍火、造成更多傷痕的軍火商。Freddie後來在交友軟件遇上比她年長的軍火商人,他告訴她,做軍火買賣就得學會「不要看回頭」,彷彿是成人的處世之道。這句說話除了對應Freddie的尋根旅程,也說明了一個非常殘酷的政治現實。國與國的紛爭撕裂得益於軍火競賽,Freddie在電影後段曾有一段時間為軍火公司工作,彷彿又為自己的出身畫上一個無法擺脫的圓環──無處不在枷鎖中,這是Freddie的生命,也是我們的生命。
沿著傷痕辨認
不過,《回首爾後》其實也為我們提出了另一個得以跨過界線的可能,即便只是一個微小舉動。電影末段,Freddie收到孤兒院的訊息指生母終於願意見她,她問孤兒院職員為何願意幫助她在法例的規定之外繼續聯絡生母,那位職員淡然地說,可能是因為某位職員能夠理解她的感受吧。
當然,電影最後似乎暗示兩人在見面後無法繼續聯絡,為這段短暫重逢寫上一個霧般的疑惑。然而,這個短暫的瞬間,卻成為了電影裡一個魔法般的時刻,因為一個人的好意,同情和同理,法規可以被僭越,僅僅是為了另一個人的苦得以克服。就像電影中Freddie的韓國朋友Tena不斷把她用法語對韓國家人說的狠話翻譯成禮貌話,可以說她是「超譯」,維持和諧表面,但某程度上她當時可能比Freddie更懂她的情緒,更懂她其實不是真的想傷害別人。這種朝向內心的翻譯,也是一種僭越的可能。
傷痕不會綻放,但人可以沿著傷痕認出彼此,就像Freddie要父親摸她的傷疤,卻是她從父親為她彈琴的片段中,認出一種愛。《回首爾後》始於身份認同的困惑,提出的答案卻遠遠大於此。如果說電影是Freddie的成長歷程,她最後成為的不是任何國族範疇底下的自己,穿過所有朝向己身的傷害,她終究成為的,也不過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