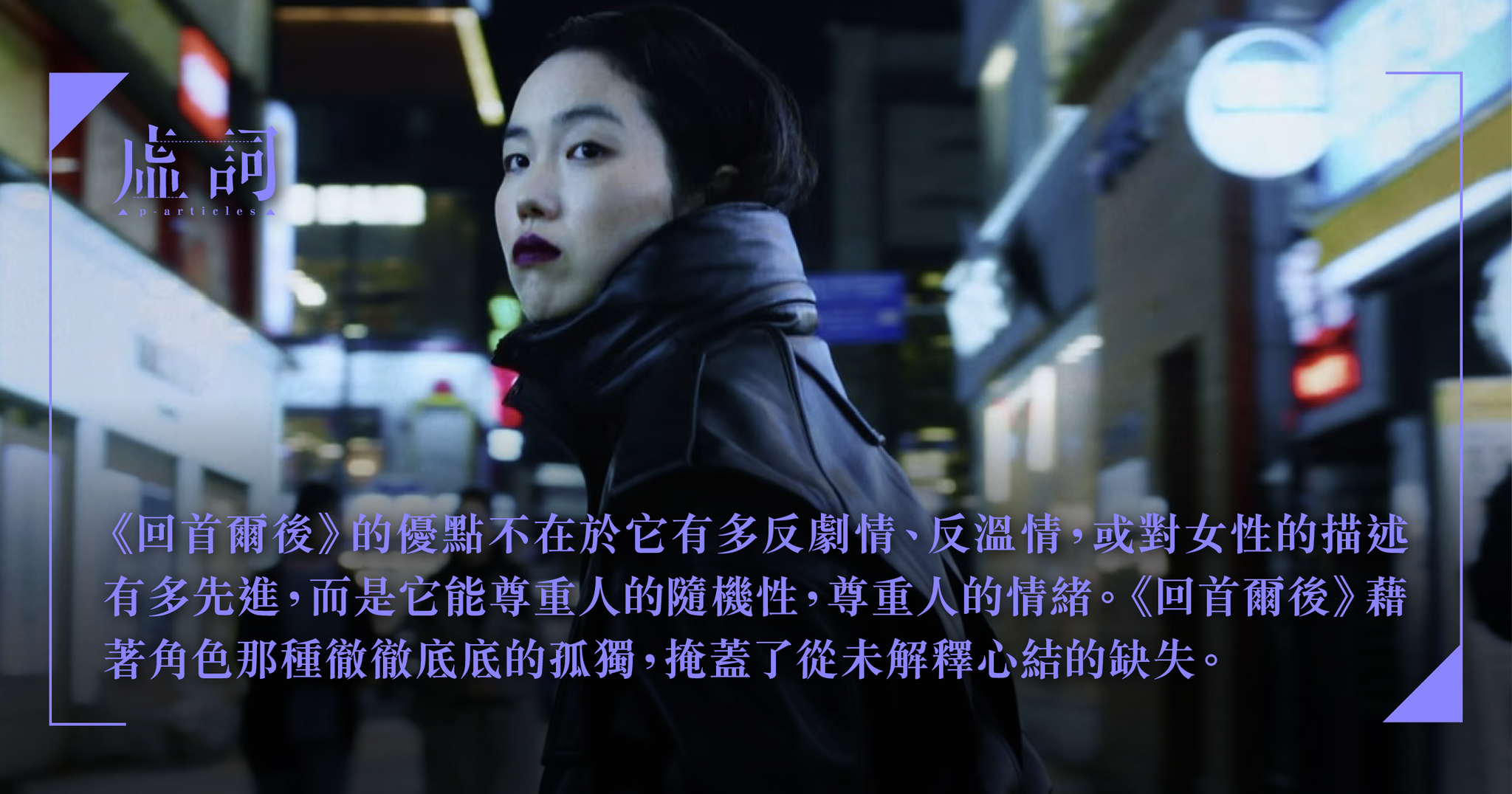《回首爾後》:如果我們一直不摘下耳機
一個韓國女生的臉部特寫。她在某旅舍的前檯,戴著耳機,聽七十年代的流行金曲,眉眼低順,短髮蓄得很整齊,皮膚白皙。另一個女生入鏡,頭髮有點毛躁,臉上沒有妝容,能明顯看到油脂,不乏自然光采。她也長了一副亞洲人臉孔,但嘴裡說的是英語,跟第一個女生寒喧,也不見外,一來便上前問:「我可以聽聽嗎?」前檯女生恭順地遞過耳機,她戴上,隨著節拍大張大放,臉上展開了一種桀驁的微笑。前檯女生又接過護照,驚喜但不失禮貌地問:「妳是從法國來的嗎?」
自從第一部Walkman於1979年面世,人們終於可以為自己的人生配樂,隨時隨地化身主角。也自此,「聽歌」成為了電影中,其中一個快速地將整個世界全盤建立在某個角色的視點上的方法。在《回首爾後》的第一幕,韓國女生把耳機交給女主角Freddie(朴智敏飾),很快便點出,接下來呈現的將是Freddie的世界。事後看來,用聽歌這種極為自我中心的活動作為開場,實在是這個視點單一的尋根故事之精神縮影。
主角Freddie小時被血親的南韓家庭送出外國,被法國夫婦領養,一直在當地生活,25歲那年誤打誤撞到了韓國,以外籍人士(expat)的身份遊走於本應是「家鄉」之地。一句韓語都不懂,卻又長得非常像「古典」韓國人(影片中角色的原話)的她,在悵然和怨恨未泯的情緒下展開尋根之旅。Freddie對自我身份的追尋與探索,以及過程中所遇到東西文化的衝突,成為了全片的兩個重點。
片中,有很多對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呈現,都典型得幾乎令人詫異。但若真要為之辯解,它們有多大程度上可以歸咎於Freddie的不覊本色,而顯得順理成章?例如Freddie在烤肉店裡一躍而起,便到處和陌生人攀談,相對之下,身邊的韓國友人顯得繃緊,卻也被很快被Freddie感染、解放;跟她一夜情的韓國男孩對她動了真心,卻只被對方視為露水情緣。後來Freddie一時性起,被意亂情迷的氣氛迅速俘擄,要輕率地親吻一直為自己到處張羅、恭敬自持的女性朋友。
這些斧鑿明顯的對比,絕對不是沒有真實性,也不一定是出發自典型。只要這是創作對Freddie本性的設計,一切便貌似說得過去。但在角色設計與典型敘事的重疊間,創作者是否一點責任都不必負上?兩者可以重疊多久而不構成延續(perpetuate)典型的問題?以創作決定(creative discretion)為依歸,是否萬能的擋箭牌?
同樣的疑問,出現在相類作品《別告訴她》(2019)。《別》中,美國華裔主角Billi(林家珍飾)因為家人決定矇騙奶奶患癌一事,舉家回到中國,以辦婚禮為名,行見奶奶最後一面之實。《別》跟《回首爾後》分別對Billi與Freddie的處理雖不完全一致,但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兩片幾乎都沒有偏離過兩位女主角的視角,要以英雄旅程(hero’s journey)去說一個集體的問題。所有對文化差異的描述,都展現於兩人對韓國、中國文化的不習慣,乃至兩者對這種不熟悉的抵抗。這種處理手法,令故事中所有的人物、環境都變成這兩個女主角處理個人情緒的敘事中的產物。我們永遠無法擺脫女主角的內在鬱結,去感受到這個地方的質地;主角所身處的文化環境是被動的,它不斷被主角的目光渲染,沒有太多為自己說話的機會。這自然不是一個問題,而是角度上的選取,談不上對錯,但它也因此錯失了很多,也解釋了為何在兩片中,處於主角「家鄉」或文化本國的本地人,總是隱約以一種令人發笑的、落後的姿態出現,以相對主角的前衛(sophisticated)。
具體來說,集中以英雄旅程的敘事,來處理文化差異,會讓作品錯過了甚麼?嚴浩導演的《似水流年》(1984),說的也是一個進步女性回鄉的故事。主角珊珊(顧美華飾)當然不如Freddie般對自己的出生地毫無認識,反而是對在家鄉汕頭的童年往事念念不忘。在香港打工二十五年後返鄉,以一副現代女性的模樣,強行插入原始山水中:她抽煙、髮型時髦、有時也不屑村代表忠叔的觀念落後,不屑童年好友孝松的憨厚與婆媽。主角及創作者對該地的理解,無一不影響著其在電影中的呈現,以及我們對它的感覺:和《回首爾後》和《別告訴她》不同,我們在《似水流年》中感受到現代化(或西方文化影響)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拉鋸,但也看到了周遭環境脫離了女主角視點後的自我呈現。
渴望現代生活但在城市卻又感受辱的強仔、從澳州回流安享晚年的孖生漢唐公、還有女主角的青梅竹馬孝松、阿珍(斯琴高娃飾)兩人的婚姻、忠叔與村事的緊密結合,都曾脫離珊珊的敘事,有過以之為主體的場面。全片雖然以珊珊為主人翁,但透過多變的視點,它讓我們感受到差異的存在不是為了凸顯差異,而是生命的多變與無常。電影要求我們理解主角,但也理解眾生,知道主角的惶惑,在當中也透見他人的命理,與更大的世界。或許這不是《回首爾後》的出發點,《回》就是要我們全程戴著女主角的耳機,沉醉在她終日無法與這個世界交流的迷失當中,在相對封閉的世界觀中,只著力認識一人。創作者的這種選擇,讓她的周遭難免淪為輔助,本能呈現的複雜性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減。也是因為這樣,片中描寫的那些差異,多多少少有些工具性的質感,終究是不能完全抹去。
如果把一切文化衝突,架在一個英雄身上體現的後果,是某程度上延續了我們對受訪之地的片面理解,是不是有必要反思這種「自我追尋之旅」大於一切(overarching)的論述?個人、私密是不是必然等於一種封閉的自我沉溺,間接簡化周遭人事的複雜性?若說這純然是種敘事選擇,世上所有奇特化(exoticizing)的視點何妨不都是一種敘事選擇?
回到電影的核心,Freddie的尋找自我之旅,雖然以怨忿與迷失為主調,但Freddie本身是積極的,並且不斷成長。在整個四部曲中,Freddie未曾停止努力適應這個無比陌生的地方,因為她渴望理解,渴望歸屬,渴望負上長著這張臉孔的責任。初次來到首爾,她絲毫沒有融入的意願,披著原生的稜角到處硬碰,無法與血親家庭舒服地相處;來到第二章,Freddie定居首爾,在這裡建設了自己的圈子(即使觀念開放的韓國人,極端地被設定為地下的音樂愛好份子和藝術家們,也許是一種典型的延續),終於找到屬於她的遊樂場,但不肯與她見面的母親始終是她的心結;第三階段,她終於能與親生父親和睦其存,能待之以寬,全片的重點卻來了——在和伴侶見完父母後回家的路途上,氣氛很輕鬆,Freddie倏地轉過頭跟伴侶說:「I could erase you from my life with the snap of a finger. (我彈指之間就能把你從我的生命中抹去。)」
突然驚醒,除了與血親家庭的羈絆,Freddie從來沒有把任何關係,從一個階段帶到另一個階段去。在四部曲之間有所連續的,只有Freddie和血親家庭。她無法跟任何人建立真正持久的關係,身邊朋友、摯愛不斷換了又換,我們從看不到她身邊的人事改變,永恆的只有Freddie和她的孤寂。到終章,Freddie在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在不知名的旅館下榻,不知道從哪裡來,不知道要往哪裡去。她已經不追尋歸屬,不深究地方,也不深究自己是誰。
Freddie的心結,始終在於不肯與她會面的親生母親。這種心結的形成,全片從未交代;在養母出現的唯一一場戲中,我們可見Freddie和養父母的關係甚好,雙方有過一起首訪南韓的約定,卻多年未起行。這必然加深了我們的疑惑——到底養父母的教育方針,或Freddie的成長經歷中,哪一個環節塑造成Freddie在戲中的模樣?但電影發展至今,我們早已放棄這種靠劇情來理解人性的執著;所謂「前因後果」不再是主宰我們感受與知覺的條件,我們今日更尊重一種獨斷的憂戚(arbitrary melancholy)。從《紐約時報》的訪問中看到(註1),被收養者所感受的憤怒與羞恥,非三言兩語能辨明,也非優渥的生活環境、善心人的援助所能驅散。《回首爾後》的優點不在於它有多反劇情、反溫情,或對女性的描述有多先進,而是它能尊重人的隨機性,尊重人的情緒。《回首爾後》藉著角色那種徹徹底底的孤獨,掩蓋了從未解釋心結的缺失。不論這點是好是壞,隨著電影的演進,以及人們對劇情理解的進化,我們早已明白,有些與生俱來、深入骨髓的東西,在銀幕上,最好是僅用一隻舞來交代。
註1:https://www.nytimes.com/2023/02/19/arts/return-to-seoul-davy-chou-laure-badufl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