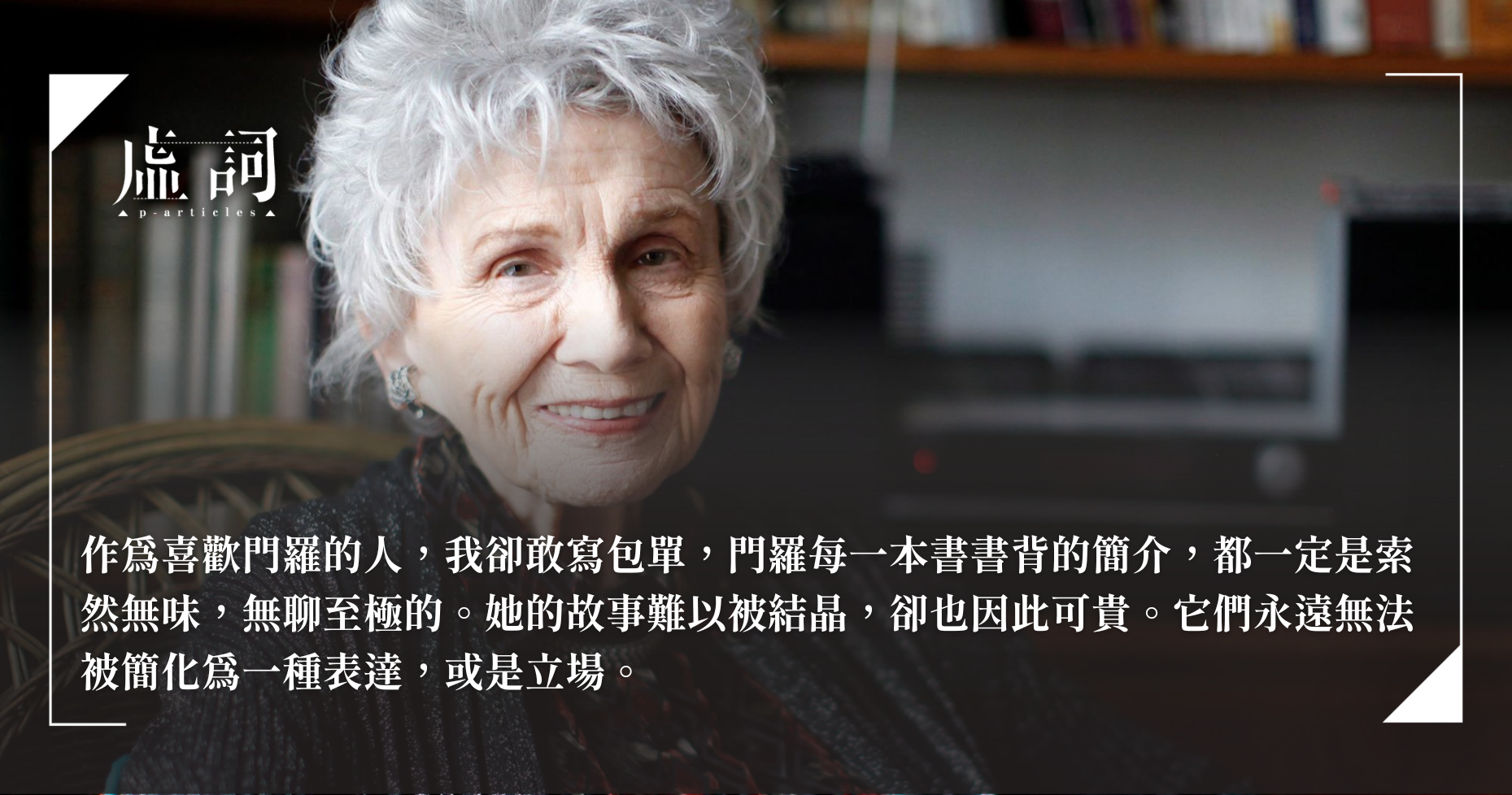不寫愛,寫一種「近乎愛」:門羅的遠近與敵意
我一度不願意承認門羅(Alice Munro)是遙遠的。
我看的第一本門羅,當屬她較為著名的短篇小說集《逃離》。看此書的時候,我覺得她是近的——這是所謂作品「成熟」時的其中一個結果和意義,即作者在自身表達和讀者需求之間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美妙平衡。在這本較晚期的著作裡,門羅的文字列車為了盡掃廣袤的人性風景,必須無懼緩慢與繞道,在一種幾乎、但最終沒有耗光讀者耐性的速度邊緣上來回試探:一個生活在馬場的女人在鄰居的協助下逃離暴戾的丈夫,卻最終選擇回到加害者身邊,這種共依附關係(codependency)的複雜性本身就是最好的劇情轉折;一個對兩性缺乏經驗卻滿腹經綸的女孩,因一段在火車邂逅而促成的婚姻,在之後的漫長歲月裡,身分經歷著無數的轉變,從女兒變成疑似第三者再變成母親,逐漸理解到自己在生活上的笨拙。門羅擅於取材最難以言喻的女性生活經驗,賦予它們一種均勻有致的形狀。
因此,我從沒想過早期的門羅會讓我感到挫敗。即使屢屢拾起《幸福陰影之舞》翻了三頁便放下,但我還是執意把它放在我床頭邊。那種描繪女性幽微處境的情狀不變,到底是什麼讓我忽然讀不下去?
我必須承認她的遙遠,了解她的遙遠,才能真正地擁抱她的書寫。
在這個年代閱讀門羅,有著多方面的困難。例如,門羅在推崇大膽私密的自我剖白、對女性主義予以基進理解的環境裡,堅持書寫內斂且內心鬱結的女人;例如,她在美加文學創作都市化為大勢所趨的時代,堅持書寫自己所熟悉的城郊小鎮,無可避免地築起了難以進入的風景;更例如,如今我們已然習慣閱讀俐落到位的書寫,她卻堅持迂迴且必不遺漏地書寫可能影響角色內心世界的一切細節,才開展故事。人們都說門羅「精準」,但這裡必須跟「精煉」做區分。門羅喜歡在故事裡包羅大量軼事的書寫方式(anecdotal),其實並不以短篇小說時常高居的「去蕪存青」為宗。她從來不介意長篇闊論地談論一小角色的身世,也意不在簡約,而在於用最低限度的篇幅,去包攬一個短篇小說不該包攬的世界。
門羅在安大略省長大,自然有不少早期作品取材於當地。但書中所呈現城鄉和都市最大的區別,並不是休倫縣(Huron County)和瓦瓦諾許湖(Lake Wawanosh)的大自然風光,而是一種詭譎地緊密的鄰里關係。鄰居對彼此的認知,或是各自的行為,竟能對彼此生活造成實質影響,這對於城市長大的我來說是全然陌生的,對在安大略省長大的門羅來說卻是日常。在《The Paris Review》的訪談中,門羅談及她曾經在北溫哥華和西溫哥華居住的經驗,十分值得咀嚼:
「北溫哥華……瀰漫著一種『非正式的一體性』(informal togetherness),我覺得很難獨處。人們經常競相談論吸塵和洗毛衣的事情,讓我感到非常煩躁。當時我只有一個孩子,我會把她放在嬰兒車裡,走很長的路來避開咖啡聚會。這比我成長的文化更加狹隘和壓抑。有很多事情是被禁止的,比如認真對待任何事情。生活被嚴密地管理成一系列被允許的娛樂活動、被允許的觀點和被允許的女性行為方式。我認為,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唯一的發洩途徑就是在聚會上與別人的丈夫調情;那是你可以感受到一些真實的東西的少數時刻,因為在我看來,在那種環境中,你能與男人有任何真實接觸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性……然後在西溫哥華,那是一個更加多樣化的郊區,而不只有年輕夫妻。我在那裡交到了很好的朋友。我們談論書籍和醜聞,像高中女生一樣什麼都能拿來亂開玩笑。」(註1)
鄉間小鎮人口疏落,但正因如此,人際網變得可以掌握,居民之間的距離反而大大拉近,彼此間的感受加倍深刻,愛恨情仇不遜都市裡的色慾男女。例如在〈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自卑但堅忍的女管家Joanna在鄉下照料某地主的孫女,在書信來往間,愛上了女孩的父親,即使他在家鄉聲名狼藉,Joanna仍不惜千里迢迢收拾所有家當赴往其所在城市,與他約定終身。不料書信是由女孩與朋友惡作劇所致,女孩父親毫不知情。書信不僅變成了兩個年輕女性在苦悶小鎮中的發洩園地,更成為憐憫或譏笑女管家兩種視角之間的角力。城鄉差別被描寫得最出彩的故事,當數〈The Progress of Love〉:主角兒時對於家母Marietta在鄉郊家中自殺不遂的驚心回憶,在席間被家母妹妹Beryl用輕鬆的語氣當笑料般道出。Beryl雖生活在城市,裝扮時髦,但感情粗糙,自以為是,空有表面上的精細。
在門羅的故事中不難讀到,她對於某種出身鄉郊卻急著要成為都市人的族群頗感不屑,而這種批判往往與女性的美麗與哀愁融為一體。然而,不屑不代表並不嚮往。在抗衡都市書寫、捍衛小人物敘事的精神背後,門羅也不忘忠於人性,勇於描寫人們脆弱、渴望被愛的一面。〈兜風〉中,路過小鎮的城市男孩,終於攻破鄉間女孩的高企心防,二人化解敵意後發生了關係,男生後揚長而去,回到城市。外表冷漠的女孩在倒後鏡中變得愈來愈渺小,最後還是忍不著揮舞手帕高呼一句「Thanks for the Ride!」(故事的原文標題),已是她用作自我防衛的冰冷面具下,竭盡可能流露的熱情。讀者不知的是,她最終是否也變成自己一度瞧不起的鄉下女孩,在每個冬天談論著她們只在夏天見過的男孩子。
忠於慾望、渴求(yearning)無疑是當代女性主義最大的命題之一。莎莉魯尼的《正常人》獲得巨大成功、安妮艾諾對身體與情慾的書寫持續被研究、米蘭達朱莉(Miranda July)最新作《All Fours》對於那種性以及「近乎性」(near-sex)的描寫也得到了廣泛讚譽(註2),甚至連《暮光之城》這類一度被認為幼稚可笑的通俗的讀物,當中所體現的女性視覺幻象都有了被理解的可能(註3)。女性無論是精神上或是肉體上的渴求,甚至是最赤裸的「horniness」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詮釋。在這樣的一個年代裡,門羅筆下的女性反而顯得疏離淡漠,熱情不足,對自身興趣缺缺。但在我看來,卻是印證了〈沉寂〉(收錄於《逃離》)中的一句話,反映出某種門羅書寫的精神:
「對Eric來說,相敬如賓至少讓彼此感覺良好,近乎愛。此刻來說,這種『近乎愛』(semblance of love)夠讓他們繼續下去,直至愛本身被重新發現為止。」 (註4)
擁有「愛」的是少數,擁有「近乎愛」的才是大多數。這是門羅透過一個又一個故事不斷闡明的深刻道理。門羅筆下的女性多長年自矜自持、做事有分寸,這種苦悶是舊時代的產物;但她們在故事中往往突然脫軌,做出自己也始料不及的事情來,這種書寫方式卻是專屬於門羅的自由。門羅最大的興趣,似乎在於描寫大部分女性在一種「近乎愛」中如何自處、斡旋。在限制裡榨取最多的幸福,這是普通人的勇氣。
在門羅成長的時代,不難想像兩性觀念保守的風氣,身邊受到父權壓迫的女性必然不少。但有趣的是,在她的故事中,女性的痛苦鮮少建立在男性的對立面,完全醜陋的男性也幾乎不存在。這並非門羅對部分女性的經歷視若無睹,而是她更重視女性之間如何互相看待、影響的複雜關係,以至於女性關係的多元性。《逃離》中野心最大的書寫,莫過於順序發展、圍繞女主人公Juliet所展開的三個短篇故事——〈機緣〉〈匆匆〉〈沉寂〉——從一趟火車之行開始,Juliet要遠赴某學校教授古典科目,在火車上拒絕了一個後來跳軌的男乘客,後又邂逅一個妻子垂死的男乘客,與之互生情愫。Juliet的笨拙與躁動,無一不顯露出她缺乏性經驗卻又渴望被愛。第二個故事裡,Juliet已與邂逅的男人結婚生子數年,如今回到娘家,審視自己對父母的感情和自己的成長。她自小被教導成為一個理智、有智慧的女人,如今也因此討厭母親的無知;她妒忌女幫工與父親的親暱,二人的曖昧關係讓她噁心,但Juliet自己又何嘗不曾參與一段「畸形」關係。透過生兒育女,她終於揭開在象牙塔裡長久的苦悶,自認為與大眾經驗接合。最後一個故事中,Juliet的女兒終於長大,卻不辭而別,投入新心靈的宗教活動,尋找自己的信仰,與堅持無神論、以清醒的知識分子自居的Juliet背道而馳。
在這個故事中,Juliet的身分歷經多次變換:先是女人,後是女兒,再來才是母親。她面對的是伴侶的前妻、自己的母親、父親愛慕的年輕女幫工,以及自己的女兒。Juliet和男性的關係都是直接而大程度上正面的,以情慾(伴侶)或是崇拜(父親)作主要的情感旋律。相反卻是生命中的這些女性,一次又一次挑戰她以「理智」作為面對世界的方式——門羅時常不諱強調女性之間一種奇妙的競爭關係,極為真實且坦誠。
我最喜愛的故事之一,〈家具〉(Family Furnishings),就是這樣一種敵意的高度展現。一場門羅式的「復仇」,揭示了城鄉、階級差異,以及女性經驗的迥異。故事以「我」和阿姨Alfrida之間長達多年的拉鋸為軸心,描寫「我」從兒時到成年後對Alfrida的態度轉變。「我」小時候還住在農場裡,家境清貧。任職某報章家庭主婦專欄主筆的Alfrida常到「我」家中作客,她談起時政起來滔滔不絕,抽起煙來自有一股風流態度,渾身散發著刻意經營的新時代女性魅力。「我」不時插話,期望得到她的認可,同時也意識到她每次都對母親辛苦準備的大餐吝嗇關注,總是把聚會變成自己的舞台。後來「我」成功考入城市裡的大學,Alfrida屢屢致電想要邀「我」到她家中一聚,「我」一直推搪,直至畢業以後,「我」成為作家,Alfrida鍥而不捨再三邀約,「我」才應允。那次聚會成為「我」心中一段無法抹滅的回憶,因為「我」終於能以成年人的目光目睹了Alfrida的窘態:她依然總是心不在焉,在「我」分享大學點滴時輪候自己發言,好炫耀自己,又對丈夫投以眼色望其注意言行、表現氣度,卻只得到平庸到近乎失禮的舉止。反觀「我」卻顯得游刃有餘,能大快朵頤,飯後極撐,在回家的路上經過藥房,進去喝一杯咖啡,聽著收音機裡正在直播的球賽,看到傍晚街道上淅淅瀝瀝的光影,「我」心裡突然變得很高興:
「我並不是在想我即將以Alfrida為藍本寫的故事,我在想我所渴望投入的工作——它類似於在空氣中抓緊某種東西,而不是建構故事。人潮的喧嘩像強勁的心跳一樣向我襲來,充滿了感傷。那些帶著莊重語氣的迷人聲浪,捲來其中遙遠、聽起來幾乎非人的附議和惋惜。
這是我所追求的。這是我該關心的。這是我希望我的人生會有的樣子。」(註5)
在Alfrida意圖低估(undermine)「我」的家庭生活經驗之後,「我」仍然能在成長的過程中尊重自己的渴求,而不屈從於一種對其他看似較「高等」的女性經驗的追隨或臨摹。困難在於,先不說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望,甚至女性主義對女性本身都有著不同的期望。能夠肯定自己的同時,不排除別人,這是「我」和Alfrida抗衡的意義。
作為喜歡門羅的人,我卻敢寫包單,門羅每一本書書背的簡介,都一定是索然無味,無聊至極的。她的故事難以被結晶,卻也因此可貴。它們永遠無法被簡化為一種表達,或是立場。門羅的文章很難被引述來理解任何當代議題,甚至無法被斷章用來說明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作者。所以很多人都說:對門羅的最高禮讚,就是去閱讀她。當她的故事就是生命,生命該如何扼要?當她總是不嫌累贅地網羅所有可能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環節,我們能看到自己的不同面向彼此緊握,以及緊握之間的縫隙。我們在她的故事裡完整,也破碎。是人,也是「近乎人」。
註(1): 原文:”In North Vancouver…There was a lot of informal togetherness, and it was hard to be alone. There was a lot of competitive talk about vacuuming and washing the woolies, and I got quite frantic. When I had only one child, I’d put her in the stroller and walk for miles to avoid the coffee parties. This was much more narrow and crushing than the culture I grew up in. So many things were forbidden—like taking anything seriously. Life was very tightly managed as a series of permitted recreations, permitted opinions, and permitted ways of being a woman. The only outlet, I thought, was flirting with other people’s husbands at parties; that was really the only time anything came up that you could feel was real, because the only contact you could have with men, that had any reality to it, seemed to me to be sexual…Then in West Vancouver, it was more fo a mixed suburb, not all young couples, and I made great friends there. We talked about books and scandal and laughed at everything like high-school girls.” 出自〈Alice Munro,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7〉,《The Paris Review》
(2):見podcast《Critics at Large》,集數〈The New Midlife Crisis〉。
(3):見Natalie Wynn在其YouTube頻道「ContraPoints」上發布名為〈Twilight〉的三小時詳盡拆析。
(4):原文:”Eric’s way of thinking, civility would restore good feeling, the semblance of love would be enough to get you on until love itself might be rediscovered.”
(5):原文:”I did not think of the story I would make about Alfrida—not of that in particular—but of the work I wanted to do, which seemed more like grabbing something out of the air than constructing stories. The cries of the crowd came to me like big heartbeats, full of sorrows. Lovely formal-sounding waves, with their distant, almost inhuman assent and lamentation.
This was what I wanted, this was what I thought I had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was how I wanted my life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