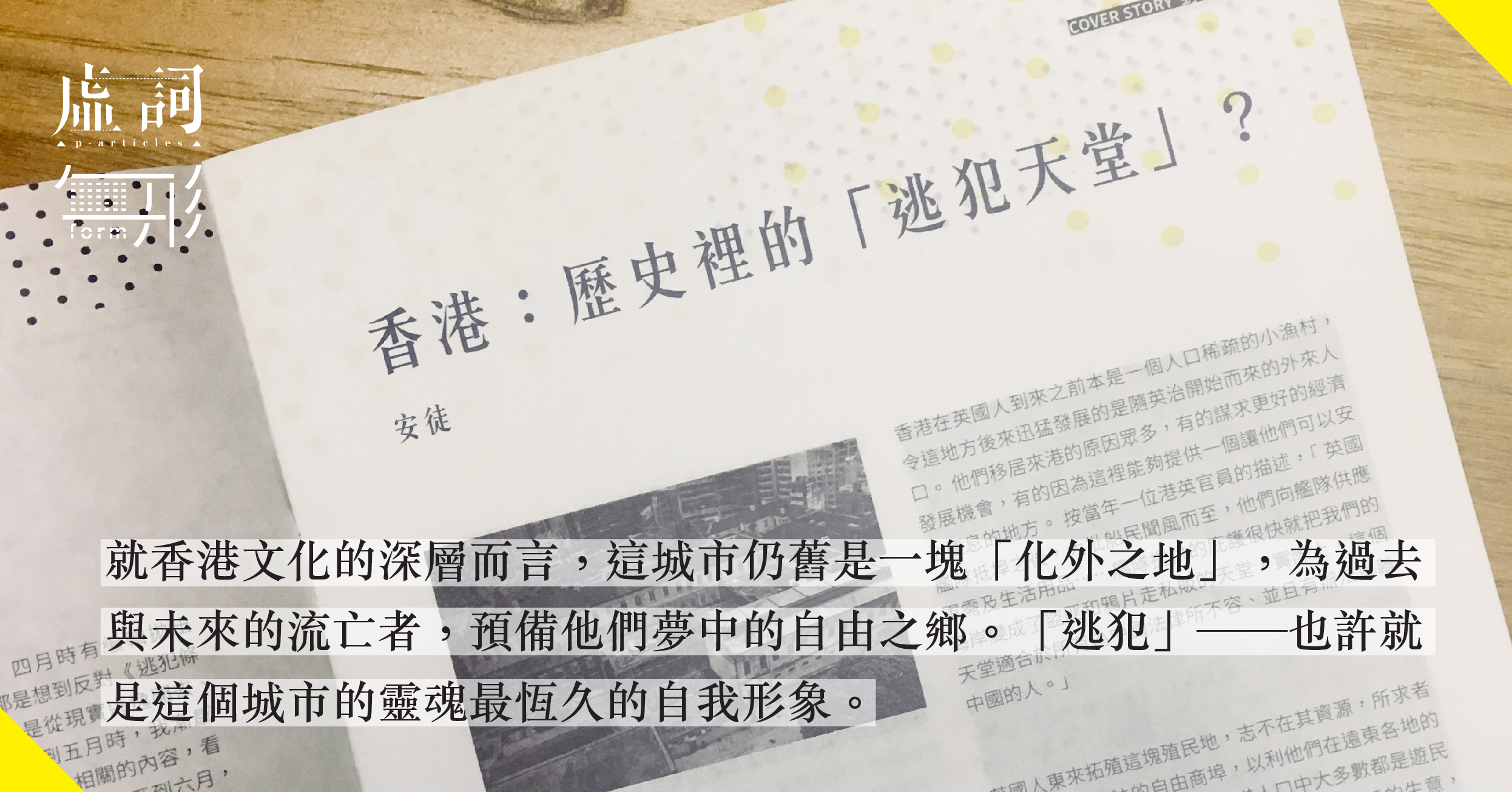【無形.逃】香港︰歷史裡的「逃犯天堂」?
散文 | by 安徒 | 2021-09-23
香港在英國人到來之前本是一個人口稀疏的小漁村,令這地方後來迅猛發展的是隨英治開始而來的外來人口。他們移居來港的原因眾多,有的謀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會,有的因為這裡能夠提供一個讓他們可以安全棲息的地方。按當年一位港英官員的描述,「英國艦隊抵埠之後,大批船民聞風而至,他們向艦隊供應軍需及生活用品……艦隊提供的庇護很快就把我們的海岸變成了盜匪和鴉片走私販的天堂,實際上,這個天堂適合於所有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
英國人東來拓殖這塊殖民地,志不在其資源,所求者乃一實行普通法的自由商埠,以利他們在遠東各地的商貿擴張。雖然,最初期香港人口中大多數都是遊民與海盜,從事一些法律和道德上都頗有問題的生意,令殖民當局要建立可靠的警政體系去維持治安都有困難,但後來終歸建立起較為完整的英式司法制度,那些「為中國法律所不容,並且有辦法逃離中國的人」(亦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逃犯」)仍然視香港為他們的自由之鄉。這些「逃犯」們不能見容於其母國,卻為香港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歷史足跡,更有不少因此播下種子,深植於本地的文化土壤之上。一部香港史不能不貫穿著各類「逃犯」的傳奇故事。
香港歷史上第一個知名的逃犯是王韜,他原是上海墨海書館的編輯,協助英國傳教士麥都士(Medhurst)把《聖經》等書籍譯成中文。1862年他被清朝官府懷疑以化名向太平天國軍隊獻議進攻上海之策,被清政府通緝。在英國駐上海領事協助之下,王韜逃到香港定居,期間協助英華書院的院長理雅各(James Legge)從事翻譯工作,將《十三經》等大量儒家經典翻譯為英文。在遊歷英法、考察西方文明之後回來,他與黃勝合資創辦《循環日報》,評論時政,大談世界大勢,倡議維新與中國變法自強之道。他的主張最後竟然受到當初向他發出通緝令的李鴻章欣賞,並邀請他回國服務。香港史家羅香林更謂,沒有王韜就沒有後來的康有為和梁啟超。我們今天或者可以說,如果沒有香港收容王韜這個逃犯,近代中國歷史就未必一樣。
康有為深受王韜變法思想影響,他在清日甲午戰爭清國失敗,被迫簽署《馬關條約》之際,聯合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向光緒皇帝請願,史稱「公車上書」。他後來更和梁啟超等共同推動「戊戌變法」(1898),但因為觸動了朝廷的既得利益,慈禧太后狠下決心要把維新計劃消滅於萌芽,軟禁光緒皇帝,追殺維新份子。康有為於是落荒而逃,成為另一名逃犯。不過,在英國官員保護之下,康有為乘船來香港避難,當時到西環碼頭迎接康有為的是香港政壇大老何東,以及當時的總警司(日後的港督)梅軒利(Henry May)。
王韜。
康有為在香港的時間不長,後來轉往日本,展開漫長的流亡生涯,主張中國建立開明專制。但他在港期間,適逢英國政府派來考察中國局勢的國會議員白雷斯福(Beresford)訪問香港,兩人曾私下會面。白氏後來出版了《中國之瓦解》一書,力主英國要向西方列強表明反對瓜分中國,但同時要迫使清政府實行「門戶開放政策」。此議受到當時香港的華商及買辦階層大力支持,並承諾他們會協助英國「將整個中華大地變成英國的勢力範圍」。有趣的是,康有為致力以變法來維護大清帝國,對買辦階層的思想並不認同,甚至頗為反感,認為他們會出賣國家利益。但他在落難之際,香港的紳商仍對這位逃犯施以援手,他們的動機雖然仍未能準確考證,但可見「香港人」在歷史上早就有包容流亡者的大度。
香港成為中國逃犯經常出入的地方,這角色直到民國革命時代仍然繼續。不過,卻很難因此而論斷香港就是一個「逃犯天堂」,因為英國殖民政府對待中國逃犯的政策其實不斷反覆。1895年孫中山與興中會同仁,首次在廣州發動反清起義失敗之後,香港政府便根據清朝廣東官府的要求,下令驅逐孫中山出境,五年內禁止在港居留。孫中山於是親函當時港英政府輔政司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逼他親自承認香港政府拒絕給予孫中山「國際政治犯」地位,是因為「有礙鄰國邦交」。當時英國下議院議員戴維德(Michael David)也看不過眼,兩度質詢英國殖民地部,因為對政治犯落井下石,未免令英國在國際間蒙羞。
其實,就算英國與清(中)國在當時的力量對比懸殊,英國也不時為了外交策略利益,順應清政府的請求,引渡逃犯或革命份子回內地。而革命組織同盟會在香港的同情者,則往往要訴諸國際公法和香港法律以阻止引渡。
例如,1907年廣東潮州黃崗起義失敗後,起義首領余既成逃往香港。廣東官府立即以刑事罪指控余既成「聚匪搶劫」,港府立即把余關押在獄。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會長馮自由立即聘請律師提出抗辯,提出多項余既成其實是革命黨領袖的證據。孫中山也親自致函港督,證實余的政治身份,反對引渡。當時孫中山的好友,也是立法局議員的何啟也出一分力,向港府申請余既成的人身保護令。當時警察裁判所雖然判了余既成無罪釋放,但廣東政府不肯罷休,狀告高等法院,纏訟多時。可幸的是,余既成最終獲得自由。
不過,香港法院也並非永遠是一個有效保護政治犯的屏障。1909年從新加坡潛回惠州發動起義的孫穩,在起義失敗後逃來香港。當時的廣東政府一樣懂得繞過「政治犯不應引渡」的障礙,改為指控孫穩犯了「搶劫罪」。同盟會為了營救他免被引渡,也替他進行了法律抗辯,可是最終失敗。港府終於把他送回廣東,隨後孫穩就遇害。這個案例活活的證明了近來香港「逃犯引渡條例修訂」的一個核心爭議點,亦即所謂「政治原因」不在可引渡之列,其實並沒有確切可靠的保障。
胡志明。
事實上,香港歷史上曾收容過的知名逃犯不僅限於來自中國內地。二十年代另一位居港的國際知名逃犯是越南的「國父」胡志明。他早年以海員身份遊歷歐美,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戰後在列強召開凡爾賽會議期間,響應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代表在法國的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提出要法國承認越南人的自決權,可是西方列強並無理會。他後來成為共產主義者,參加過黃埔軍校,也當過蘇聯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與孫中山之間的翻譯,支持過「省港大罷工」。後來他更以廣州為據點,開展抗法的反殖民運動。直至1929年,在缺席審訊的情況下被宣判死刑,一直通緝。他在逃港期間組建越南共產黨,於1931年被逮捕,關押於域多利監獄(即今日的「大館」)。
在港英政府準備把胡志明送回越南之際,當時的「共產國際」為他發起了救援行動。在英國的「反帝國主義國際聯盟」向英國政府施壓,香港律師公會主席羅士庇(Loseby)親自為胡志明辯護,為他申請了人身保護令,並要求撤銷遞解。此案一直上訴到英國樞密院,最後控辯雙方達成和解,胡志明要離開香港,但毋須指定一定要送返法國或越南。胡志明乘船到新加坡,豈料抵岸之後立即遭到遣返,後來在香港總督貝璐(Peel)的協助下離開了香港,經廈門去了上海。
事實上,蔣介石於1927年終止了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針對共產黨員進行了極為血腥的「清黨」行動之後,大量中共黨員都成了亡命天涯的逃犯。中共為了逃避白色恐怖,防備其在中國各地的據點(「蘇區」)被「圍剿」,於是積極利用香港作為在上海的黨中央與各個「蘇區」聯繫的紐帶。由1930至1933年間中共建立了以香港為中轉站的一整條地下的「紅色交通線」。不過,雖然香港成了「中共逃犯」從事「非法」地下活動最方便的地方,但沒有改變香港成為他們的「天堂」,因為港英政府一樣不時按國民政府的要求逮捕中共逃犯,一些未經法定手續就強押回廣州,另一些則由廣州方面正式來提解。中共的早期領導人蔡和森是「旅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就是在香港被捕而給遞解至廣州,最終被殺的中共最高領導人。
戰後香港的地緣政治地位隨著中國大陸政權易手而改變,政治難民和經濟難民大量湧入。香港倒是庇護過不少逃離中共政權的「逃犯」。六十年代的「大逃港」潮進一步帶來大量「非法離境」的人口,令香港社會再一次灌注入「逃犯」的血液,進一步豐富了這難民城市的流亡文化。及至1989年的中國民運及六四屠殺事件,部份香港人亦組織了營救被通緝者逃離中共追捕的「黃雀行動」,協助包括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陳一諮、蘇曉康、王軍濤等一批大概三百名學運領袖與異見份子逃離中國。
一時的「思想犯」、「政治犯」也許就是另一時的「歷史英雄」。上面談及的王韜、康有為、孫中山、余既成、孫穩、胡志明、蔡和森及今日的民運份子等,絕大部份均是香港、中國以至世界歷史裡面的正面人物或甚至是英烈之士。但他們在自己的時代,都曾經是或至今仍是「罪犯」,被(幾個不同的)「中國」或西方的政府通緝,要求引渡,因為他們都曾是或仍是「國家的敵人」。他們之間的政見或者南轅北轍,甚至互相對立,但他們都曾經在香港尋求自由,有些獲得香港為他們提供脆弱的庇護,有些則失敗了。但是沒有了他們在香港留下的足跡,中國和香港的歷史大體就會改寫,也就沒有今日大家仍然珍惜的香港。
一百七十多年以來,香港這城市最首要的價值,在於它是一塊自由之地,容納不同地方的移居者來港。也因為這裡的自由精神和法治體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讓流亡與異見者在面對強權打壓之時,提供法律上起碼的庇護和讓他們有機會尋求各種支援。最近《逃犯條例》修訂所引爆的爭議和反抗,促成了香港自主權移交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原因固然是修例的內容影響廣泛,甚至會動搖香港自治地位的基礎,令人人自危,但也在於,它觸碰到香港和香港人歷史體驗的最深處。
香港,憑藉著這裡積累了百多年的法治架構,以及尊重程序正義的文化,使她在不少歷史的關鍵時刻,成為流亡者的庇護站,雖然有時這種庇護只是很短暫和脆弱。然而就香港文化的深層而言,這城市仍舊是一塊「化外之地」,為過去與未來的流亡者,預備他們夢中的自由之鄉。「逃犯」——也許就是這個城市的靈魂最恆久的自我形象。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