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小說中不能承受之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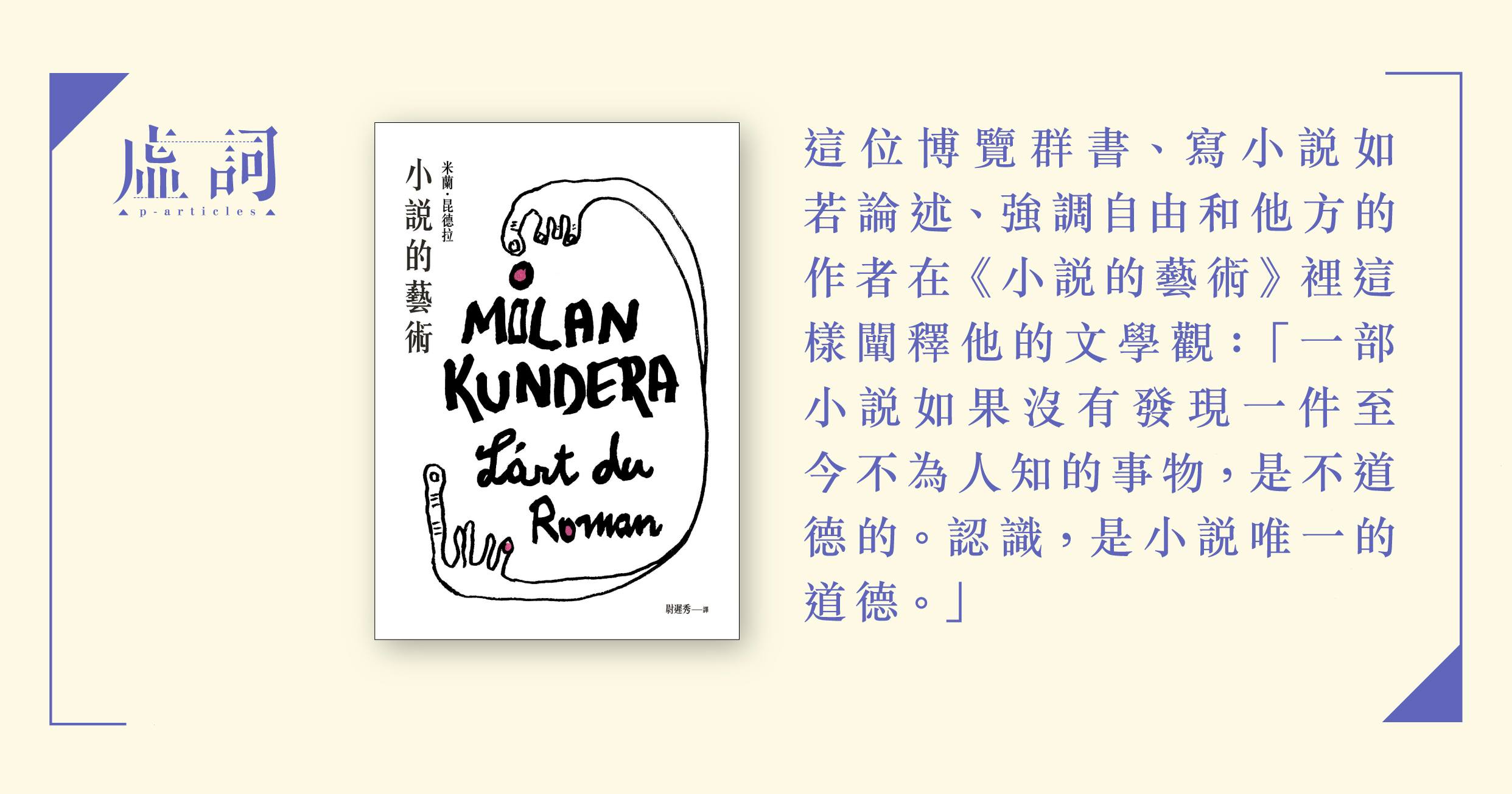
274192352_335110598567771_5077135627800725860_n.jpg
米蘭.昆德拉享負盛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劈頭就引述了一段尼采:「永劫回歸是個神秘的概念,因為這概念,尼采讓不少哲學家感到困惑。」這段描述所帶來的困惑,並不只是尼采賜予給哲學家的美好難題,更多是落在我們——小說讀者——身上。我們大概是最困惑的一群,這段引文跟小說人物的關係是甚麼?而且在此之外,昆德拉為甚麼常常採用問句?又為甚麼總是用「我們」來解釋哲學問題,我們有很熟嗎?
昆德拉的敘事風格是自成一家的,這也是他能在上世紀末獨領風騷的原因。但為甚麼是這種風格,而非其他?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要先知道昆德拉如何想像「小說」這個體裁能夠承載的事物,它的任務又是甚麼。「發現那些唯有小說才能發現的事,這是小說唯一的存在理由。」這位博覽群書、寫小說如若論述、強調自由和他方的作者在《小說的藝術》裡這樣闡釋他的文學觀:「一部小說如果沒有發現一件至今不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
在小說裡,昆德拉嘗試帶我們去認識的,大多是現代人忽視的生活狀況,比如某種懷舊心理,又或思鄉、媚俗、無解的性慾,諸如此類。而他總像個交通警察,伸手把故事截停,再插入一段哲學討論或夾敘夾議,把人物的頭擰向他的思考。「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這句武斷的話折射了一種奇異的光:如果只有認識作為小說的道德,那我們為甚麼需要小說?為甚麼是文學,而非哲學,又或其他?小說要怎樣承載認識之事?這真是個神奇的概念,因為這概念,昆德拉讓不少文學家感到困惑。
截停故事,小說中的多重時間
「文學的作用就是讓理念去實現對思想的思想。」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在〈文學在思考甚麼?〉一文裡歸納了文學最基礎的作用,在這裡,巴迪歐的文學與昆德拉的小說概念可以互通,它們都是對於思想的思想,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思考尼采的永劫回歸那樣。而這種思想在昆德拉眼中,應當要是新的、未經發現或琢磨過的,一個作者帶讀者去認識新的事物,這就是昆德拉的道德。
昆德拉所發現的東西可真不少:歷史與遺忘的鬥爭、媚俗與污穢的對立、此處和他方的角力、輕與重的互補。我相信昆德拉的忠實讀者絕對能舉出比我多十倍的例子,他的小說就像解剖,把故事麻醉暫停,將人物切開,讓尖銳的觀察灑滿一地。「其實,要說文學在說甚麼並不難。」巴迪歐指出:「文學談的是一般的人類主體,它知道他的失敗,知道他的脆弱,在此之上,它改變了聽天由命的必然性。」昆德拉的小說所談的就是人類的這些面向,在理性和客觀主導的現代社會下,這些軟弱的部份、輕的部份,讓人得以觸碰到偶然。而偶然,在昆德拉和巴迪歐眼中,都是生命裡美好而璀燦的寶藏。
對於思考的思考,就是昆德拉小說的內容。那麼,問題就在於他採用怎樣的形式呈現內容?最直觀地採用二分法來分析的話,昆德拉是講述(telling)而非描繪(showing)的大師,他會停下來中途介入,跟你分析事情,而不會呈現事情是如何發展到這個地步的。在《雅克和他的主人》這部戲劇中,沿用狄德羅概念的昆德拉甚至指出了:人物怎樣來到這裡是可以被隱去或忽略的,最重要的是,小說要去分析人物現在的狀況。
把講述和描繪對立起來的人不少,彷彿文學或電影必然要用描繪才高雅,而講述就是低手。這種說法忽略了說故事的傳統一直在強調講者和聽者之間的親密性,其次是,昆德拉想要表達的是現代人的複雜,而這種複雜恰恰好就是要強調:在一個淺薄的表象之下,人的思維必然是多向、複雜、有背景、甚至可能是非理性的。這裡就是講述進場的地方了,唯有不惜在故事進行當中伸手截停它,把時間像橡皮般拉長,仔細解釋發生甚麼事,才能比較完整地交待其中奧妙。「認識是小說唯一的道德」,為了道德,昆德拉寧願不採用高雅的描繪,也要把他的認識講得清清楚楚。
比如在《無知》這部小說,描述了一場奇異的誤會:在蘇聯入侵捷克過後,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分別流亡到了不同的國家,結婚工作落地生根。多年以後蘇聯解體,他們各自回鄉探親,並在偶然之下碰面了。他們決定開房做愛,這兩位移居外地、多年沒有講過母語的捷克人一調起情來簡直是天雷地火,講起母語髒話來更是豐滿多汁:「多麼出乎意料!多麼令人陶醉!二十年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這些捷克的髒話,他一下子就興奮了起來,彷彿他自從離開這個國家之後就沒那麼興奮似的。」
你以為接下來就是性愛描寫了嗎?當然不是!多麼出乎意料!昆德拉中途折斷了這種興奮,然後開始講述他的發現:「因為這些粗俗、骯髒、淫穢的話,只有在他的故鄉的語言裡,才能對他發揮作用,正是因為這語言,為了這語言深遠的根源,他才會湧起一代又一代、代代相傳的興奮。直到此刻,」是的,敘事者像足球旁述一樣講到此刻:「兩人竟然都還沒親吻。現在,兩人興奮異常,幾十秒鐘過後,他們就開始做愛了。」
在昆德拉的小說裡,時間是多重的,人物有人物的時間,但敘事者隨時可以把故事按停,比如讓流暢的性愛過程中止,像用手機看影片看到一半時彈出一個不得不接的電話,而人物的時間就會流向敘事者中途介入的講述。雖然是說,寫作這回事往往是從中間介入的,它比開始和結束都要有趣,但它也是個最不舒服的處境,因為原本的流動被暫停了。不過,正是這種暫停加旁述才能承載昆德拉的思考,否則,作者要怎樣才能仔細表達這對男女久未回家被口音生疏激發的情慾?昆德拉並不放心讀者可以在閱讀描繪過程後得到與他相同的結論,因此,他的描述總是在外面的,是圍繞著人物的衣服,我們從厚重的材質剪裁和洗衣標籤上認識到它的多元和複雜。
角色的意義不在此處,而在他方
「在布魯姆的腦袋裡,喬伊斯(James Joyce)放了一支麥克風。藉由內在獨白這個神奇的臥底,關於我們是甚麼,我們知道了非常多的事。可我不知道怎樣用這支麥克風。」昆德拉在說述他對於《尤利西斯》的觀感時,把自己的缺點坦白從寬:在他的小說中,外部的聲音比內部強大得多,人物的聲音總會被敘事者的聲音徹底壓垮,一如那對做愛的捷克人會被講述鄉愁的聲音蓋過一樣。
在文學史上確實有很多讓人物徹底聽話的作者,最著名的是納博科夫,他曾經講過,他驅使筆下的人物就像驅使一個農奴或者一個棋子,「如果我要我的人物過馬路,他就過馬路。我是他的主人。」這種觀點無所謂優劣,因為一篇小說確實是從作者手上生出來的,而作者有權力對自己的人物為所欲為,他只需要去考慮人物的說服力,換言之,他的人物寫不寫實。
而這種權力到了昆德拉手上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它中途就像臨檢般截停角色。就以過馬路為例好了,昆德拉會讓人物先自行走一段路,走到馬路中間時就喊停時間,開始插入議論。他會以一個問句開始,為甚麼這個角色會在過馬路時想到這些事情?然後說馬路的定義、人為甚麼要過馬路、馬路的前身是甚麼、捷克文和法文裡馬路的幾個同義詞、馬路和自由的關係、馬路現代性、馬路哲學、蘇聯開進捷克的坦克有沒有停紅燈。諸如此類。而他的人物就會停在那裡,等論述過了才能繼續行動。昆德拉的議論就是平交道上二三十車的貨運火車,截斷了一切。
這種做法有時甚至還是橫行霸道的。在《笑忘書》裡有一名角色名為塔米娜,她的整個存在都是一個比喻,用來反映一個過氣的、不合時宜的舊時代捷克人狀況。「我將為她起個絕無僅有的名字,一個從來沒人用過的名字,」昆德拉這樣寫:「這是一部關於塔米娜的小說,當塔米娜走出舞台的時候,這就是一部為塔米娜寫的小說。她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主要的聽眾。」
她所象徵的是舊時代的捷克人,於是她的故事必須落幕於與新時代的矛盾衝突中,這是小說理所當然的發展軌跡。而昆德拉寫她的方法,簡直令人嘆為觀止,因為直接寫她和新時代的衝突會過於明顯,又沒有辦法讓她在平靜的生活中好好落幕,於是他決定,要用一個詩意的結尾,要如夢一般把她從現實世界抽離。他讓她流落到一個只有小孩(下一代)的孤島上,但在此之前,她一直都是在一個寫實的世界與寫實的人物打交道的,要怎樣才能把她擄到一個虛構架空的寓言世界裡呢?於是,接下來就是我所看過「讓人物過馬路他就不得不過」式書寫最最無賴的描述了:「為甚麼塔米娜會出現在小孩的島上?為甚麼我會想像塔米娜出現在那裡呢?我不知道。」
寓言體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讀者:我是假的,是個比喻,真實的意義在他方。昆德拉的人物也時時刻刻告訴讀者,真實的意義在我們上面,在昆德拉那裡。他們都是一些棋子,任由擺佈,事做到一半可以用來證明論點了,那就停下,後來昆德拉甚至連說服讀者它是真實的都懶得做了。在《雅克和他的主人》裡,角色想到自己的造物主,也就是作者,於是他們說:「我們應該敬愛創造我們的主人;我們愛他的話,就會更快樂,更安心。」他們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昆德拉批准他們讚美自己了,用來證明真實的意義在人物之上。米蘭.昆德拉,這個多嘴的雜貨店老闆,驕傲地向你指明每件貨品的歷史和瑕疵,他的思想統治了敘事,反思就像贈品一樣分給讀者。而那些贈品本身的價值低得像免稅店送的鑰匙圈。當一個作者告訴你某個角色是主角時,就代表了,她的重要性低得需要被重點提出,而重要性全部都在敘事者鋪張揚厲的說教當中。
小說的主角是填滿的動作本身
要判斷一部小說的成就高低有許多標準,當昆德拉說到小說「唯一」的道德是認識時,是相當武斷與危險的一件事。因為除了思想以外,技術、形式、敘事、結構、對話對象等等元素綜合起來,才能形成一部好的小說。「我以為小說之失敗,不在於人物不夠生動或深刻,而在於小說無力教會我們如何適應它的規則,無力就其本身的人物和現實為讀者營造一種飢餓。」英國評論家詹姆斯.伍德指出了小說的重要核心:它有規則,而它要說服讀者投入它的世界,並且飢餓地想知道接下來發生的事。
昆德拉是能夠營造飢餓的,比如是《無知》裡那對流亡男女終於回鄉時會發生甚麼事、《笑忘書》的塔米娜到了孩子島會遭遇甚麼、《雅克和他的主人》中角色從何而來又要到哪裡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四位主角一條狗的下場等等。問題在於,昆德拉非常著重「小說唯一的道德」認識,這種是對於立體人物的狂熱,絕對反對標籤化和扁平,於是人物就像氣球一樣吹脹了。讀者被中途插入的敘事搞得暈頭轉向,像哲學家被尼采搞得困惑頭痛一樣,不只飢餓,讀者被沉重的論述搞得腰痠背痛,而昆德拉還恐怕你讀不懂地持續堆填。
到了最後,小說的主角就成了這個填滿的動作本身,這個手勢,這雙孜孜不倦無時無刻都在勤奮補貨的手。小說強調的自由和立體在這刻倒轉過來,而敘事者成了控制人物的暴君,因為他的人物除了過馬路要聽話以外,每個細胞每個毛孔都成為說教的論據,除此以外幾無價值。「整體而言,小說不過就是一個長篇的質問,沉思式的質問(質問式的沉思)是我構築所有小說的基礎。」昆德拉這樣說,而這種質問會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人物只是個論據。
到了最有名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時,這種技術更上一層樓,它除了一邊解釋一邊讓劇情推進外,甚至變得更有系統。在〈誤解的詞〉一章裡,昆德拉採用了詞典形式來解析他的人物:「如果我把薩賓娜與弗蘭茲的談話記下來,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有關他們誤解的詞匯錄。算了,就編本小小的詞典,也就夠了。」於是,他攔截了正在發展的故事,進入了他擅長的夾敘夾議中。詞典的意思是,我們可以通過查閱它來理解世界,換言之,人物再次變成了認識世界的論據和工具。
昆德拉沒有做到的事情,是放手,是讓人物自由奔跑,在他的「認識」及意義編程過後還能夠像個人(而不是切片標本)那樣活下去。他太沉重了,甚至讓人覺得他其實是不會笑的,就算笑了,他也得翻出兩種笑的意義來解釋自己為甚麼懂得笑。這個問題與昆德拉本人的創作觀息息相關,他不相信別人真的懂得他的東西,他之所以無間斷地解釋和陳述是因為覺得別人總是在誤解他(不幸的是,語言必然存在誤解)。「一次,當我問及媒體對昆德拉小說的某些評價時,他答道:『我只在乎自己的看法!』」《巴黎評論》這樣描述與昆德拉的訪談過程。在另一場對談裡,他又說:「讓一個小說人物變得生動,意謂的是對他的存在的問題意識追問到底。這意謂著:對於塑造這個人物的某些處境、某些動機,甚至某些字詞追問到底。」
這意謂著:昆德拉的小說不留白,如果留白了也是一不小心,又或無法處理(比如寫塔米娜時的「我不知道」)。昆德拉的人物無法自由行動,因為小說目標是把誤解逐出它美好的王國,是要去認識人物的一切,一切的一切,追問到底,直到他們完全喪失神秘感。他帶來飢餓、頭暈與腰痠背痛,然後我們甚至忘了人物的所思所想,因為他們沒有那支內在的麥克風,抬頭一看,像個大球場那樣環迴立體聲地放滿了昆德拉本人的喇叭,重低音把你的耳膜炸個內出血。「輕輕地請求我們相信,這使小說如此動人。」詹姆斯.伍德這樣說,而請求這個行為正正就是昆德拉有能力去營造最終卻決定不執行的,因為,這就是昆德拉那些渴求挖掘更深、認識更多的小說所不能承受之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