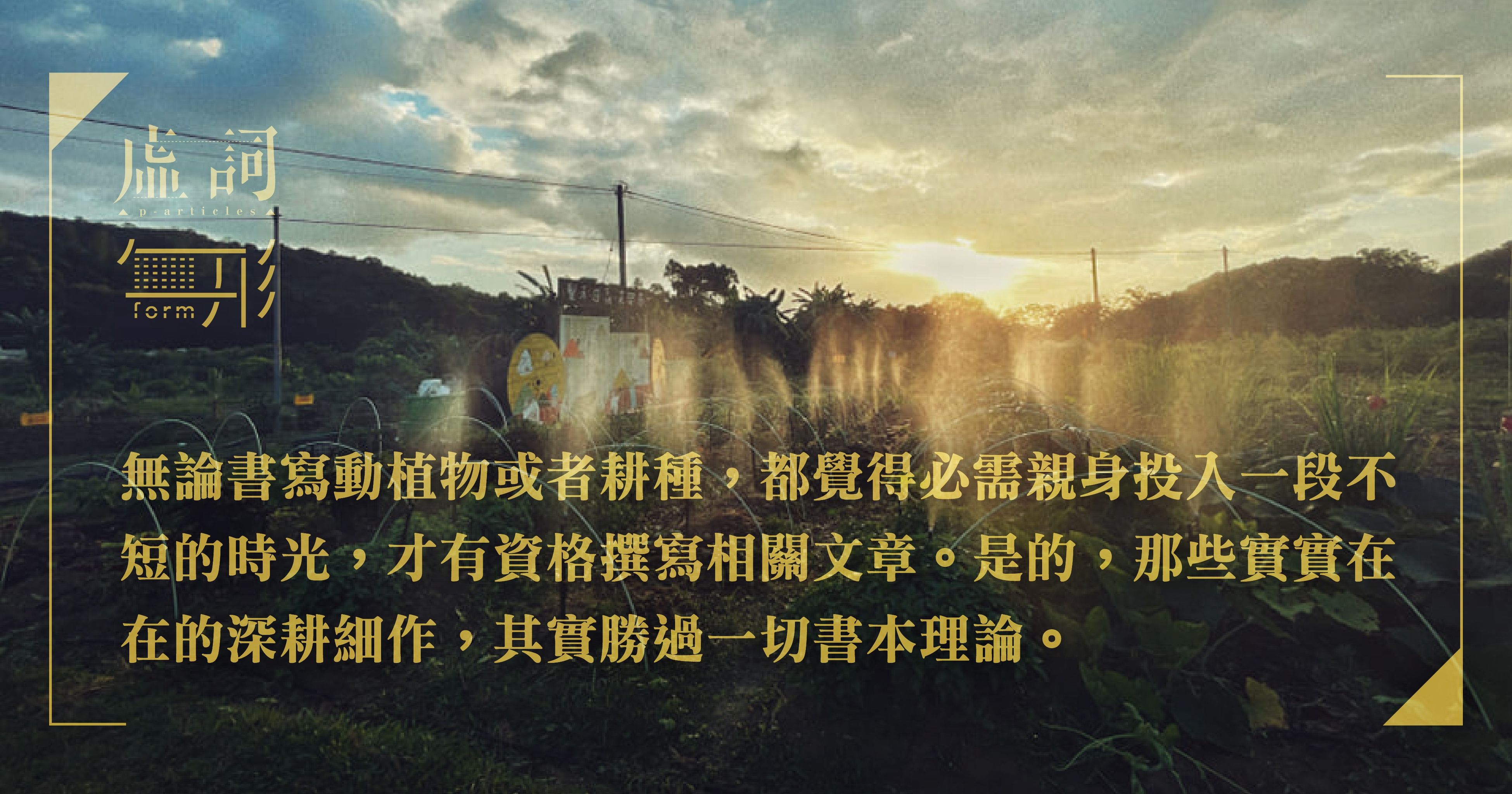【無形・共赴青山】隱山 In situ
自二零一四年出版《尋花》以來,妳與大自然的關係愈趨密切,每星期約有兩、三天窩在山中,而「在山上,下山再電聯」竟然變成一句經常掛在口邊的電話內容。妳愛上自然的質樸,頻繁地走到野外,渴望真真正正與這片大地連結。
曲水有情,石頭淨潔沉穩;多年前抑鬱受挫,當時確是自然界中那些細小柔微的花朵給予安慰,讓妳轉移視線,安頓靈魂,引領妳慢慢走過險峻的幽谷。
妳說妳多麼喜歡史耐德(Gary Snyder)的〈比幽特溪〉:
//一道花崗岩的山脊
一株樹,這就夠了
甚至一塊石,一道小溪
池泊裡一片樹皮,也夠了。//
小野花、石上青苔、根本不開花的低調蕨類,都足以讓妳賞玩半天。妳當初並不知道,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石屎森林」,竟也有原生植物二千一百多種;雖然沒有園藝植物的瑰麗,但原生植物擁有著強大生命力,更能適應本土環境及大氣候。
妳總是說:園藝植物往往僅是盆土與植物的關係,遍佈四方的原生植物卻是與整個大地互相呼應。
於是妳也特別喜歡in situ這個詞,是一個拉丁文片語,指「在原本位置」;進行in situ在地研究,人們便能發現研究對象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世世代代地,與環境及附近物種產生互相依存的親密關係。
動植物間或掙扎求存、或相依相親,種種關係令妳充滿聯想,擴闊出更多創作上的可能性。
曖昧地帶
撰寫小說《隱山之人in situ》時,妳便發現位處荒蕪「郊野」與繁榮「城市」之間,其實也有一大片曖昧地帶,正是鄉村農田。
2019年,社會最動盪的日子,妳進駐遙遠的新界東北梅子林村參與藝術活化計劃,主職為荒村房子外牆繪畫生態壁畫,希望能透過繽紛的畫作,打破這裡以往的廢墟形象。梅子林村總是散發著一股隱世村落的氣息,原因是上世紀80年代以後,原居民全數遷出,偶爾周末才有一兩戶人家回來打掃,人跡罕至,卻成為野生動物的樂園。
這的確是一段不尋常的時光,在這個紛亂的時勢,它恰好成為妳的避靜天堂。後來妳又認識兩位鄰村荔枝窩村工作的農夫,萌生合作念頭。
事實上,香港的漁農業歷史悠久,蘊藏傳統智慧及文化。魚塘、農田和濕地等多樣化生境,吸引不同種類的生物覓食及棲息。大自然透過漁農資源餵養人類,但在高度城市下,都市人往往忘記食物本源。
妳記得台灣農田詩人吳晟的詩:
//我不和你談論詩藝
不和妳談論那些糾纏不清的隱喻
請離開書房
我帶妳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看看遍處的幼苗
如何沉默地奮力生長
我不和妳談論人生
不和妳談論那些深奧玄妙的思潮
請離開書房
我帶妳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撫觸清涼的河水
如何沉默地灌溉田地//
是的,妳瞭解自己沒太多想像力,因此,無論書寫動植物或者耕種,都覺得必需親身投入一段不短的時光,才有資格撰寫相關文章。
是的,那些實實在在的深耕細作,其實勝過一切書本理論。
隱山農場 Farm In-situ
「小隱隱於野,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是中國古代的道家哲學思想。白居易說:「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隱」於「山」林的人,厭倦於繁亂的社會現實,需要置身清靜山林,以達到心中的平和境界。
荔枝窩位處香港東北一隅,背山面海,屬隱世良地。隱山農場(Farm In-situ)敲定於此地紮根。
現在,隱山之人們有塊小田,租間屋,種了些美麗花果,讓未來有了寄託與希望。再給你們一兩季時間的話,這裏將會變得更漂亮。
秋季來了,試試舉行導賞或工作坊,大概還會做些農產品吧。妳從沒有想過賺大錢,只期望延續「半農半X」的生活。
荔枝窩一帶的農業團體,在「自然管理協議」的約束下,均採用「生態友善農耕」,透過保持水土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不使用任何化學藥劑肥料、基因改造產品的耕作原則,達到與大自然共存共生。
走過清晨霧濕的田野,揚起了蝶和蛾,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生物。那些田裏的小生命,對農夫來說是降解堆肥和傳播花粉的好幫手。
下雨了。窗外的雨水淅淅瀝瀝地傾倒而下,蒼白天空堆滿了灰色烏雲,快要塌下來一樣。大氣以雨及霧的姿態,降水於陸地,水沿著地表往低谷方向下流,匯集成河,入海,最終蒸發而回歸大氣,成就一個完整的水循環。
每次降雨,表土被突如其來的雨水沖蝕,從樹林衝進溪流,令溪裡霎時充滿了森林裡的有機物,看起來污黃混濁。但這只是暫時性的,經過幾個小時,物質沉澱,水就會回復清澈如初。
通往未來的霧,《森林村落:梅子林及蛤塘永續鄉村計劃》
梅子林村的故事原來尚未結束,在新一輪的計劃中妳將擁有多重身份:壁畫策展人、文化記錄者和珍稀植物的保母。
根據正式的生態調查,在梅子林及鄰村蛤塘,發現了超過 250 種植物,其中一些被評為「罕見」。妳將會挑選合適的日子獨自踏澗而上,小心翼翼地採收珍稀植物的種子,然後帶回荔枝窩悉心栽培。
依山傍水,夾於山邊海岸之間的荔枝窩平地,房子常被隱沒在雲霧裡;在春夏季,早上的地板總是潮濕,打開門走出去,四周圍繞濃重的郊野濕氣。把種子輕輕埋在培養土中,不出七天就會萌動發芽。
田野生活與植物們
田野生活注定與植物難捨難離,妳也將逐一筆錄各種植物的故事。
樟Cinnamomum camphora:
《本草綱目》解釋了樟樹名字的由來:「其木理多文章,故謂之樟」。樹幹上紋路分明,是藥材、香料、殺蟲劑的重要原料。
木質重而硬,有強烈的樟腦香氣,味清涼,有辛辣感,防蟲防蛀、驅霉防潮,由古至今,都被視為具價值樹種。在荔枝窩有棵享負盛名的五指樟。據村民說,樟樹原本從主要樹幹分叉出五支,形同五指,故取名「五指樟」,但在日軍侵佔村落時,其中一指被鋸下,村民馬上指此樹為神樹,住有樟樹精靈,其餘四指才得以保存,避過日軍砍殺,所以我們今天只能看到殘缺的五指樟。
漆 Rhus verniciflua:
談未來的生活憧憬,不得不提「漆」。荔枝窩隱居的日子,大概能重拾荒廢數載的漆藝。
漆藝源自中國,卻在日本和越南發揚光大。天然漆是一種提煉自漆樹樹脂的塗料。漆樹 Rhus verniciflua 樹皮灰白色,常裂開,裏面具乳白色的樹脂,即「生漆」。
東漢許慎 《說文解字》云「漆」本作「桼」,「可以䰍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漆」可謂人類最早的其中一種工業塑料,不僅有黏連加固的功能,亦能耐酸、 防水、防鏽, 保護器物長久不壞,甚至可在漆中加入不同色料,繪畫花紋以美化器物。自古以來一直被廣泛應用於人類日常生活中,在新石器時代前期,中國已有人製作漆器。
莊子在《人世間》中有語:「漆可用,故割之」,是中國最早關於采割生漆的記載。事實上,莊子跟漆樹亦有段可堪賞味的故事,據《史記.老莊申韓列傳》載:「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爲漆園吏。」
「漆園吏」 專門主督「漆事」,是掌管地方漆樹種植和生漆生産的官吏,在當時只是一介小官。後來楚威王聞莊子賢德,遂派使者以千金聘請他任宰相,他不幹,反而對使者說:「子亟去,無污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要求使者「趕快離去,不要玷污了我!」莊子一生除了做過「漆園吏」,便沒有做過其它官,他生活雖然貧困, 但淡泊名利,以修道為首務,寧願在小水溝裏快樂地遊戲,也不願被國君所束縛;最後更決意終身不做官,追求絕對的精神自由,讓自己心志愉快。
荔枝 Litchi chinensis: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嶺南一帶氣候濕暖,被視為荔枝的原生地。在公元前二世紀,司馬相如之著作〈上林賦〉,記載了荔枝的原名:離枝。
離開的「離」,樹枝的「枝」,因為果實一離開樹枝,就不易保存,詩人白居易曾精妙地形容荔枝短暫而珍貴的特性:「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
荔枝木是上乘木材,材質硬重,堅韌耐用,不怕水的浸泡。木材上有波浪的花紋,還會微微反光,這讓我想起我從前居住的荔枝角,它原名為「孺地腳」,是客家話,解作兒子沙灘上的腳印。
就像小孩子沙灘上留下淺淡的腳印,又像質地易變的「離枝」,香港這城市,滄海桑田,明年今日,又會變成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