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共赴青山】Nothing more to say, No more ace to play——專訪蘇苑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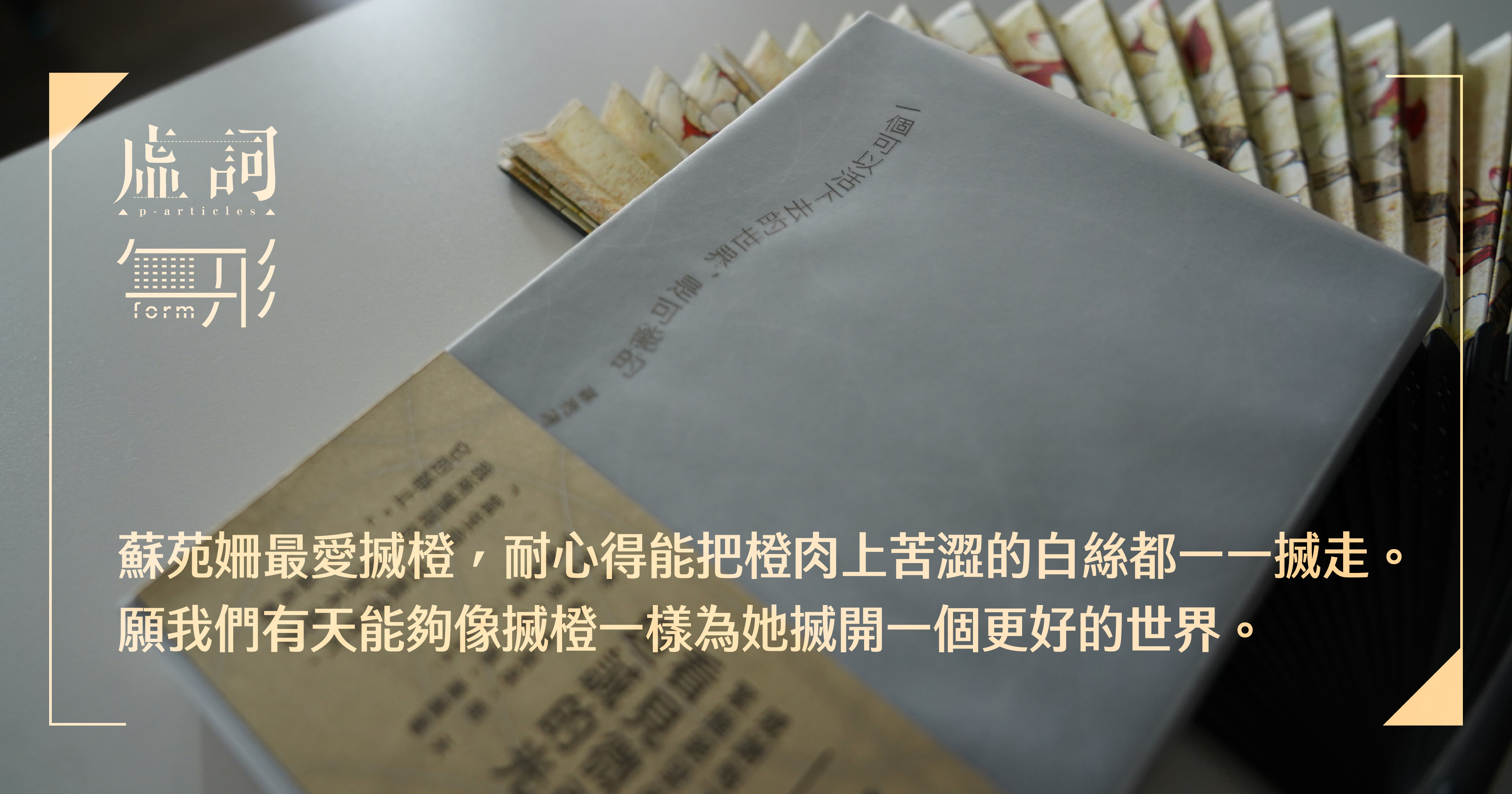
244077786_590675352290438_4094866434352034785_n.jpg
認識蘇苑姍的時候發生了一場誤會。朋友R告訴我她有一位朋友,因為患病無法工作,但文字很好而且熱愛寫作,用得著她的話都希望我們多加鼓勵。R這位朋友我一直沒有忘記,直至三年前在文學館相認,我問她的心臟現在還好嗎,她笑著說,甚麼心臟病,是血的問題。一直都是血的問題。一場誤會。連同她的新書,《一個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都是一場誤會。在每天的治療之後,蘇苑姍記錄下來的不只血淚與病榻,她最想說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的,其實是公義。關於醫療的公義,關於另一個人死亡背後的公義,以及真相。
《一》的寫作時間很長,可以憑時間追認的文字,最早是二○○四年。因為這些文字記錄,我們知道癌細胞一直跟蘇苑姍鬥強,中學發病接受治療後曾一度康復,成年以後癌細胞又悄悄跑回來,隨著血液流動全身都受影響,範圍大得連治療有時都像瞎子摸象,是,又不是。
幾年前,蘇苑姍血癌第三度復發以後,壞細胞重又出現,在重複的入院檢查抽血檢查治療檢查出院檢查模式之下,這次卻又跟以往有所不同。因為梓豪已經不在了。蘇苑姍說那是病發前一年,任職社工的男朋友被同事誣捏偷拍裙底而遭停職,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被逼辭職,但她心水清,「大家都明呢一行係點,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唔使旨意搵到工。」約一星期後警察上門調查,就在他們拍門一刻,絕望了,梓豪從寓所一躍而下,墮樓身亡。「那是二○一七年六月一日,每年一到六月我就好驚。」
我們都生活在陰溝裡
梓豪是蘇苑姍的男朋友,也是她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彼此認識二十多年,蘇苑姍清楚他的為人,由始至終她都知道而且相信,他是清白的。明查暗訪,後來發現梓豪被人誣捏一事另有內情,是公司有人要上位、減預算,因此捏造理由向他「開刀」,將他從公司逼走,更將他從世界逼走。同年九月,梓豪遭停職的機構被發現財政管理混亂,曾登上報紙新聞頭條長達一星期,理所當然地令人想到,減預算搵人開刀與財政混亂兩件事並非沒有關係。事發後,警察拿走了梓豪的電腦和電話搜證,最後當然找不到任何證據。而梓豪的朋友亦曾到過機構要求他們還梓豪一個公道,卻沒有證據證明他被誣捏。加罪者沒有證據,受冤的也沒有證據,事件就這樣不了了之,沉冤未雪。
「對世界絕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冇做過,冇力再走。他在遺書中這樣寫。」兩年前得悉香港大學法律系的免費法律諮詢計劃,在朋友的幫助及陪同下,希望透過法律途徑為梓豪奪回公義,卻被告知人死了又沒有證據,口同鼻拗,冇得打。可以做的都做過了,全都不奏效。蘇苑姍只好以自己的方法來處理。即使梓豪的名字並未常常出現在她的文字之中,但《一》的寫作源起其實是他。
「我不知道講出來有咩用,或者有沒有用,出版與否也不重要,我只知道必須寫下來,那是我唯一能為他做的事。通過自己的寫作與文字,將梓豪放進書裡,我會想像,那個他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世界,應該係點點點的。」蘇苑姍通過寫作來展現,一個(他)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二○一七年,蘇苑姍的世界比我們的更早崩塌,但也因為執著於為他尋求公義,自病情有變以來,一直成為她堅持下去的力量。
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不只一次從蘇苑姍口中聽到梓豪的故事。第一次是在沙田工作後,我們坐在巴士上層談論她的病情,經過一些景色,她說,快要六月了。然後她開始憶述那個六月飛霜的故事。慶幸當時我們坐在上層,目光穿透一切落在失焦的遠方,試圖以木然掩蓋各種情緒。這次因為《一》她又再完整地憶述四年前的往事,同樣的冤屈、同樣的傷痛、同樣的敘事,不同的是,她的語氣彷彿變輕盈了。
「二○一九年六月,香港進入漫長的黑暗,面對這樣的周遭,自身一切變得無足輕重,我的經歷或感受,那種需要說出來的內心騷動,顯得難堪地瑣碎,寫著,愈覺得慚愧,於是便收起。」《一》自序中的話,跟面前的蘇苑姍,始終如一地將自己的感受縮到最小最小,姿態如此謙卑。每次跟她談到寫書、做訪問,她總是用問題將我們打發走︰「我的書對其他人有咩用?我沒有訪問價值,我的話、我的感受對其他人有咩用?」一個人的價值高低無法以個體自身來衡量,正如她今後的人生永遠承載著兩個人的命運一樣,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似乎就是這樣難以言明的東西,誰能說得準自己對他人其實毫無意義?這大概就是她所說的,連結。尤其是在個體、社會、世界逐一分崩離析的時候,能夠有所連結,總教我們卑微地竊喜。
蘇苑姍沒有說,但我們都知道,寫作就是她跟這個世界及其自身,微小而強大的連繫。「我其實不明白『能寫』其實意味著甚麼,以至這話本身的意義,只是裡面的甚麼好像被叫醒了一下,然後有一刻,覺得再也不能不去抵抗,那一連串他所留下的問號,然後明白,艱難時,人大概是要透過蓄儲力量去安住自己,而每當我在鍵盤上反覆敲字,也總有一種深沉無名的壓力。」縱使難以易地而處,或無法理解死亡如何超越生存,反過來成為生存的意志,但經歷了過去兩年,相信我們都明白到「再也不能不去抵抗」的意志,是如何透過日常生活中各種連結,慢慢牢固,或重新蓄儲起來。
梓豪的故事,相信只是公義社會逐漸崩坍,所斷裂出的其中一塊碎片。從這角度來看,《一》未嘗不是社會崩壞的一份記錄。即使在時代面前人變得如何渺小,但公義始終是每一個時代、每一個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問蘇苑姍下一步會點走,她的方向很清晰,只是沒有任何具體的事可以做到。「你問我下一步會點走,就係盡力,所有事都盡力,做自己做到嘅事,食飯、飲水、食藥、打針、落藥,醫唔醫到、藥有冇用嗰啲,真係唔太重要。」
蘇苑姍最愛搣橙,耐心得能把橙肉上苦澀的白絲都一一搣走。願我們有天能夠像搣橙一樣為她搣開一個更好的世界。不會被絕望逼死,一個大家都可以活下去的世界,是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