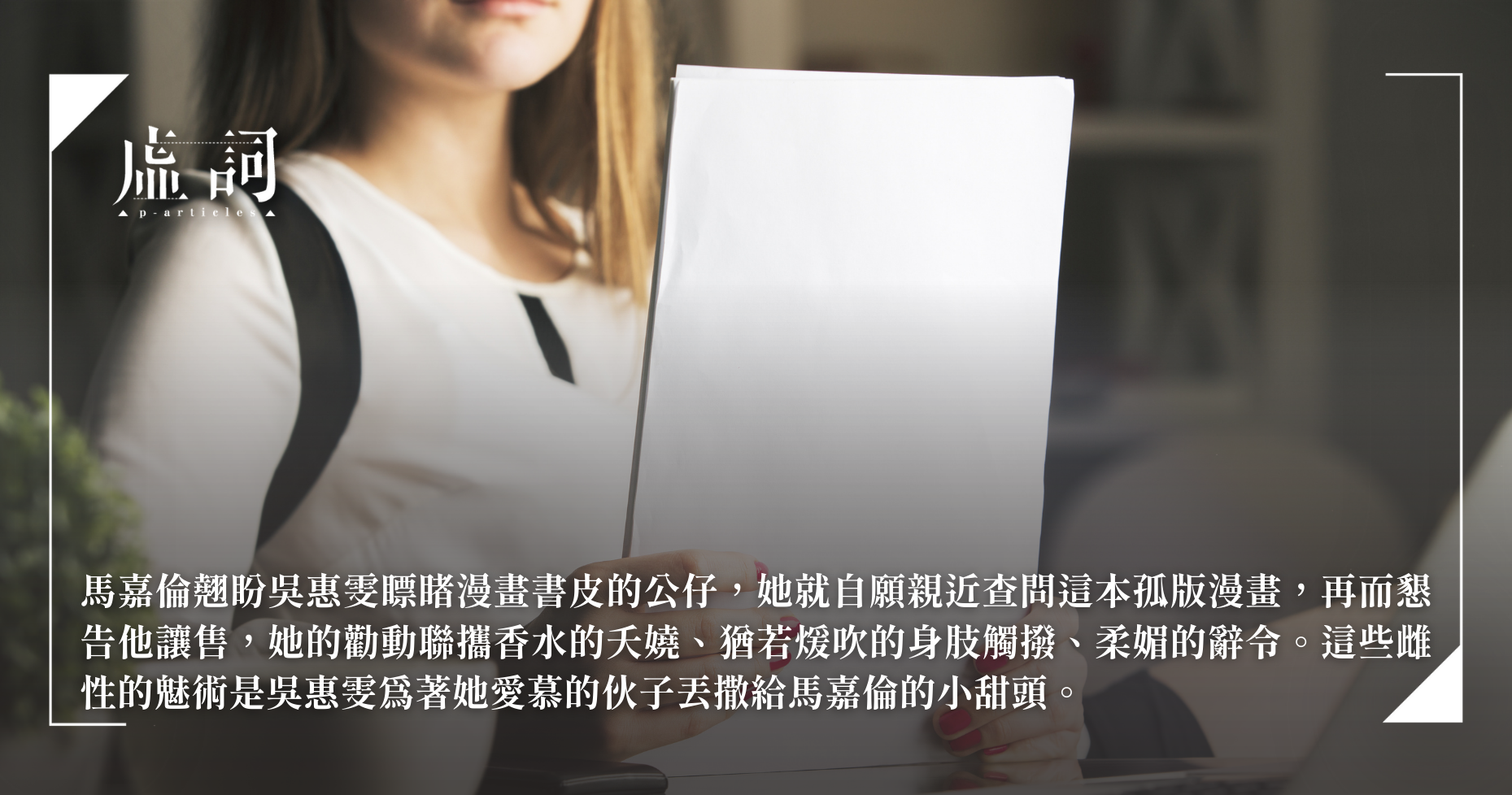藍移吧!
小說 | by 黎喜 | 2025-09-19
黎喜傳來小說,書寫對天文學充滿熱情的A,因年少時一次對「B612星球」的直率糾正,與有著特別地位的Z斷了聯繫。兩人在大學重逢後,A試圖用理性的「多普勒效應」分析情感,以「割圓術」般笨拙地靠近,卻被「牛頓第一定律」的慣性困住。他深陷情感的「拉普拉斯妖」式決定論,直到「愛因斯坦」的量子力學為他帶來轉機。 (閱讀更多)
詩三首:〈希望〉、〈蝴蝶結〉、〈你和他的位置靠近拉扯〉
詩歌 | by 潘國亨, 梁偉浩, 侯瀚 | 2025-09-20
讀詩三首。潘國亨傳來〈希望〉,首兩節透過天堂與地獄的荒誕意象,最終回歸對逝去親情的真實渴望,將希望的定義從遙遠的宗教信仰拉回至最樸素的人間情感;梁偉浩的〈蝴蝶結〉以腹中的蝴蝶隱喻一段無疾而終的愛戀,情感的消逝如同一場內在的祭奠,最終留下精緻卻又束縛身心的結;侯瀚以〈你和他的位置靠近拉扯〉一詩捕捉人際關係的疏離與矛盾,那些未說出口的話語與無法拼湊的回憶,都化為透明的光,映照著一段無聲的告別。 (閱讀更多)
當代的某些關係
小說 | by 苦橙蒿 | 2025-09-19
苦橙蒿傳來小說,書寫「我」作為一名對外貌與身分認同感到焦慮的無性戀酷兒,身處在保守的城市中感到格格不入,既厭倦了交友軟體,也對線上社群中基於觀念的激烈碰撞感到疲憊。就在放棄社交之際,他認識了短暫返鄉的之格,在對話之中讓「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被理解、接納與溫柔。 (閱讀更多)
智慧腐蛀
黃戈傳來散文,書寫自己需要拔智慧齒的「酷刑」,繼而聯想起關公刮骨療毒,以及好奇《國產凌凌漆》的「轉移視線分心大法」是否有效。雖然打了麻醉藥,且試圖以忍尿、默念文字、洗腦歌方法來分心,但最終諷刺地被牙醫電鑽的恐怖聲響所「拯救」。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