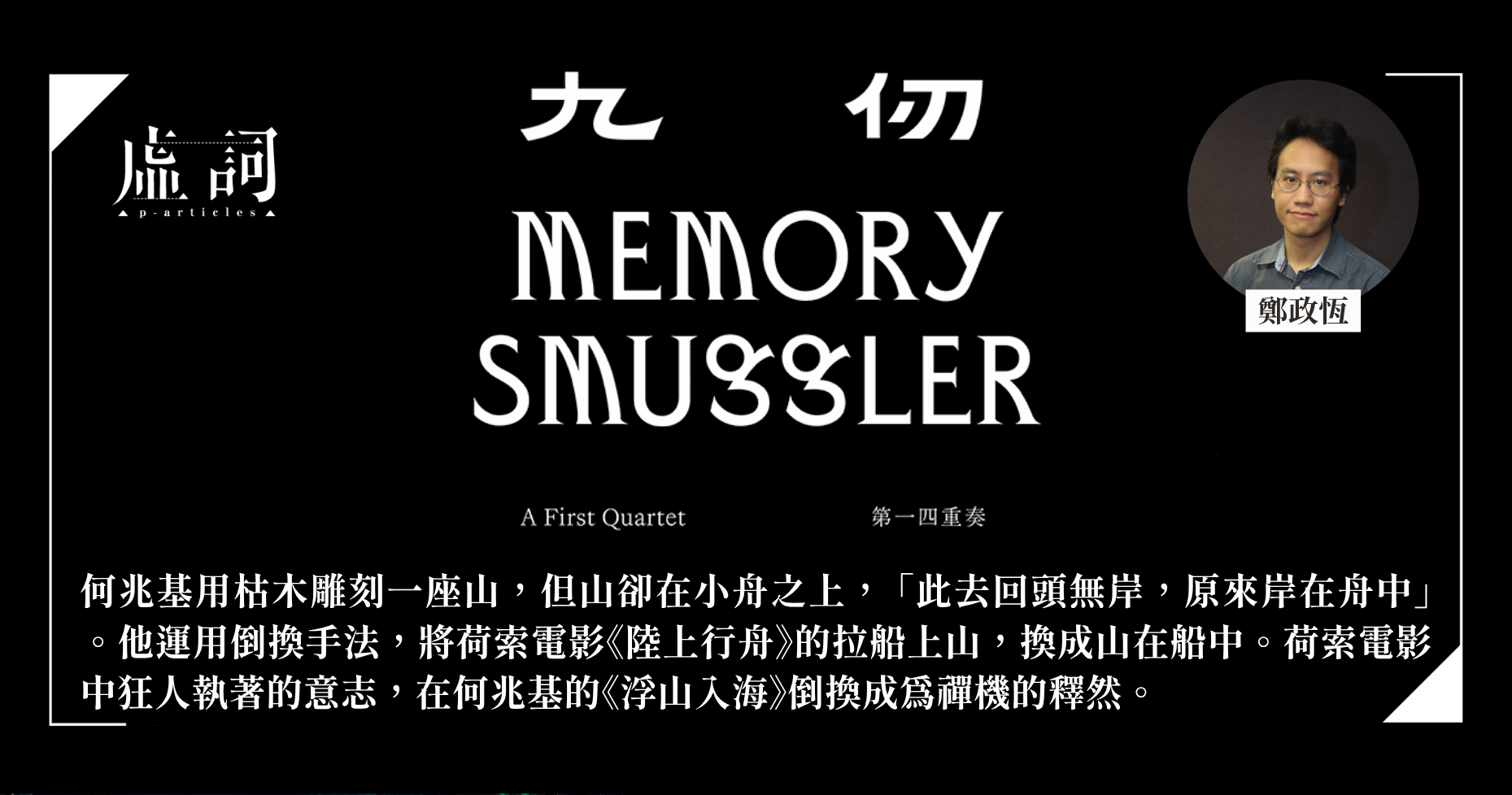火炭、山、艾略特:九仞的藝術及文學蹤跡
「九仞」是火炭嚮渡藝術空間的開幕展覽,展覽中有朱樂庭、何兆基、劉家俊及李寧的作品,他們的風格迥然不同,但在廣闊的展覽空間中,形成和諧的共存,甚至互有呼應。
展覽名曰「九仞」,令人想到典出《尚書》的「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事情就只差最後一步了,新的藝術空間經過大規模裝修,展覽卒之順利開幕,功不唐捐,定不是功虧一簣。除了《尚書》的教化,「九仞」其實令人想到山。
嚮渡藝術空間位處桂地街,靠近火炭山谷,地處邊陲,而青青的山一直向更深的山脈延展。四位藝術家或多或少以作品呼應火炭和山,大抵上,朱樂庭和劉家俊偏重於「實」的火炭地理和生活痕跡(或遺跡),何兆基及李寧則偏重於「虛」的山的種種聯想。
朱樂庭的考古式踏研,有明確的路線圖,展覽中就有她的《勘探者地圖》。朱樂庭善於運用白水泥,作品自自然然有重量感,而且成功結合負空間的失落感,以及遺物的破碎感,昔日的民間信仰和生活場景,已是一去不返。
《勘探者地圖》,朱樂庭
朱樂庭的錄像作品《看得到,抓不著》,卻著眼於輕盈的灰塵,她拍攝了廢屋與宗祠,錄像作品呼應劉以鬯《對倒》中的句子:「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著灰塵的玻璃,他會走回早已消逝的歲月。」(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也用了這一句。)《看得到,抓不著》似要穿過積著灰塵的玻璃,直視不再的昔日生活。
朱樂庭面對消逝的昔日,而劉家俊著眼轉變中的當下,而當下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也逐步進入昔日的歷史範圍。劉家俊的作品是當代火炭的現實紀錄,劉家俊的《賣磚頭》位於展覽入口,是觀眾第一個接觸的作品。《賣磚頭》展示了火炭工廈單位的租金,正所謂寸金呎土,作品在沉重中見批判。劉家俊多用木版雕刻和混凝土,好些作品離不開建築用料,而火炭也離不開地產市場。
《賣磚頭》,劉家俊
前呼後應,觀眾最後一個接觸的作品,應該是劉家俊的手造書《砼》,整個火炭的發展,在手造書的形式中有紀錄存檔,成為一頁頁歷史。
李寧的畫作和錄像都有超現實感,他並不糾纏於過去與當下,反而有未來感和虛幻感,他將山聯繫到人的鼻尖,三聯畫就以Sitting on the tip of the nose在中央,面對無邊無際的意識流,另外兩幅都有撐船者,船上都有罐子,似要運載或走私記憶,令人想到展覽名為「九仞」,也名為Memory Smuggler。李寧的三聯畫其中一幅To the Show,明顯呼應一眾藝術家和作品。
《To the Show》,李寧
關於何兆基的作品,我聽過他的導賞,講解得十分精彩,我的文章當然難以全面概括。他的作品徘徊於真和假、輕和重、內和外,也善用3D 掃描和新的AI科技,而全部都離不開山的思索,他的作品出入力學、佛學、美學、荷索電影《陸上行舟》(Fitzcarraldo),而且運用的藝術媒介也比較多樣(如寶麗來照片、木雕、表演等),何兆基似要裡裡外外窮盡山的不同面向。
《浮山入海》,何兆基
最後要略探展覽之中,艾略特(T. S. Eliot)《四重奏四首》(Four Quartets)的一些詩句運用。《四重奏四首》是艾略特關於宗教、哲理和時間的組詩。展覽中,在近入口處,朱樂庭的土地廟作品《凝固在空氣中》上,就有《四重奏四首》第二首East Coker的名句In my beginning is my end.(在我的起點就是我的終點),彷彿展覽開始於一些事物的終結,而終結就如一早命定。
在展覽的中央部分,有四位藝術家的作品,展版上書有Impossible union,另一塊展版上則有spheres of existence,分別抽取自艾略特的句子:Here the impossible union/Of spheres of existence is actual,存在的領域不可能融合,在這裏真的融合了,成為事實。而展覽中不同風格的作品,互相對話,在這裏形成巧妙的對話和融合。
最後,在何兆基的十幀AI生成圖片的寶麗來照片上下,有Fare forward, travellers一句,旅人前行,呼應何兆基的《浮山入海》。《浮山入海》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藝術家用枯木雕刻一座山,但山卻在小舟之上,「此去回頭無岸,原來岸在舟中」。何兆基運用倒換手法,將荷索電影《陸上行舟》的拉船上山,換成山在船中。荷索電影中狂人執著的意志,在何兆基的《浮山入海》倒換成為禪機的釋然。
And all shall be well and All manner of thing shall be well,一切都會變好,矛盾得以調和、組合和融合。在展覽的出口,印上了《四重奏四首》第二首East Coker的結束一句In my end is my beginning.(在我的終點就是我的起點),前呼後應,形成不休的循環往復,旅程圓滿又再開展。「九仞」展覽正是朱樂庭、何兆基、劉家俊及李寧的四重奏,他們從不同角度看火炭,也看山,而艾略特《四重奏四首》的詩句則帶來超然的提示和融會串連。「九仞」是第一四重奏,第二四重奏相信也會奏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