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落日照千山,故土而異域
教育侏羅紀 | by 陳躬芳 | 2022-08-16
今年香港科技大學(下文簡稱「科大」)進入創校三十周年。這三十周年不僅見證了學校的發展軌跡,也見證了香港社會的種種變遷。那坐落在校園廣場正中央的火紅日晷(常被稱為「火鳥」),展翅高飛如同普羅米修斯所帶來的天火般賜於人間以光明與溫暖,也象徵著智慧與文明。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座位於西貢灣畔的學府帶來了享譽國際的榮耀,也培育了無數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學子。
記得1992年第一次聽說起科大的名字。那是在中學的時期,每天早上上學會遇見上一位同棟大廈男生一起下樓。時間久了,會互相點頭道早安;後來有一天,在九月開學不久的一個早上,他帶著欣悅興奮的神情告訴我:他入讀了西貢的科技大學,是剛創立的大學。還問我:你知道這是一所怎樣的學校嗎? 我當時茫然地搖頭表示一無所知。他又告訴我:學校大部分是男生,由於剛成立,宿舍還沒弄好,故他這學期只能每天早起長途跋涉從荃威花園轉幾趟公車去西貢上學。下學期若入住宿舍,就會輕鬆點,並邀請我以後若學校開放日歡迎參觀科大。我說:我的興趣攻讀文科,對注重工科的科大不感興趣。不過作為一所懷著當時香港社會所期望的一所新式大學,著重發展科學、金融、工程等應用課程的大學,很多人還是慕名而往參觀那簇新的校舍。
想不到來到1995年的聖誕假期,學校推薦我和幾位預科同學一起參加大學首次舉行的全港中學生冬令營,提前來到科大校園體驗的校園生活。為期七天的校園體驗大學生生涯的「日與夜」活動中,我走遍了科大的每個角度,對這所嶄新的、具現代化的、正在起飛中的學校及其校園文化充滿了希望。它是直接跨越香港的傳統、守舊的社會發展而來,似是乘著火紅的飛鳥洶湧而至,把香港從過去荒島的形象,直接通過一道道教學樓作為橋樑連接了過去與未來,從古典主義的香港社會直接導向了未來的金融、科技業的現代城市面貌;經過多年的努力下,科大在世界排名一直享譽盛名。

1995年參加全港中學冬令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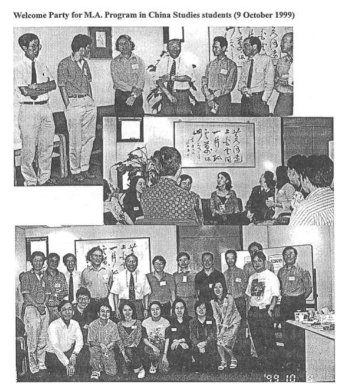
1999年的中國研究碩士課程歡迎會。
1999年,我成為了科大人文部研究生。我想不起自己報讀科大的原因,但一定是被當時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學者如丁邦新、張洪年、洪長泰等教授所吸引;或是當時的人文學部所開設性別史(童若雯教授的中國當代婦女史)、區域史(如何傑堯教授的清末民初廣州史)、華人移民史(王心陽教授的華人移民史)等抓住眼球,腦子一股熱就走上考研的路上。而今翻閱當年出版的中國研究碩士課程通訊(N0.2,November,1999)有這樣介紹的:「這是院方唯一的一個中國研究碩士課程,是文學部和社會科學部的跨部門聯繫,不單結合了兩個學部,更容許各個學科作學術交流。它的優點,正是推動科際整合,不限於過度專門的研究,使學生能挑選不同門類的科目,從而探討廣闊的知識領域。這個課程的設計著重於中國研究中的各項新發展。它的整體焦點放在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經濟、社會學及政治學上,把不同研究領域的相關點顯示出來,讓學生可以從多種觀點去看某一事物。」而我在參加完當時的歡迎會後,有感而發地回應丁邦新院長關於談談參加這個課程的感受而寫下的這樣一段話:
「偶爾靜心佇足在這充滿後現代主義的建築物裡,我以乎聞到一股志同道合的氣息,這種的感覺使我覺得不是孤軍作戰。原來在校園裡的某個角落有一群辛勤的學者們一直為中國整個歷史(Total History)的發展而努力。他們對於每位學生的各種課題都表示支持,並循循善誘地啟發學生以問題為出發點去做學問。在如此沒有人情味的校園中,卻又是如此地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也許,中國研究就是代表著中國人任重道遠的傳統,為中華文化的反思與重建,為人類歷史的重寫,凝聚了學者們的深情厚意。但願中國人不會迷失在科技追求的領域裡,並以悠久的歷史文化為定點,重現中華民族的輝煌!」
如今再讀此段話,看到當年天真簡單的自己,縱然一江春水依舊,卻是「故土」而「異域」。當時科大的本地研究生佔多數,及少數來自全國各省優秀的尖子和海外研究生;討論課題時多採用英語,輔以國語,無論大型或小聚會的討論,我們融洽無礙,沒有種族、族群、顏色、階級分野;我們會討論某個觀點而面紅耳赤,但會後我們依然是教授與學生、朋友與同學。跨學科研究方向在當時如平地一聲雷,驚醒如我般淺薄不才的年輕學子,課程重於從文學、哲學、宗教、歷史、人類學、社會、經濟及政治等多方面去進行當代中國研究,嘗試從不同的觀點與角度去歷史問題,擴闊了知識的範圍,也同時兼顧身心和人文道德。我在校園度過了五年,翻閱了圖書館內所有有關婦女史、學生運動史、近代中國革命史、廣州方志史、教育史等所有的期刊及書籍,畢業後也在圖書館內的學術論文類的架上留下了一本厚達三十萬字關於民國時期廣東地區的女性教育歷史的論文,十八年過去了,不知道有多少學人曾翻閱或徵引過這份印證了自己在科大的努力成果呢?
然而,十八年後的中國與香港,歷史的巨輪覆手翻雲而來,一切發生鉅變,我們再也無法風輕雲淡地解讀一般歷史事件。曾經以為對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足夠認識與掌握,如今在風雲變幻中卻晦暗難解,萬般詭譎。曾被視為蠻荒之地的漁村,曾被晚清遺老朱孝臧在《夜飛鵲.香港秋眺懷公度》中以悲愴而恢弘的心情紀錄這即將失去的方寸小島:
「滄波放愁地,游棹輕回。風葉亂點行杯。驚秋客枕,酒醒後,登臨倦眼開。蠻煙蕩無霽,沾天香花木,海氣樓台。冰夷漫舞,喚癡龍、直視蓬萊。多少紅桑如拱,籌筆問何年,爭割珠崖?不信秋江睡穩,摯黥身手,終古徘迴。大旗落日,照千山、劫墨成灰。又西風鶴淚,驚笳夜引,百折濤來。」
如今讀來,畢業多年的自己也如同前朝遺老般「食古不化」,與這個表面上時尚的現代化城市在近年種種變革終而漸漸沒落在一片荒涼的思緒中而回不過神。多年以後,當我審視我曾經生長的地方,我該如何呼喚你的名字呢?也許,只能像十九世紀英國詩人拜倫(George Byon)一樣「含著眼淚」望向這曾經心愛的「東方之珠」而「默默無言」!也許,也會在時間的餘燼裡,拾起你隱約的碎片,讀著早不成調的小令,執素舉哀那個遠去的時代。
一代歷史學家余英時說:「歷史上重大的『突破』,往往都有一個『崩壞』的階段為之先導」。當時代的「疏離」與「異化」不期而遇時,這就如校徽「UST」字母從富有希臘神話的光環走向含有張力或哀傷籠罩下的UST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ars 或university of suicide and tears)的自我嘲諷,如斯景況,校友們的關切之心如懸在刀刃上,看過學弟學妹們的激昂陳詞以及史維校長難忍深情的垂淚,當讀到校長發給校友的信件中,彷彿在理性與感性之間選擇、遊離在冷峻與仁義之間悲鳴、神傷在離別與展望之間流連,或許這裏並不存在二元的抉擇,只有我們懐緬著那漸漸遠去科大人美好而浪漫的人文傳統。走過炫目光線穿透天花的ATRIUM(賽馬會大堂),時間的長廊見證了熙來人往的畢業生;從露臺上眺望遠處的西貢海灣,遙想當年入學時年輕懵懂的自己,遇見了談笑風生的教授們,在研究生辦公室邊忙活邊吵鬧的同學們,當時的時光也似乎只能通過「穿越」才能再次感受到人文學部的學者們那種無比寬容的胸襟及艱苦耐勞的做學問態度。那一片絢爛的落日與身後的火紅時間之輪依然守護著校園的科研與人文精神,為工科為主的校園注入了人文的道德內涵,但願「黃昏日落」沒有降臨這座典雅而現代的校園……
人生總是令人意想不到呀!人文學部正式創立二十五年後的七月三十日,我們重聚了!這是一個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炎熱的盛夏!我們人文學部老師、舊生在「相聚離開總是無常,疫下相聚更是難得,此後再聚也是遙遙無期」的呼喚下,大家一呼百應相約齊聚在校園廣場正中央的火紅日晷旁。那依然一身火紅昂然高飛的火鳥,卻如同城中自二十五年以來首次在七月雄赳赳地到處掛滿了紅色而張牙舞爪、迎風飄揚的旗幟一樣「奪目耀眼」。多年來,從未碰面的老師與同學遽然乍現眼前,想起了已逝去的青春,那是個讓人激動澎湃,不悔的時代。想起了,同時也是一個讓人感動憂愁,遠去的時光!原來歲月神偷不知不覺中已經偷走了我們的青春,我們不再年輕的面容似乎依稀還是當年的那個模樣,卻不再是那個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的香港人了。當那把無情的光陰利箭穿透獅子山下無數寓居於此的「本地人」(那殖民地港督口中的Punti),也涼透了自命不凡拜金主義至上的「遺民」或那2019年盛夏在街上亂闖的「蟻民」或即將向全世界散去的「移民」。
或許,回到1884年的夏天,同樣炎熱的七月,十八歲的孫中山來到香港入讀了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在這裡他反思中國的現狀,對英殖民的印象深刻,概嘆西方制度之餘,「奇想英人能把像香港這樣荒蕪之地改變」,故痛惜中國的落伍,興起改革之意。1895年殖民地部檔案編號一二九卷二七一的有關乙末廣州起義詳細記錄了當時香港警局全面圍城追捕四百位革命勇士的情形,成為回憶清末時期的香港歷史上最生動的圍城印記。當孫中山在三十年後(1923年)來到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紮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因此作此結論:「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註1)。歷史發展的軌跡總是何等相似呀!科大呼應1997年的回歸應運而生,人文學部在1993年開始草擬籌辦,陸續在1997年收生,逐漸開展校務,教授們拚著時間把科大推向國際的視野,這樣三十年過去了。2022年初夏,科大第二分校在廣州宣布籌建,想必另一批的學者終將科大面向大彎區一體化的方向,在未來的日子逐漸開展了,而我們該老了不像樣了!

2022年7月30日,我們相聚在火鳥邊上。
在這個仲夏之夜,在這短短的四個小時聚會當中,往昔的師生情誼讓我們迅速地回到了那個談笑風生的光影裡,彼此訴說著二十五年來的個人發展與前路。當學部老師陳榮開教授帶著全場師生合唱三次李叔同的《送別》向剛故去的張灝教授—一代歷史思想家表達緬懷之情時,一種感嘆知交一半零落如塵土、一半離散在天涯的悲傷瀰漫著校園,我們似乎重複著國人在近代中國大時代中顛沛流離的命運,和應著歷史的迴音壁上「念念不忘,必有迴響」的初心—人文關懷的堅持。當洪長泰老師深情地回顧著當初從美國應丁邦新院長之邀回到他小時候的移居之地—香港以及創建人文學部之初,一時多少故交相知雲集於此授業,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遙想當年科大師生融洽相處,互助互勉,學部充滿了讀書聲和笑聲,那段日子最令人緬懷。」誠然地,這就是當時人文學科師生協奏出的一種濃厚的人文校園氣息!在這大時代的重疊光影中,委婉而幽幽的歌聲加上喃喃的低語像是為往日消逝的時光而「招魂」,在晚風輕佛的清水灣畔暫時溫暖那漸已荒涼的黃霑筆下的「海角天邊」。

科大校園的火紅日晷。
曾記得,那西貢海上的落日也曾牽引著李歐梵教授預言式的、具現代性的文學想像—《清水灣畔的臆語》,寫下了SARS(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相同)時的「圍城」景象。爾今重讀,一片觸目而驚心:「幾個世紀的進步發展有把我們的文明改變成甚麼樣子了?為了面對個人對人類前途的悲觀,我覺得更要學習卡繆(Albert Camus)的勇氣—不是愚人之勇氣或空泛的自信,而是在災難中反思後的存在勇氣。」事實上,在關於香港嘈雜描述中,過往的倉促間建立起的城市面貌卻劫墨如灰,煙消雲散在一道道來自北方的狼吼聲中。過去和現在的「圍城」,讓我們在瘟疫日復一日的枯燥生活中失去了某些記憶,變成了卡夫卡小說《變形記》中的那隻甲蟲;在吟罷低眉無寫處的時候,也只有笨拙、絮絮叨叨地、低聲吟唱著羅大佑的「守著滄海桑田的諾言」,如若一個失去家園的怨婦般在哀悼!
據神話的記載中,普羅米修斯在失去自由的同時,也昭示了人可以借助自我超越的自由不斷向宙斯的專制神權發出挑戰;同樣宙斯所送贈的「潘朵拉盒子」也是充滿了邪惡與災難,唯有「希望」我們終將得到救贖。憐憫與愛、自由與希望,讓我們即使足纏腳鐐、遭致懲罰下仍然舉步向前。苦難與眼淚、自由與幸福就像雙生兒般互相緊扣。然而我們校園的火鳥還在,人文道德的情操也依然是我們不忘的堅持—「循此苦旅,以達星辰」(Per aspera ad astra),是永恆不變的追求!
寫於清水灣畔,2022年7月30日
〈編者按:此文據科大三十周年特刊徵稿而修訂〉
註1:《華字日報》,(1923年2月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