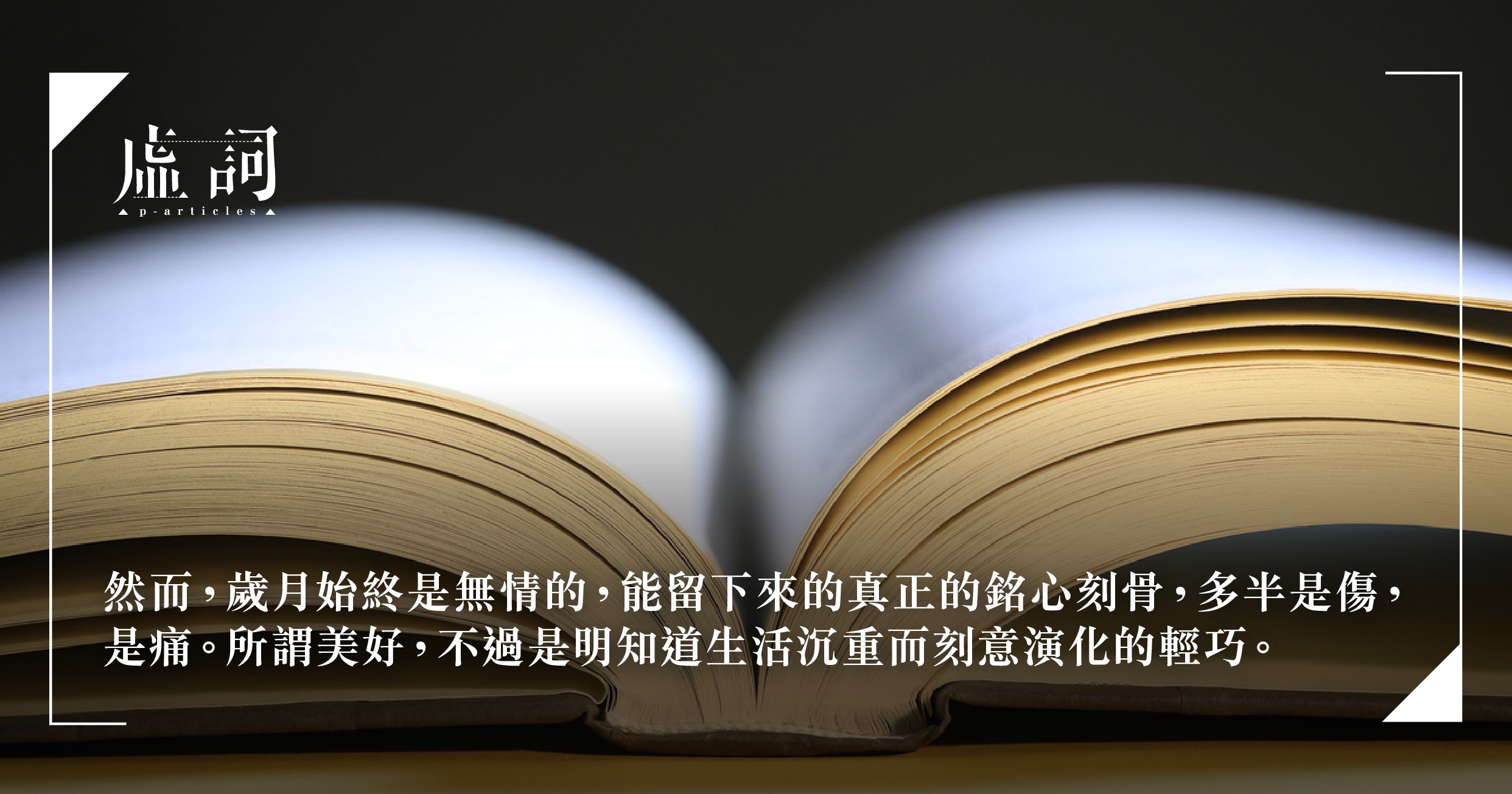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碎
教育侏羅紀 | by 游欣妮 | 2022-08-30
那個下午,她獨個在新居撕毀一堆老相片、舊文件。
終於可以離開校園,可以撤離舊居,原來數年以來朝朝暮暮冀盼的這刻臨到時,並無什麼特別感覺,更沒有她想像中的輕省放鬆。
拿着剪刀把相片中的人像剪去的時候,起初是一種非常機動似的模式,無甚大感覺,只是生硬地不停重覆同一個動作,沒有任何情緒可言。本來為了省工夫省時間,她曾有過只剪去自己的身影的念頭,反正其他人面、風景,不知何時開始於她已毫不重要了。到得剪了大半,才又想到,這好像不太好,誰願意在垃圾堆裡看到自己的臉呢?即使當事人會在垃圾箱裡翻出自己的機會微乎其微,然而將心比己,還是有點良心不安。
於是,又只得花了不少氣力和精神,在廢紙舊物堆中翻掏,挖出被粉碎的缺角相片,在各式面孔上不規則地剪幾刀,或逐一撕成錯落、崩裂的拼圖。同窗的臉、同工的臉、學生的臉……不同的臉混在一起,拌勻了她漫長的過去。如果有碎紙機,她會把相片一張一張放進去快速地碎「撕」萬段,千刀萬剮嗎?她不敢肯定,或許會的,至少乾脆俐落,爽快一點,不必消耗過多精神來做些意義不大的事,人生無意義的事已夠多了,沒必要再添一樁。
照片堆中大部分是中學時期的校園照片、活動照片,也有大學時期的生活照片,職場上的照片不多,都是典禮或宴會後的留影,有些黏附在一起的照片,強行撕開時那「嘶喇」之聲,損毀了人面,也割破了往昔。剪着剪着,她發現了自己的畢業照片,大抵是收拾時弄亂了,這張照片應該歸為與家庭照同類,家庭照都在父母的老家。想來也是時候回去走一趟了,畢竟已數月未見兩老。
除了照片,還有積累了多年的筆記--如果以歷史最悠久的一份計算,再多兩年它們就要有五十載資歷了。這一筆一劃,全是她長久以來的勞動成果以及教學經驗的顯證……因為沒有妥善儲存的緣故,大部分已隨年月褪色、脆化,凝視眼前一堆雜亂的出土文物,她疑惑,從前曾經覺得這些人,這些時光無比重要,無論處事為人的態度,或是選擇投身教育行業,都被他們深刻影響過,怎麼後來印象會變得那般模糊,一切感受都變得那麽輕巧,像是尋常得無所謂不能丟棄或割捨的記憶或關係?甚至到了近年,更覺得非要與它們劃清界線不可?她沒有失憶,部分舊日片斷仍鮮活如昔,只是感覺已經相當薄弱了,薄弱得連要丟棄都沒有半點不捨或眷戀,到底這中間經歷了怎樣的轉化過程,才可以將珍視過的完全放輕?或是從前不過是誤以為自己非常珍惜,其實用情並沒想像中那般深厚?
一室空盪盪,使得撕紙的聲音份外清脆,為何這些繁雜瑣碎的負累會隨其他家具行李一併遷入新居?搬屋師傅登門,呆在原地的她看着師傅們專業俐落地入箱、封箱:「呢啲統統都要呀嘛?」剎那間不懂應答。「搬埋過去先慢慢執啦!」當時是誰爽快地替她做了決定呢?
當撕成幾截的紙片堆成小丘,她忽然想起初中時期的一位中學老師。他扔過她們班上許多物品,報紙、小說、各科習作……有時甚至會把這些東西撕碎,起勁地撕個稀爛而面不改容。同學都對這位老師必恭必敬,誠惶誠恐,只為了保存在抽屜裡傳閱的盛載大家對未來無限憧憬的愛情小說;或是勤懇辛勞完成的功課,當然還有永遠傳不完的「紙仔」……
「我唔會容許同我嗰科無關嘅嘢出現喺我視線範圍之內。」數年前再次聽到這句話,自同工口中吐出,她已成為老師近三十載,頓覺如此熟悉,更覺這種想法的不可一世。當時,她仍有心思力氣去提點「晚輩」,甚至據理力爭,然而,在現實的茫茫汪洋裡勉力游移,一層又一層的後浪掀起,重重拍擊着她,提醒她無謂的堅持早已不合時宜。
與其成為被人嫌棄,不如盡快淘汰自己。
雖說不上落荒而逃,但當可以正式退休時,她是急於離場、急於擺脫這數十年的過去的。回首前塵,不論求學抑或工作,她都自覺失敗的,不是因為沒有目標和方向,只是一切發展都沒有如她所想,即使每天的機械式生活未磨蝕她有過的熱情,惟人事足以叫她心灰意冷。
舊日老時光真的特別美好,特別教人陶醉嗎?事實或許未盡然,不一定因為從前過的是苦日子,所以不堪回首,反倒是因為年月漸長,訝然於舊日輕狂,輕易對人對事上心動情動氣,才會覺得一切感覺都特別深刻,特別有份量。然而,歲月始終是無情的,能留下來的真正的銘心刻骨,多半是傷,是痛。所謂美好,不過是明知道生活沉重而刻意演化的輕巧。
誠如醫師所言,這輩子到最後能陪伴她度過餘生的,只有積勞而成的,慢慢佔據她皮囊的豐足痛症和毛病,而剩下的日子可長可短,如果可以,是時候放開、擺脫,盡力過些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