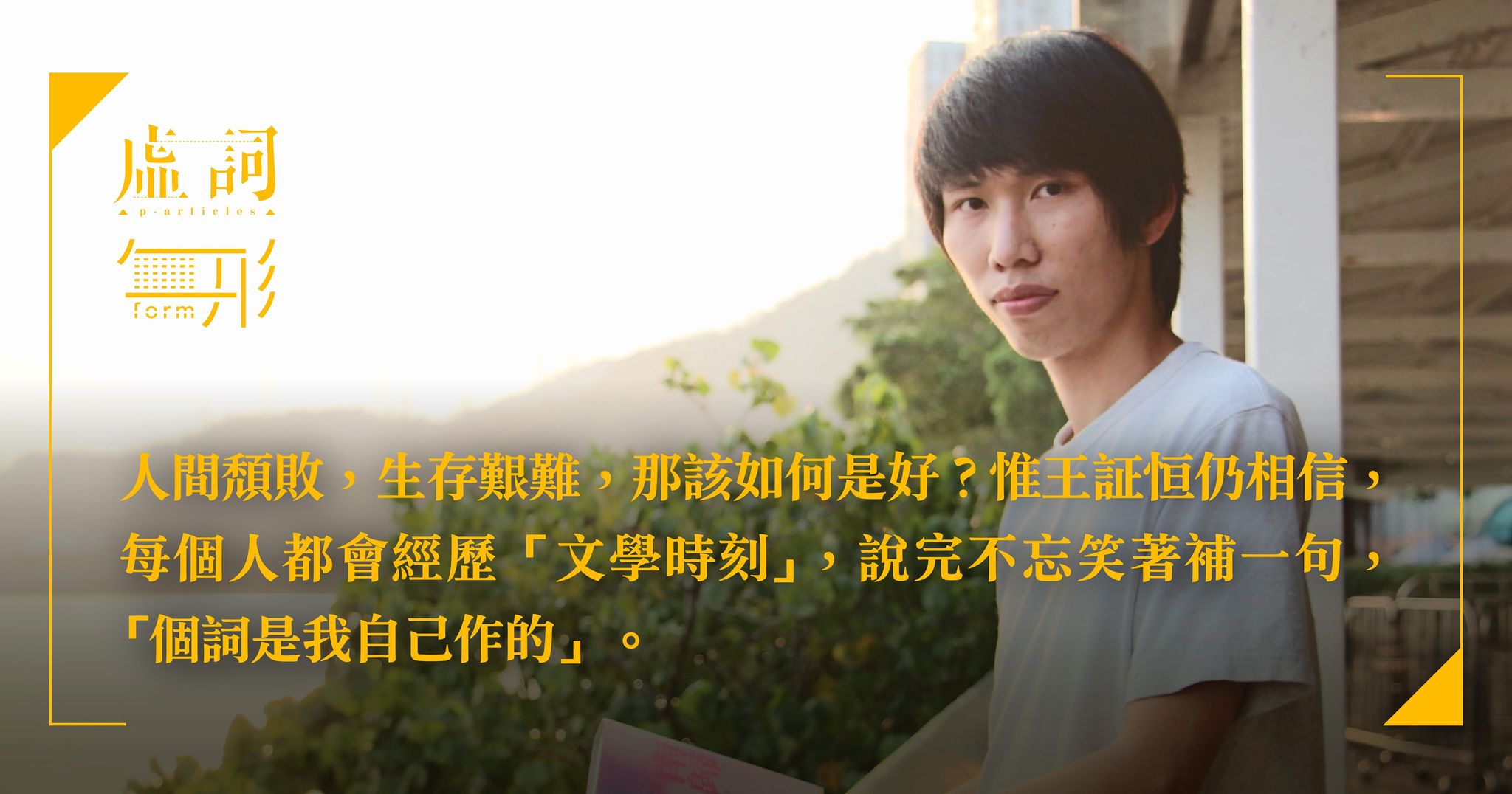一場「感覺很安全」的網絡緣分,造就「感覺很自由」的唱作組合石山街
Marstn一針見血地回答,「可能很多人會覺得我們的音樂風格很獨特,但我們又沒有這樣想,主流與否是由觀眾決定,若聽眾覺得我們的歌曲是流行曲,那就是了。」楊彤補充,「外國很多流行音樂都很『獨特』,如Billie Eilish就不會用一些major chord作曲。我不想特別把音樂區分,其實任何一種類型的音樂,都可以是大家日常會聽的音樂,我甚至希望大家有天會認為,石山街也是主流音樂。」 (閱讀更多)
【無形.初登無形也不驚】無限接近實的幻——專訪謝曉虹《無遮鬼》
從去年的長篇小說《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到今年的《無遮鬼》,私密流瀉出街道上,謝曉虹認為已不僅是對自己的交代,而是想聽一下別人怎麼看這件事。像拿起電話說「喂喂」。「其實『喂喂』是沒有意思的,你不是想要表達什麼,你是想知道有那個人還在,他還在你身邊。我其實出這本書其實有頗強烈的感覺是這樣,想表示,我也在這裡。」 (閱讀更多)
【無形.Comfort Food】 「我的理想是平靜的生活」——筆訪杜杜《飲食魔幻錄》《甜美的悠閒》
專訪 | by 無形編輯部 | 2021-05-25
筆耕逾半世紀,文字輕盈通達的杜杜,在筆訪談及去年再度復刻出版的《飲食魔幻錄》以及新書《甜美的悠閒》。在他的生命過程裡,痛苦和快樂皆有,但最終理想還是過平靜的生活。如杜杜所言,即使時代再壞,快樂仍是很簡單。 (閱讀更多)
從一人雜誌談到新馬文學生態——筆訪《Seal》總編輯牛油小生
來自新馬的作家牛油小生,因為眼見馬來西亞的文藝空間被壓縮,才冒出辦文藝雜誌的念頭。他一人製作文藝誌《Seal》,雖然盛載的內容不算多,但也不失為一個新嘗試,令更多讀者接觸文學。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