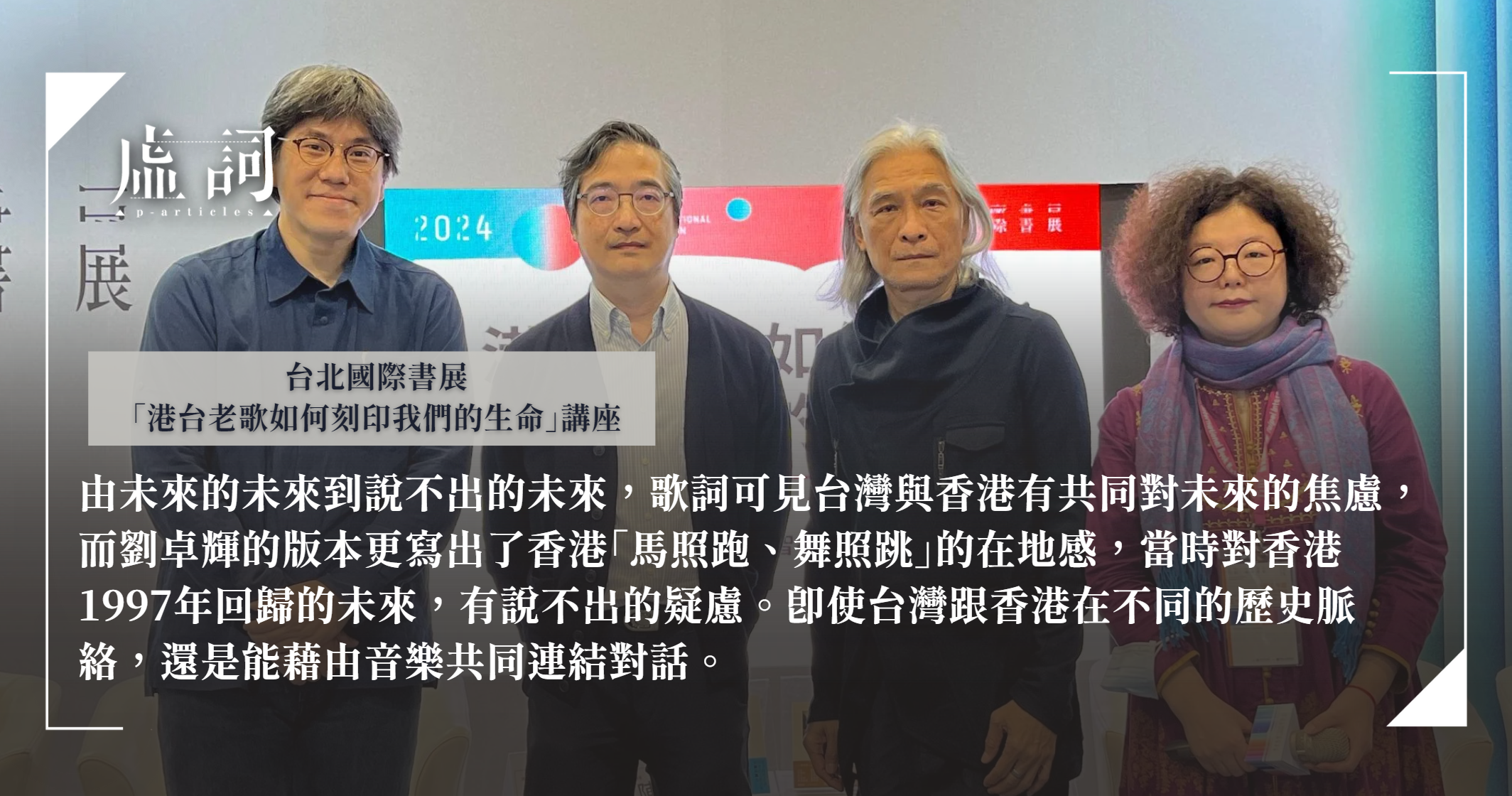【台北國際書展2024】「港台老歌如何刻印我們的生命」講座側記
報導 | by 陳諾霖 | 2024-05-15
在台北國際書展的一隅,傳來泰迪羅賓〈點指兵兵〉、姚蘇蓉〈今天不回家〉的歌聲,60、70年代的港台老歌步過世道變幻,在此時此地,再作迴響。台灣廣播人馬世芳、學者作家陳智德、香港填詞人潘源良同台說起,港台老歌對時代、城市及他們個人生命的深刻意義。
「我們那時候看香港,是羨慕的,是仰望的,覺得那是一個打造巨星的夢土。」
1971年出生的馬世芳,有幸見證香港流行文化的全盛時期,70年代香港電影工業風起潮湧,使台灣的影迷也為之瘋狂,他回憶起小時候跟爸爸去買香港電影的票,常常大排長龍,第一輪買不到票,第二輪還是只能買到第一排的位置。他那一代人對香港流行音樂最早的印象離不開電影,包括他最深刻的第一首廣東歌,便是許冠傑為同名電影寫的主題曲〈天才與白痴〉,以廣東話口語填詞,生猛地展現香港庶民文化。除了許氏兄弟,馬世芳指他兒時看香港温拿樂隊的五虎,也非常深刻,覺得又帥又有個性。The Beatle在60年代末紅遍全球,掀起港、台、日年輕人組搖滾樂團的風潮,大家大多都是翻唱英文歌,後來是香港先開始以廣東話融合搖滾樂來寫歌,克服了當時漢語如何跟外來形式結合的爭論。
馬世芳作為廣播人聽過海量的搖滾樂曲,但這首香港老歌依然讓他驚艷至今,他即場播放由泰迪羅賓作曲、填詞、主唱的〈點指兵兵〉。前奏的木結他響起,馬世芳便對當年的錄音技術、編曲、以及泰迪羅賓獨特又具魅力的歌聲一一讚嘆,但更妙的還在後頭。香港新浪潮電影《點指兵兵》在1979年上映,這首同名主題曲呼應電影警匪主題,以孩童兵捉賊遊戲作概念,歌詞有深度地思考兵賊宿命,中段的hook以兒童合唱出童謠,稚嫩之聲反襯出大人在江湖的無奈:
點指兵兵 點指賊賊
一點中你 怎去躲
馬世芳驚嘆泰迪羅賓揉合流行搖滾及童謠的編排,已使這首歌的層次更上一層樓,在歌曲的結尾部分,泰迪羅賓竟用樂器代替人聲,以木結他及電結他的雙獨奏,在歌曲盡處接着說故事,說不盡的餘韻,也使這首歌經得起時代的考驗。在〈點指兵兵〉推出的同一年,英國前衛搖滾宗師樂團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也使用了孩子合唱團的方式來演唱。這兩首歌曲編曲之前衛,可見香港的音樂人在見識、技術、題材及創作的彈性上,都遠超過當時在亞洲的同行。
馬世芳見證香港的顆顆巨星,他指香港老歌不只是港人一代的集體記憶,更是影響整個中文世界的聽眾:「我那時候看到的香港,如此熱鬧的流行文化場景,並不是理所當然,而是共同體意識經過了慢慢凝聚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只在文化、經濟領域、也包括政治領域,在整個歷史的動盪背景之中,如何慢慢去孕育跟凝聚,以廣東話作為一個樹立認同的文化符號。」

雙城對歌 說不出未來的未來
陳智德與港台老歌關係之深處處可見,他喜愛收藏雷射唱片及黑膠唱片,年輕時是樂隊成員,去年更出版了《樂文誌》,以散文追懷華語老歌,寫音樂與時代文化及他個人生命的抒懷。
在陳智德成長的80年代,聽到羅大佑、李壽全等人的台灣新搖滾,大大改變了他對台灣歌曲只有青山、姚蘇蓉的印象。他其中最欣賞的,是1986年李壽全出版的專輯《八又二分之一》,李壽全主唱及作曲、張大春填詞的〈未來的未來〉。這首歌是台灣新電影《超級市民》的主題曲,本來想命名為〈模糊的未來〉,卻因台灣處於戒嚴時期而過不了審查,才改為〈未來的未來〉。陳智德即席高歌,唱出張大春的詞,歌詞逆反「未來會更好」的思維想像,寫出台灣當時的社會狀態,人們對未來的焦慮及無法想像未來的模糊性。
〈未來的未來〉
雨水和車聲擁擠在窗口 我在都市的邊緣停留
少年的往事在回憶中消失 三十歲我的職業是自由
告訴我 世界不會變得太快
告訴我 明天不會變得更壞
告訴我 告訴我
這未來的未來 我等待
〈未來的未來〉推出的同年,香港電台舉辦了「生活中的香港」填詞比賽,指定以李壽全的這首歌,讓參賽者重新填寫粵語版歌詞。當年劉卓輝以〈說不出的未來〉獲得比賽冠軍,也從此開始他的詞人生涯。粵語版的〈說不出的未來〉由夏韶聲唱出,並收錄在1988年同名大碟中。陳智德把兩首詞並置唱出,如雙城對歌,昇華成非常有趣的對話。
〈說不出的未來〉
霧裏看都市 憂傷與灰暗 人們在抱怨天氣 互說風光
我對你傾訴 但充滿了隔膜 似是我故作寂寞在一角
曾話過 賽馬不禁 跳舞自由
曾話過 這裡不變 我會逗留
你問我 我為何
說不出對未來的感覺
由未來的未來到說不出的未來,歌詞可見台灣與香港有共同對未來的焦慮,而劉卓輝的版本更寫出了香港「馬照跑、舞照跳」的在地感,當時對香港1997年回歸的未來,有說不出的疑慮。即使台灣跟香港在不同的歷史脈絡,還是能藉由音樂共同連結對話。

「浪子詞人」潘源良的詞人之旅
潘源良的童年,沒有玩具,沒有電視,最廉價的娛樂便是圍着收音機聽歌,自己改詞唱歌,他回憶道:「我童年聽的歌都是廣播電台選的,不是自己可以挑的,不像現在可以在網路上,想聽哪一首就選哪一首。」60年代是一個很多事情還沒發生的時代,那時,看電視還屬於富貴人家的奢侈,電晶體收音機才剛開始盛行,電台會編排節目表,排好每個時段會播怎麼樣的歌,有粵劇、上海的電影曲、歐美流行曲等等。他特別記得電台常回播The Platters的〈Smoke Gets in Your Eyes〉,小時候的他雖沒學過英文,可一遍遍聽歌手演繹歌詞的情感,讓他好像聽懂了。
當時台灣流行曲也是一股新潮流,台灣歌手會來港登台表演,沿着彌敦道不同地點唱歌,才八歲的潘源良,對姚蘇蓉、青山的歌倒背如流,而正是這些老歌陪伴他成長,一點一滴啟蒙他成為填詞人。
姚蘇蓉的〈今天不回家〉可算是潘源良的寫作啟蒙,這首1969年台灣同名電影主題曲,讓還是小孩的他,聽得非常過癮。歌名明明是「今天不回家」,可歌詞卻勸說要你不要忘記家的甜蜜,迷失的你快回家吧。當年唱片推出後,還因為歌名而成禁曲,後來的唱片封套更把「今天不回家」改為「今天要回家」,可潘源良正是從歌名與歌詞的矛盾中得到啟發,甚至在上學的寫作課業上,把這「自相矛盾」的妙招學以致用。
他接着談到,在廣播第一次聽到廣東話原創曲〈勁草嬌花〉帶給他的衝擊,60年代很多經典歌是由電影而生,皆為戲中角色的唱曲,而當時電台廣播劇《勁草嬌花》創造了粵語主題曲的先河,讓潘源良覺得十分驚奇。他不但見證了主題曲這種音樂形式的誕生,還從〈勁草嬌花〉的歌詞得到啟發,要怎麼把劇中的亮點隱藏在歌詞間,主題曲要像預告片一樣,吸引觀眾去追劇。其後寫出林子祥的名曲之一〈最愛是誰〉:「後來我為電影、電視劇的主題曲填詞,也是這樣從電影主題去發揮。電影叫《最愛》,我就寫〈最愛是誰〉。」
潘源良從老歌當中吸收成為詞人的養份,一寫便寫了三十年,創作出超過六百首詞,為天王巨星寫出首首金曲。一切都是由那個伴在收音機旁,不亦樂乎地徜徉在老歌之中,好玩地把歌詞當成自己的玩具,聆聽、拆解、置換、創作,那好奇的小小潘源良開始。
文/ 陳諾霖(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