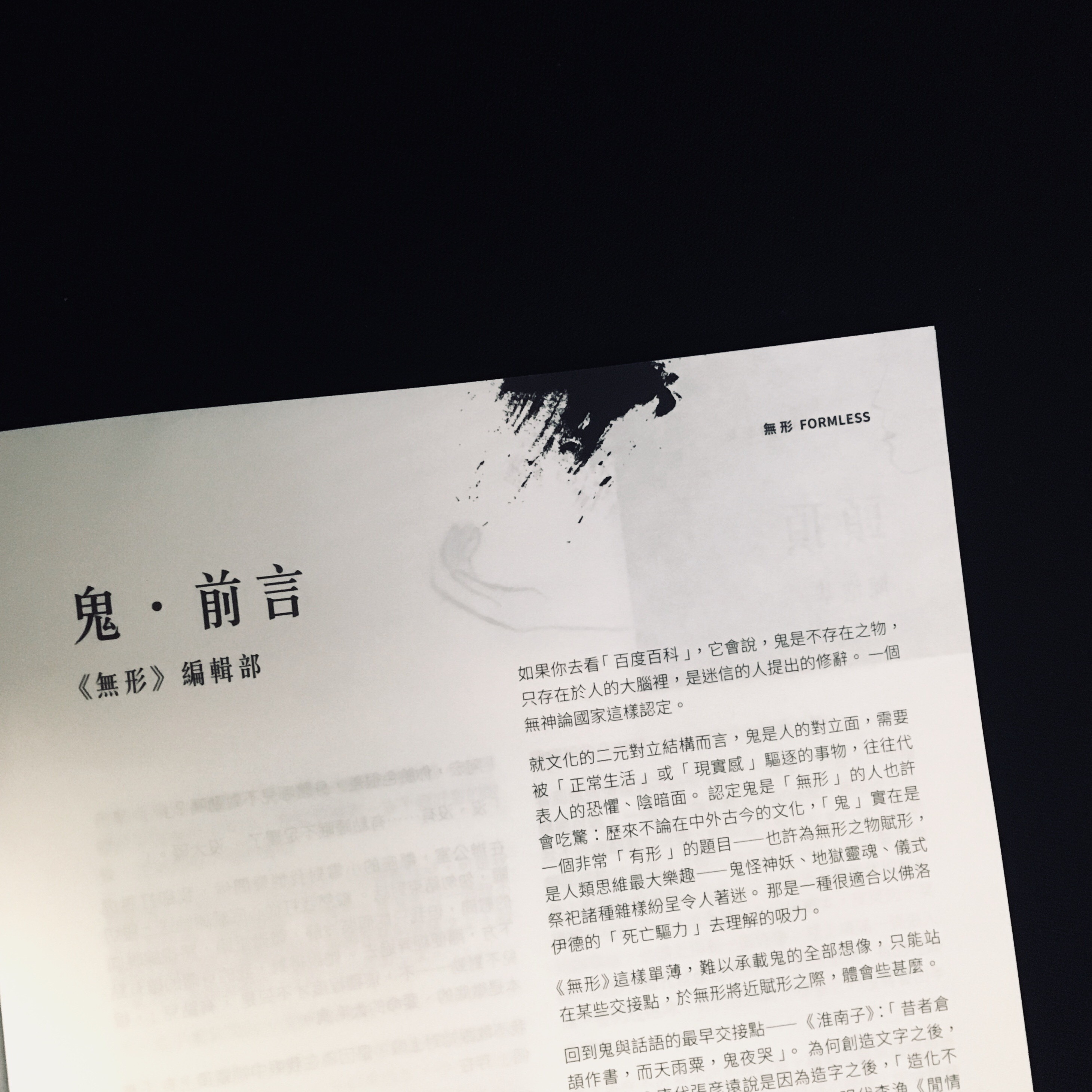【無秩序編輯室】鬼.前言
無秩序編輯室 | by 《無形》編輯部 | 2018-05-27
如果你去看「百度百科」,它會說,鬼是不存在之物,只存在於人的大腦裡,是迷信的人提出的修辭。一個無神論國家這樣認定。
就文化的二元對立結構而言,鬼是人的對立面,需要被「正常生活」或「現實感」驅逐的事物,往往代表人的恐懼、陰暗面。認定鬼是「無形」的人也許會吃驚:歷來不論在中外古今的文化,「鬼」實在是一個非常「有形」的題目——也許為無形之物賦形,是人類思維最大樂趣——鬼怪神妖、地獄靈魂、儀式祭祀諸種雜樣紛呈令人著迷。那是一種很適合以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去理解的吸力。
《無形》這樣單薄,難以承載鬼的全部想像,只能站在某些交接點,於無形將近賦形之際,體會些甚麼。
回到鬼與話語的最早交接點——《淮南子》:「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為何創造文字之後,鬼會夜哭?唐代張彦遠說是因為造字之後,「造化不能藏其秘」,「靈怪不能遁其形」;明代李漁《閒情偶寄》也對「鬼夜哭」作「以造化靈秘之氣洩盡而無遺矣」之理解。因為有了語言文字,天地間的秘密終將洩漏,隱密者都驚動不安。後來又有人將之引申為:有了語言文字,人類文明必將發展,遠離先民淳樸無爭之狀態。無論以上何說,均將「鬼」理解為神秘、蒙昧、與啟蒙相反的事物。蔣勳則獨將「鬼夜哭」理解為對倉頡造字的讚美祝賀(類似於「驚天地、 泣鬼神」 ),與羅智成名篇〈荀子〉中「張大眼睛,胸懷天明」的啟蒙精神呼應。
鬼到底告訴我們甚麼?陳浩基〈頭頂〉中的異象,城中無人願意接受,見異象者被定義為瘋狂,其實是「2+2=5」的規訓。廖偉棠〈清明夢書〉,歷史的死者與存在之內在剩餘結合,成為詩的能量所在,「人之所歸」。黃仁逵短篇小說〈六月物語〉生死難辨,香港地舊社區舊記憶,木樨地達姆彈,六月為何是鬼的季節?對某些目擊者來説,六月永遠是鬼的季節。
理性科學平等的墨子,卻認為人必須相信有鬼,若人人相信有報應,天下就少了亂事。「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墨子.明鬼下》。子墨子,抱持兼愛、非攻、選天子等超前信念的學術,曾抵抗秦國統一六國而組織軍事行動,敗後近乎湮沒無存的墨子一脈。
鬼是另一種真實。若人世存在極大壓抑,鬼就是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