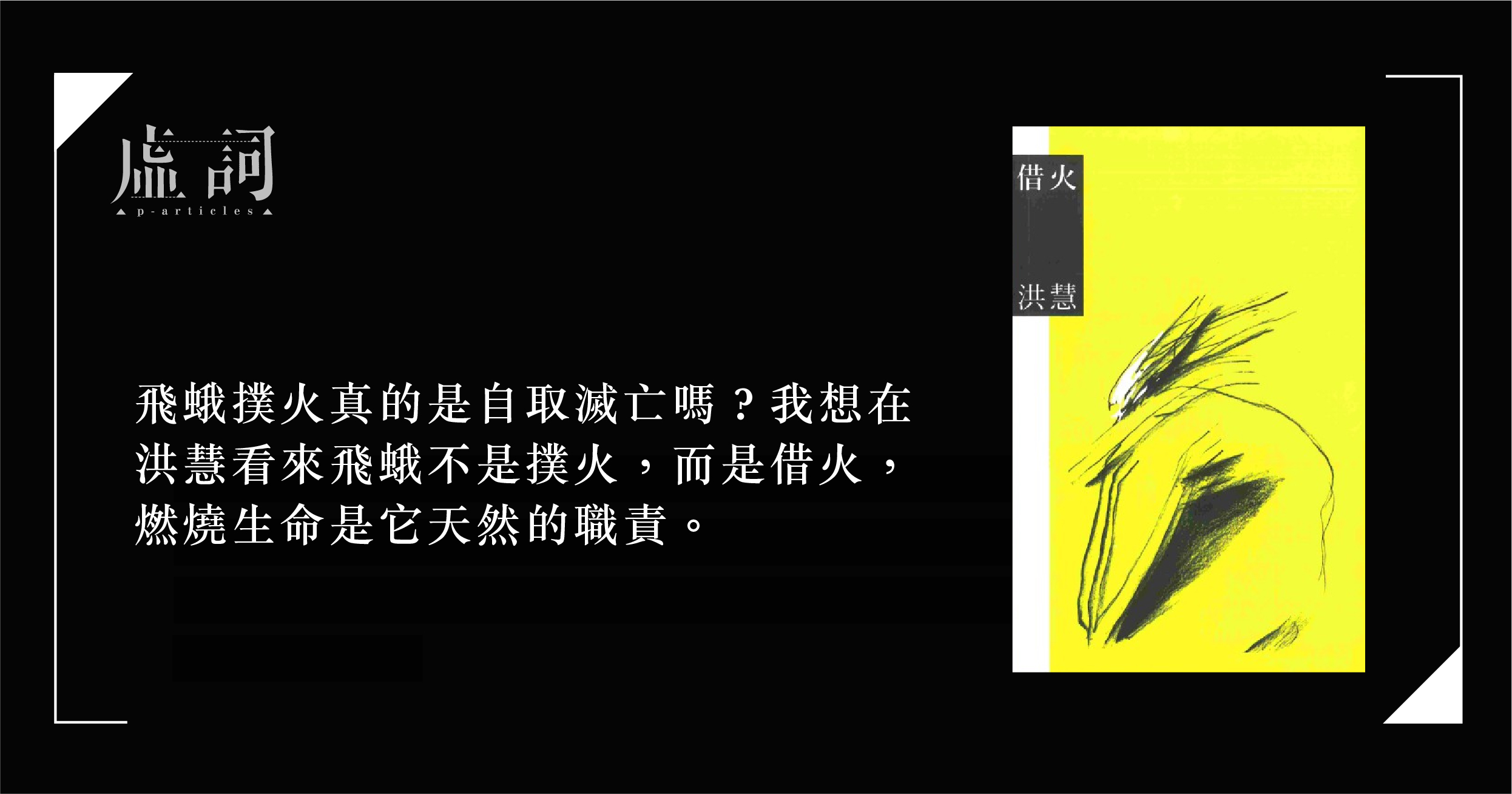不是撲火,是借火——讀洪慧〈借火〉
這是一首流暢卻不輕浮、暴烈而不盲目的詩;它按下快門,你附和歷史的腳步就要停住,它當頭棒喝,教人重新開始學習思考。不過,在我一開始讀完這首詩時,腦海中即時浮現的是至今還被印製在服飾、書包、杯具上的頭像:哲古華拉。
在此,哲古華拉的傳奇故事本身並不重要,它和這首詩的共鳴來自於一次歷史性的抉擇,準確地說,是哲古華拉的第二次抉擇。哲古華拉是阿根廷上流社會出身,父母皆名門望族,原可享受錦衣玉食的舒適生活。然而,青年時期長達八個月在南美各國的遊歷改變了他一生,加之家庭與時代環境的影響,哲古華拉毅然決然投身古巴革命,協助卡斯特羅兄弟推翻獨裁政權,這是他的第一次抉擇。真正令哲古華拉為世人銘記的是他的第二次抉擇。古巴建立起新政權後,哲古華拉被授予公民身份,擔任農業改革部長、內政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等要職。不過,高官生活持續不到六年,他就決定辭去一切職務、放棄公民身份,甚至拋下妻兒,回歸了叢林,投身剛果、玻利維亞等國的革命,直至最終被玻利維亞政府軍槍決。在哲古華拉的一生中,始終不存在一個可待完成的革命目標,換句話說,他的目標與信仰就是革命,他說:「哪裡有帝國主義,我就到哪裡去同它戰鬥」;在給孩子的書信中他寫道:「應當永遠對於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非正義之事,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李劼發表於1995年的文章〈喬治.奧威爾和切.格瓦拉〉指出,流淌在哲古華拉身上的是「純正的唐.吉訶德的血液」,他的革命本身是浪漫而富有詩意的。這篇文章提出了不少重要看法,譬如哲古華拉的革命是一種「流浪」,目的是行俠仗義而非奪取權力,它的本質含義在於「自由」,緣於「心靈的自由抒發」:
它既不是階級相殘,也不是恩怨復仇,更不是對異類的追殺,而就是一首詩歌,一曲浪漫的交響,一次毫無功利意味的行為藝術,一種對歷史對人性的雙重審美觀照,一場唐.吉訶德式的征戰,一個叫做海倫的美女。
而我以為,李劼的看法並不涉及對哲古華拉本人的客觀評價,而是建基於哲古華拉革命的詩性解讀。恰恰是這種革命的純粹性及其由「自由」而迸發出的詩意,使我在讀罷洪慧〈借火〉一詩時當即想起了哲古華拉。飛蛾撲火真的是自取滅亡嗎?我想在洪慧看來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它天然的職責。
〈借火〉一詩寫在2015年7月。陳子謙在〈不要悲傷,做憤怒的人〉一文提出此作「多少折射了雨傘落空後社會氣氛和青年意識變化」。我很贊成把此作放在公共意義上、在社會生活層面加以理解。進一步說,〈借火〉形成的毀滅性力量是具有公共價值的,這首詩的高潮亦就是它最動人的詩行寫道:「不用改革和火了/我們自己就是」。它意味著,傘後青年不再把個體乃至集體的「希望」寄託於制度的完善或偉人的領導,這種毀滅性力量既出自抗爭行動的失敗,實際又是對抗爭行動的再次確認。「希望」只由「抗爭」帶來,有抗爭才有希望。
於是,我們遇到了重新樹立「抗爭主體性」的問題。一方面,我認為「抗爭主體性」遠不僅是擺在傘後青年面前的命題,它的社會意義其實早在知識界展開對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批判時就已萌發。在蘇珊.桑塔格看來,這個社會通過提供大量的娛樂來麻醉、操控群眾。尚.布希亞也指出,它對差異的崇拜是建立在差別喪失的基礎上,「自我」和「個性」在談及自身時已在工業鏈條上、生產線上有所指稱。這個社會試圖說服我們,追求活得更舒適、活得更好就是我們的「希望」。視自由為靈魂的「抗爭主體性」,在這種嚴酷的社會條件下產生,它不可能同意那個富有創造力的「人」任憑擺佈,不可能承認我們窮盡一生所要發展、發揮的,只是消費或者被消費。
我們究竟如何理解洪慧詩中所寫「我還未準備好革一切的命」與「不用改革和火了/我們自己就是」之間和各自的悖論?他可曾猶豫不決?他是否失去了目標?為甚麼革命首先是革自己的命呢?為了嘗試解答這個問題,請允許我再談一談約翰.伯格關於上述社會批判的看法。伯格探討了「時間」和「歷史」的關係,當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變動不劇烈、歷史大環境看似一成不變的時期,我們的人生是被一種永恆的時間包圍著,簡言之,我們仍然相信「永恆」;不過,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歷史的變動速度加快,歷史演化的原理被提出、開始覆蓋時間概念,即是說「永恆」漸次被「進化」取代。時至今日,不僅「永恆」或者任何總體性概念已經被解構,我們周遭社會、時代、歷史的變遷速度也遠勝於我們短暫的生命歷程,沒有甚麼人、事、物不是轉瞬即逝。因此,對歷史而言,任何與時間擦身而過的逝去者,不過就是被歷史所穿越的人或事物罷了,一旦被穿越也就無關緊要了;對商業社會而言,則不論逝去者還是未逝去者都被化約為商品形式,主體性喪失了生存空間。約翰.伯格相信,解鈴還須繫鈴人,人的異化最終要靠人自己尋求解決。他講過一句話:「拼命的抗議行動,若是能讓人們不再覺得自身僅是客體,那麼歷史便停止了對時間的壟斷」。這真是精彩的斷言,不論你把革命瞄準何處,你首先應當革自己的命,須有痛徹心扉的自省,須有克服屏障認清自我的決心,通過與一個「被操控的自我」抗爭,為人生在狹長的歷史長河裡贏得主體地位。任何隔岸觀火的行為到最後只造成個體的埋沒、個性的淪喪,一如前述,飛蛾不是撲火而是借火,燃燒生命是人的天然職責。
因此從社會批判、公共價值的角度看,無論在大歷史還是在香港的小歷史,重樹「抗爭主體性」都具有無庸置疑的積極作用。但在另一方面,「抗爭主體性」亦屬於一種生命力的審美批判,它的旨歸還在於一種關涉自我人生的思考。在此,我將結合〈借火〉一詩,並將原本並未分行的整首詩劃作三個部份來談:
燒。燒世間所有該燒之人
燒啊 燒鬼國裡每頭敗壞的邪靈
火不夠。把所有史書丟進去
賠上雨林,賠上每棵偉人親手
墾植的良心
這首詩一開始就有典型的洪慧式語調並貫穿始終。聽過洪慧讀詩的人就知道,讀也好寫也罷他都能做到中氣十足:吟誦時抑揚起落,其聲鏗然,其神放逸;寫出來的許多作品則結構條達而無所間斷,行文氣勢強勁卻又變化多端;且你總會「摸到一個意象/心臟:鮮活滾熱/用稜角分明的節奏/跳動成我的抒情」(〈數稜角〉)。〈借火〉自不例外,他如此堅決,燒所有該燒之人,不惜賠上史書、良心去添上一把火。然而,誰是該燒之人呢?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判斷他「該燒」?這裡顯然存在一把標尺,使得這幾句詩不以一種瞬間爆發的激情出現,其表達方式和內容教我們看到作者的嚴肅態度及其長期的思考、醞釀。唐太宗李世民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史書」的功能就在於幫助我們整理過去興盛衰亡的規律或案例,為我們今時今日的行動提供參考,不讀歷史就不能深入理解當下乃至未來。同時,「史書」自身除了「記載」還要「評判」功過是非,這也是它提供行動標準的途徑。我認為,詩人所言「把所有史書丟進去」並不是否定歷史(畢竟在「過去」、在「曾經」至少還有他「深深滿意的詩」),而是呈現了人的命運和歷史之間的悲劇性衝突。服從歷史按部就班、跟隨潮流的人最終為潮流所淹沒,要贏得個體人生的榮光,就要同歷史抗爭,要燒(生)就必然有毀壞,這些過去的、既定的規律或標準,不能定義今人的行動,詩人對歷史的態度再明顯不過了。那麼,難道「良心」或者說「道德」就可以提供「該燒」與否的標尺嗎?詩人在此運用了反諷的寫法:一面說良心是「偉人」親手墾殖的,強調它的寶貴和示範性意義;一面又暗示這類良心已經被大面積種植為「雨林」而泛濫成災。概括地說,在「燒」(生)的進程裡,既定的「史書」或者虛偽的「良心」都不能提供行動標準,甚至就是要被燒毀的對象。
更多的火。更多的肉身
何必衣冠戴肉身
死就是,死。就是
把無頭孤墳的骨灰也撒進去
所有亂葬崗
都已被草草堆填
在洪慧這首詩裡,「火」、「燒」屬於一體兩面,都指向了生命體,卻既有生、生長、創造的一面,也有死、 消亡、 毀滅的一面。這一段可見現代人對「死」過於清醒的認知了,或可說是詩人在表達他對死亡的預期。現代科學顯然不相信靈魂有三十五克或者二十一克,一如詩人所言,死就是死,身體停止運轉、逐漸腐爛,而人的意識也在那一刻憑空蒸發。在他看來,死亡是不需要修飾的,死的形式應該和它本身的殘酷性保持一致,屍身被草草堆填,而誰的人生不是無可避免地草草結束呢?不存在一個生來有之的使命或任務,一旦完成才應該死、才可以死,任何人的死都是一念之間匆匆收場。正如火的使命就是燃燒直至盡頭,死是對生的完成,前者的殘酷性恰恰揭示了後者的重要性。如果你一定要談到生的使命,那麼不是別的,「我們自己就是」。
再讀一首曾經深深滿意的詩
再吻一次你曾經的嘴唇
你不借我火就滾到旁邊
我還未準備好革一切的命
但我已經把千億年的石油
和,自己裝滿黑色棺木
不用改革和火了
我們自己就是
從某種偏見出發,這一看就是年輕人寫的詩吧?記得有一次在某詩歌平台上分享洪慧詩作,因為整個系列事先被定位為「香港青年詩人」盤點,於是我循例在個人簡介一欄填上了「青年詩人」,後來經過商議又把「青年」二字刪去。原因顯而易見,當下的文學平台愈加重視培養、推薦新人,背後包含對技藝新變、對社會生活日益豐富並深入理解的期待,可是同時又點明這些作者還只是「青年」、處在不成熟、不穩定的狀態,讀者不必對作品質素和內容有過高期待,甚至應有所寬容。這當然是事實,不過就一些詩人或具體作品而言,這樣的標籤或許是值得一併燒毀的。
在〈借火〉最後的這幾行詩裡,同樣存在一種可以輕易被判定為不成熟、和青年一樣激進的氣質。但從整首詩來看,這種判定顯得那樣草率、無理。我們不妨將話題轉回革命。「我們自己就是」已經不是歷史上農民起義那般的革命參與者,那是受壓迫者忍耐到了極限方才被迫反抗。本文之所以將〈借火〉與哲古華拉聯繫在一起,意在指示這把火或詩中的「我們」不是參與到所置身的歷史行動中,而是出現了對主體命運和價值的自決,整首詩憑藉毀滅、死亡的藝術表現來闡發它對生存、周遭現實的理解和態度,其中最值得珍視的,就是這種生命的自足性,以及自我賦予的正義感和行動合法性。約翰.伯格在《攝影的異義》裡討論到了一張哲古華拉被槍決後的照片,有意思的是,伯格認為「他所設想的死亡,不再是用來衡量這無法忍受的世界非得改變不可的標準。在他察覺到自身真實死亡的那個當下,他在自己的生命中找到了可以衡量自己行為正當的標準,於是對他而言,他所經歷的那個世界變得可以忍受了。」
自我實現在當代人的精神結構中最突出,但自我實現的目標不應是既定的或被分配的,而是通過艱辛的努力追索而來、並加以自證的。「不用改革和火了/我們自己就是」,看似輕鬆實則艱難,當中的險阻和魄力非「千億年的石油」不可才表達出來,對生命自足和自決的不懈追求和讀一首「深深滿意的詩」、「再吻一次你曾經的嘴唇」一樣,都滿懷信心和激情,歸屬於人類原始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借火〉固然有其社會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但從根本上說,就像哲古華拉的革命那樣,這把怒火,最終因回到審美的、詩性的領域、回到個人人生的自證上,才再度精神煥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