骯髒的年代,都總有些被外判的人負責抹塵 ——《窄路微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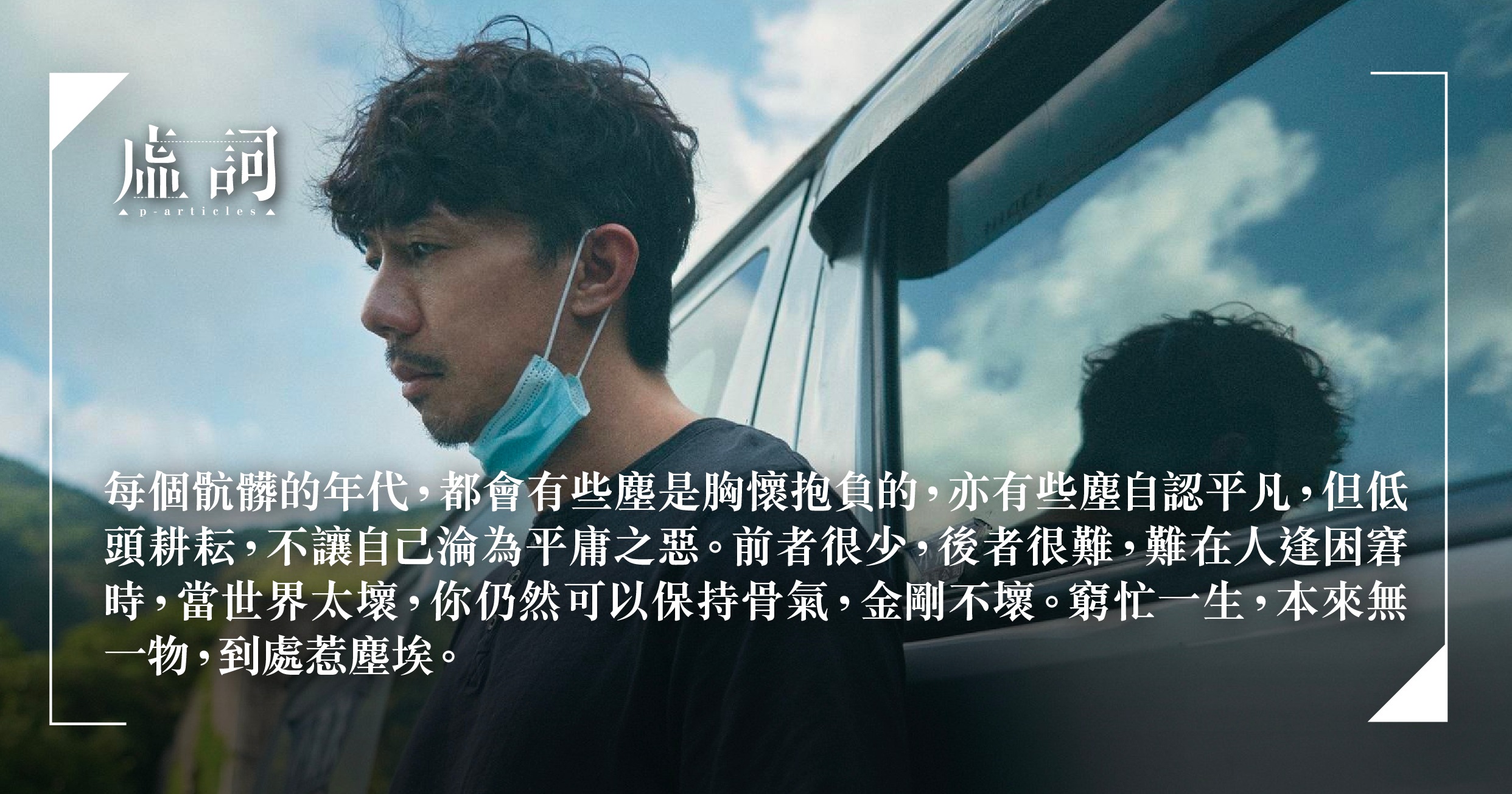
323571923_1249725902424198_7103621946329604521_n.jpg
從未試過有那麼多人,以不同途徑問我:「你覺得《窄路微塵》和《 X X X X 》相比,哪一部比較出色?」可能因為本地作品近來都愛用四字片名。客觀而言,許多《 X X X X 》從劇本到演員都可能比《窄路微塵》優勝,但《窄路微塵》有一些《 X X X X 》們都沒有的東西,就是它「沒有」去展露一部出色作品所擅於經營的睿智與機鋒。深信重劍無鋒,而大巧始於不工,這種「沒有」才是《窄路微塵》能夠打動人心的最大原因。
窮,忙,廢,人到中年,對上有高堂,對下卻無人無物的自僱清潔工,人稱窄哥(張繼聰),同樣是「沒有」的代表,唯一優點就是有骨氣,夠老實。名義上他是清潔公司「小飛俠」的老闆,卻其實只是個甩皮甩骨的老江湖,別人開舖前、收舖後,就是他的開工時間。專門承包別人不做的低下粗活,他的勞動,上天看不到,甚至連地上的人都看不到,或者不想看見。大家只知道,總會有人「執手尾」,但那個人是誰,毫不重要。窄哥不冀求出人頭地,只想活得心安理得,閒時食串燒有檸檬汁。導演林森和編劇鍾柱鋒都很有愛,疫情之下百事哀,卻焉知非福,人人都要消毒、要清潔,為窄哥帶來賺多少少的機會,而睡讓他遇到愛逞強,喜歡貪小便宜的單親媽媽 Candy(袁澧林)。
《窄路微塵》最初取名《窄哥》,當時疫情尚未爆發。因此,最終觀眾看到的版本其實是順勢而生,演變成疫情時期的香港社會觀照。用另一個角度看,其實上天是一直看到窄哥的,所以偶然也來參一腳,把《窄哥》引導成《窄路微塵》,特意讓全城人都戴著口罩,為他安排了一場淡淡相遇的「傾城之戀」。
電影選角出色,不搞笑的張繼聰,撇低了文青女神標籤的袁澧林,角色本身就有一些演員本人的真性情。或者,都跟演員這些年的際遇有關。電影上映前,訪問過幾位跟袁澧林合作的導演,包括那時候仍在英國的林森。他們大致上都覺得袁澧林聰明、悟性高,但可能太標緻好看,她的演員身份一直被低估。林森形容,袁澧林有時會太用力想證明自己的本事,未必特別討好,但這一點就恰好很像戲中 Candy 這個角色的性格。張繼聰亦在近期的一些訪問提過,自己年復一年密密做,投入喜歡的音樂和電影,但娛樂圈對這些漠不關心,從來只跟蹤他的明星夫妻生活,看不到他這一面。或者,窄哥就是張繼聰這一面的自我投射。導演選對了他的兩名主角,演員也遇到了可以代表自己的角色。
《窄路微塵》確實是淡,淡的是戲劇張力,這方面不及節奏緊湊的《正義迴廊》,也沒有《飯戲攻心》那些計算準確的笑位與台詞。然而,濃的是低下階層的關懷。電影有它的苦中作樂姿態,既不慘情,也不憤世嫉俗,他們窮,但是不寒酸,粗活但不灰頭土臉。像小女兒細朱有時不生性,但有時也懂得哄媽媽,「住在這裡幾好呀,起碼都有個窗。」窄路相逢,還未絕望,抬頭仍然有它的可愛之處。
這幾年看過的香港電影,許多都花了心思,想承載一些公共訊息,帶出一些與時代同行的道理。誠然,電影是城中人的情感寄託,也是崩壞世道裡仍可以倚賴的鏡像。但《窄路微塵》的步調很特別,林森沒有將一些陳義太高的社會抱負壓在兩個為口奔馳的主角身上,不騎劫他們的日常對話為時代表態。作狀的社會關懷,自覺幽默的政治嘲諷 —— 這種上流知識分子的視點,在《窄路微塵》裡從未出現過,是難得的如此實在、如此誠懇。他們就是買不起炒價口罩,連買兩根雪條都要等半價的渺小人物,只顧著低頭勞動,沒有大學問的洗禮,更沒有閒暇仰望大時代。活在時勢裡,隨時飄起,隨時四散。萬般帶不走,打拼過、掙扎過,然後一敗塗地,又再從頭開始。
俗世浮沉,始終只是一粒塵,他們大抵從未接近過「何處惹塵埃」的脫俗境界。但人死了,有人負責沖走屍骸。城市髒了,自然要找個清潔工。塵世多苦難,總有些被外判的人負責抹塵。每個骯髒的年代,都會有些塵是胸懷抱負的,願意拋頭顱,灑熱血,敢教日月換新天,亦有些塵自認平凡,但低頭耕耘,不讓自己淪為平庸之惡。前者很少,後者很難,難在人逢困窘時,當世界太壞,你仍然可以保持骨氣,金剛不壞。
當然,窄哥只是個「時時勤拂拭」的清潔工,不是佛門智者,但都有自己的擇善固執。
窮忙一生,本來無一物,到處惹塵埃。
不過電影世界始終是個童話,導演與編劇骨子裡都很窄哥、很善良,至少他們不捨得糟蹋他們所關懷的角色,在他們的人生灑鹽。但這裡不是童話,這裡是香港。電影上映時,導演林森已經與家人離開,逐漸適應了新生活。隔著電腦屏幕訪問期間,偶然聽到兒子在他旁邊吵嚷的聲音。林森一臉無奈。是的,這個社運少年、導演,同時也是一位父親,唯有把自己的作品留在香港,然後離開。
第一次看《窄路微塵》,特別記得窄哥那句「個世界閪,但你唔一定要做閪人」。聖誕前夕,導演遠道歸來,謝了幾場票。我再看第二遍,無家可歸的 Candy 對睡著了的細朱悄悄說了句「你以後大個咗,實憎死我」,聽著更覺得心酸。這裡不是童話,這裡是香港,而現實世界只有更閪、更殘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