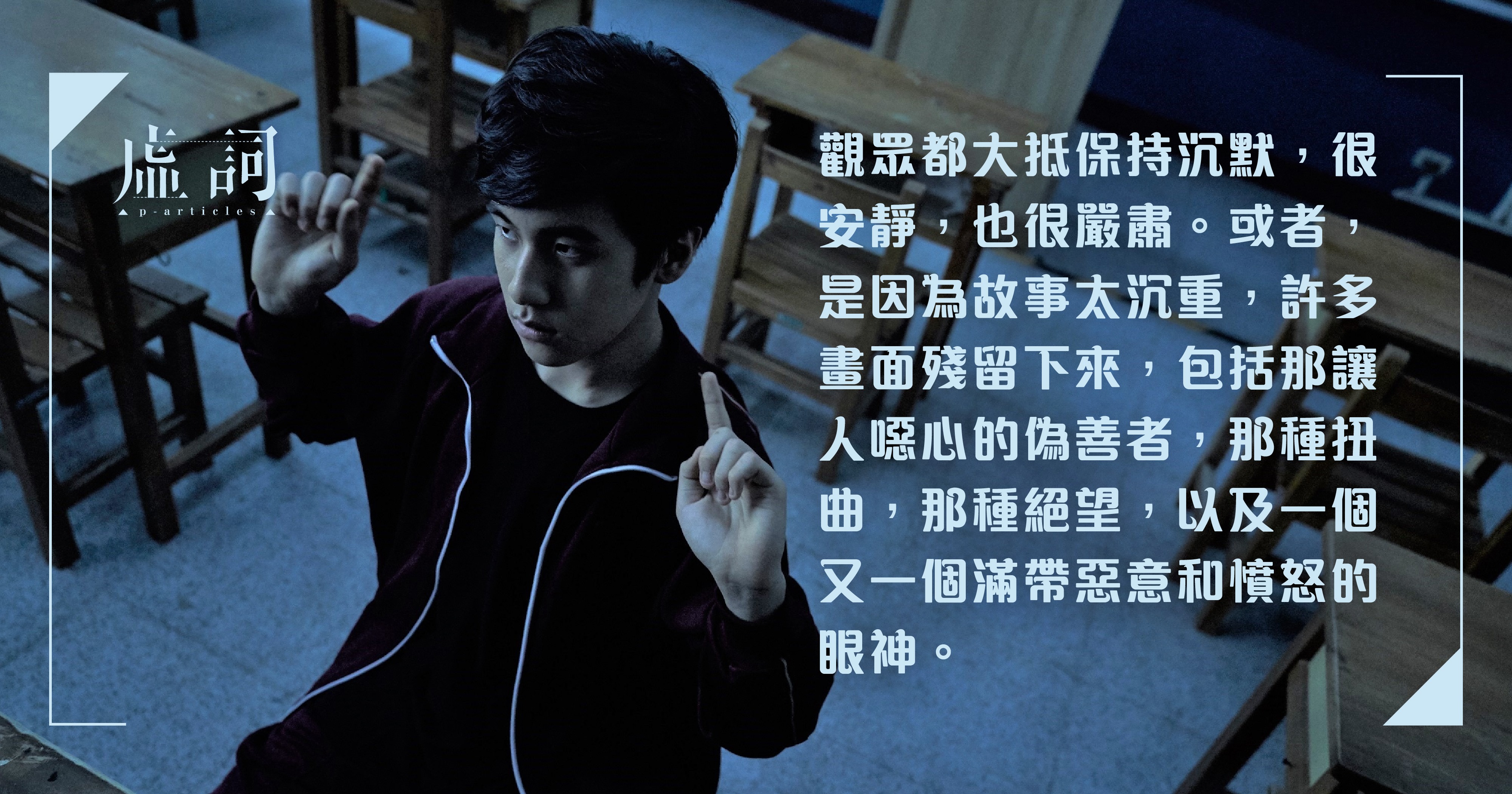《無聲》:讓我們學懂成為惡
有些電影,是真的無法忍心看第二遍。《無聲》就是其中一例。
那夜散場後,只見觀眾都大抵保持沉默,很安靜,也很嚴肅。或者,是因為故事太沉重,許多畫面殘留下來,揮之不去,包括那讓人噁心的偽善者,那種扭曲,那種絕望,以及一個又一個滿帶惡意和憤怒的眼神。電影大部分情節都「沒有對白」,只有字幕,只有仇恨,像是質問每一位觀眾,撫心自問,有沒有做過沉默大多數,是不是也將仇恨種在別人心裡,於他們往後的人生誕下惡果。
《無聲》改編自 2011 年轟動台灣,牽涉過百名聾啞學童的師生集體性侵犯醜聞。電影標題其實有多重意義。首先,它既指受害學童無法說話,一旦遭受霸凌和性暴力,想即時拒絕、反抗,甚至求救,都呼喊「無聲」。另一方面,屢次被班上同學集體強姦的女主角貝貝(陳姸霏飾演),即使本身不願意,卻選擇「無聲」啞忍不反抗,其後更若無其事與施暴者繼續在校園生活。
貝貝除了害怕家人知道自己被性侵犯,覺得丟臉,亦因為不想鬧大事情,害怕要離開特殊學校這個保護圈,回到「聽人」的現實社會遭人歧視。在她眼中,正常人的世界更可怕,她情願留下來被同樣殘障的「朋友」不斷強暴,縱然作惡,他們始終都是跟自己活在同一個圈子裡,他們才是「朋友」。

儘管不是《無聲絕境》(A Quiet Place)這一類恐怖科幻片,但《無聲》本身還是呈現了一種寫實而詭異的恐怖氛圍。性侵過程之中,受害學童的憤怒、屈辱、絕望,都只能訴諸沉默,不是不作聲,而是根本無法作聲,無法說話,觀眾亦無法聽到任何與畫面情節對應的聲音。唯一能夠聽到的呻吟聲,不成言語,反而產生一種被「靜音」的壓迫感。
但「無聲」最為尖銳之處,是用來指控這一所特殊學校裡,上至校長下至教師、輔導員與司機的這些能發聲而無聲的「聽人」。暴力與性侵犯就發生在一個近到無法不察覺的距離,但他們仍然心安理得,選擇視而不見,不作聲亦無意關顧,隱瞞真相。他們就是那些帶著歧視目光的「聽人」,覺得殘障學童只是負累、被飼養、無殺傷力的次等生物,更不會有能力作惡,根本不用認真處理。直到新入學的張誠(劉子銓飾演)發現貝貝被同學在校巴後座強暴,他看不過去,跟熱血老師王大軍(劉冠廷飾演)告密,王大軍才揭發貝貝的遭遇不是孤例,校內的性侵犯問題其實失控已久,幾乎每個學生、男男女女都曾經被侵犯過,不想被繼續侵犯的話,就只能選擇跟施暴者「一起玩」,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尋找下一個受害者。
故事像洋蔥一樣逐層剝開,卻一層比一層毛骨悚然。班上同學都知道貝貝不會拒絕,猥䙝行為就更變本加厲。男主角張誠為了拯救貝貝,獨自對抗他們的首領小光(金玄彬飾演),但原來,作為始作俑者的小光,本身就是長期遭受性侵犯的受害者。張誠終於知道,小光從小學開始已經被老師不斷性侵犯,情況持續多年,他是為了將自己的秘密和慘痛經歷轉嫁給其他同學,所以才讓自己成為施暴者。在聾啞學童的世界,他們無法擺脫校園,只能用傷害彌補傷害。
另一方面,張誠除了對侵犯貝貝的施暴者懷有極大仇恨,同時亦對成年人一直袖手旁觀更甚至轉而斥責深感憤怒。他無法用言語表達心中不滿,只能將仇恨寫出來,「為什麼犯錯受罰的是學生?」整個故事,藏著對於社會和教育制度的批判,制度的存在,從來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制裁提出問題的人。性侵事件的背後,就是一場公義與醜惡制度的抗爭。代表公義一方的王大軍,揭發事件之餘,更發現校長(楊貴媚飾演)早已知情,只是不報警不張揚,選擇低調處理,姑息施暴者。他為公義挺身而出,校長卻笑他初出茅廬,血氣方剛不世故。校長聲稱,怕傳媒大肆報導會造成二次傷害、孩子們「玩玩而已」沒有惡意、要顧全大局,各種狡辯與道理背後,動機明確,就是保住校譽,不想被問責,影響自己仕途。
「學校並不是你的敵人。」面對校長的辯解,王大軍轉而質問,「作為校長,連手語都不懂,你愛的到底是學生,還是學校?」王大軍的明知故問,是以良知識破了制度的偽善之惡,這一幕,無獨有偶聯想到香港話劇團最近重演的舞台劇《原則》。《原則》寫的不是性侵事件,而是更為微小,卻同樣觀照了政治現實的一場校規風波。故事之中,校長堅持「執法」處罰違規學生,繼而存心逼走意見不合的副校長,其專制手段惹來任教多年的資深教師不滿,不但帶頭請辭,更支持學生的罷課行動。然而副校長反問一句,「到底你是為了學生,還是為了逼走校長?」
用另一個角度來說,到底是為了公義,還是為了仇恨?在《無聲》的故事裡,仇恨總是曖昧出現於追求公義的身旁,張誠對小光有仇恨,王大軍對校長亦有仇恨。
或許,張誠與王大軍最終都相信了自己成為拯救者,他們的抗爭,最後換來了貝貝的重獲新生。但他們都低估了仇恨,低估了傷害本身所留下的記憶。性侵醜聞曝光,校長下台,整件事是否等於解決了呢?王大軍看到報章上的報導,似乎亦隱約感到心虛。發生過的傷害已無法修補,又是否因為戰勝了醜惡的制度,守住人性和公義,未來就不會再有人受到傷害?

一切尚未完結,前人留下的惡,像一個詛咒,一個循環:施暴者當初其實是受害者,拯救者其實又不經不覺成為了別人眼中的施暴者。惡已經種下,只會一層一層延續下去,無從完結。結局是一個相當沉重鬱悶的 Happy Ending,狠狠掌摑了王大軍所作表的公義勝利。
其實,在某些人眼中,他們就跟自己痛恨的制度一樣偽善、無能和自我感覺良好。不是每個學生都獲得拯救,無法被拯救的學生,內心就有仇恨。因為仇恨總是曖昧出現於追求公義的身旁。
台灣的真人真事,卻無法不聯想到今日香港的新生代,他們對整個社會,對成年人的集體仇恨,正是當下政治體制、教育體制都在粉飾隱瞞,刻意迴避的問題。像故事裡從來不將學生放在眼內的校長,以為低調處理 —— 處理掉所有將事件鬧大,不受控制的激進份子,就可以讓事情告一段落,一切就會重上軌道,經濟活動、人際關係與城市發展,如常運作。
然而,受過傷害,就不會忘記。仇恨已經埋在心裡,誕下以惡之名的下一代。
電影正告訴了那些指摘下一代惹事添亂、作惡多端的人,惡是循環,是 Stephen King 筆下那個不斷回魂的跳舞小丑,是宮崎駿電影裡,動物對人類積怨所化成的凶煞神。惡,就是果,是大家昨日苟且過活的時候親手種下的因。惡是惡的反芻,你解不開,誰也抹不走,是一整代人的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