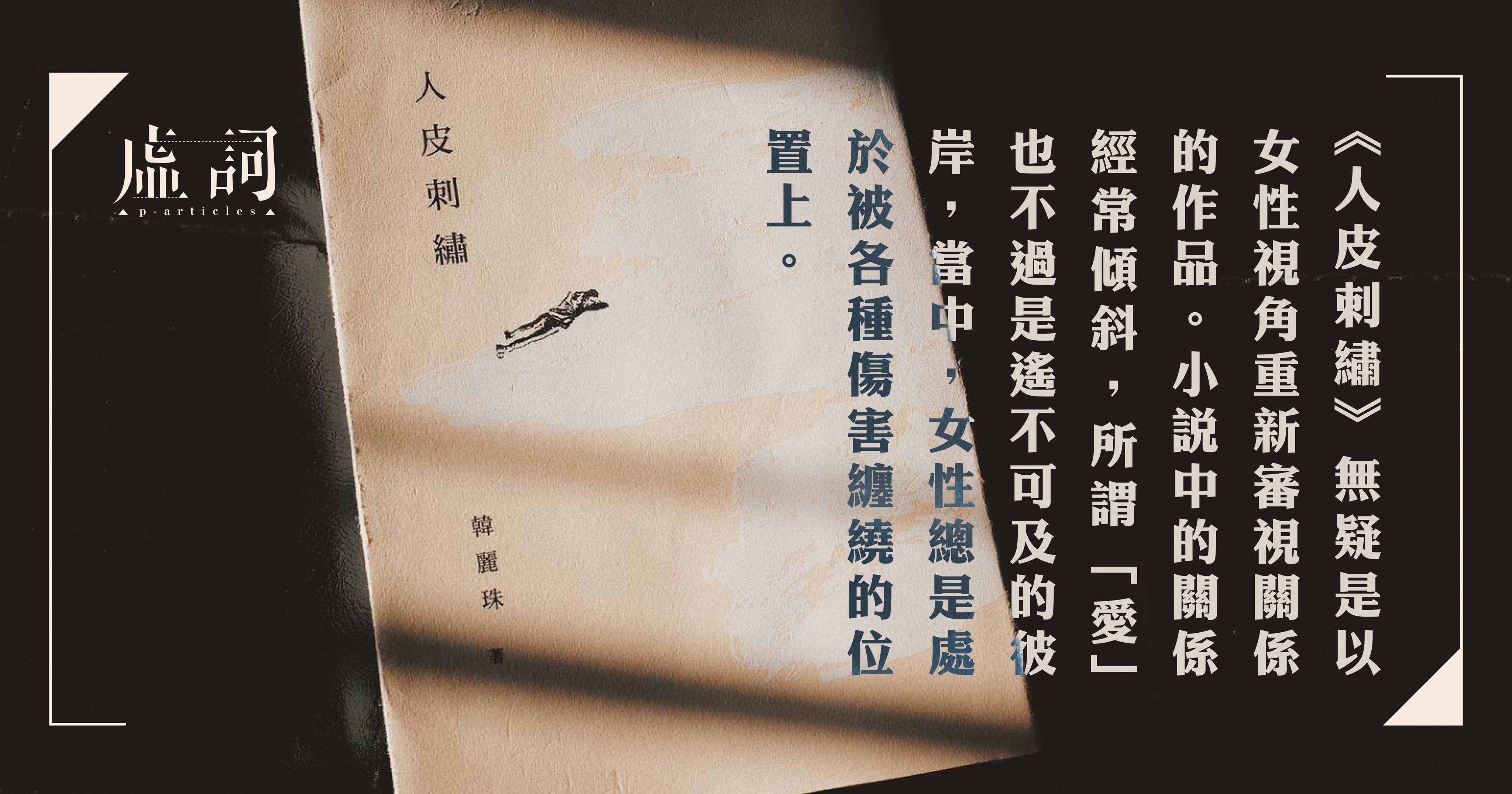愛是不可能,沉默的女性:讀韓麗珠《人皮刺繡》
書評 | by 黃臻而 | 2020-04-27
香港作家韓麗珠新近出版的小說集《人皮刺繡》,是尺寸如日本文庫本、可以藏進口袋裡的輕巧小書。故事所承載的重量卻與之相反,由開篇〈種植上帝〉開始,到同題作〈人皮刺繡〉,關係所換來的傷害始終環繞著角色,如書中所言,「身上被一團灰霧似的影子所籠罩」。
這裡說的關係,首先指的是男女關係。《人皮刺繡》無疑是以女性視角重新審視關係的作品,這些關係並非自然而然,也可能沒甚麼關係是「自然」的;小說中的關係經常傾斜,所謂「愛」也不過是遙不可及的彼岸,當中,女性總是處於被各種傷害纏繞的位置上。我們幾乎看不到小說裡有任何溝通的慾望,所以性是不可能,愛亦不可能。
女性作為自然的比擬
以性別角色來表現關係中的傾斜,於〈種植上帝〉裡尤其明顯,甚至帶點暴烈。〈種植上帝〉的主角是名為「火」的男性,他把身邊的女性控制起來,予以宰制,並把一切視為自然不過的犧牲與奉獻,就如他自許為「上帝」,又視大自然的供給為理所當然一樣。小說裡甚至有一段可以視為性侵的描述:
「他看著以太裸著身子,嘴巴被他的陽具堵塞著,臉容滑稽地扭曲著,像一個自願被綁架的人,發不出聲音,無法逃走、呼叫或求救,他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來,對她說:『精液是氣血精華之所在,吃下它,你會變得愈來愈美。』」(頁6)
那當然是一種自說自話。讀者在小說中亦聽不進任何女性的話語,只有火近乎自我中心的敘述,乃至意義的扭曲。關於性暴力的女性主義研究屢屢提及,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文化總是教導男性透過性來表達他的男性氣概,從而一再肯定男性自覺是主導和主動的性別角色。小說以這種性政治的表述,來形構一種不可能有愛(但火卻一再稱之為愛)的關係形式。
小說也藉由這種剝削的性關係,進一步指涉人與自然的傾斜關係。小說中,火是一個耕作者,但他對自然的態度跟對女性的態度無異,視之為維繫一己生命的「他者」:
「昆蟲的生命必須終結,田才能順利播種、澆水、栽種、長成和收割,女人必須一次又一次恍如死去般被他侵佔、掠去所有,她們和他才能重生。」(頁17)
小說的比擬中,自然生態與女性是互為表裡的象徵,在男性角色的敘述下,她們的消亡都是為了孕育和成就自己,是一種「自然定律」,由此合理化這種傾斜並以不斷索取為核心的關係。我們由此看到一種「中心主義」(-centrism),不僅是以男性為中心,更是以人類為中心,像火一樣認為不平等的關係才是命定真理,物競天擇的邏輯竟化成關係的基礎。我們知道這是謊言,這些謊言窒礙了關係的開展,火卻認為是真理,在他眼中彷彿只有自己的欲求。
但〈種植上帝〉並沒有就此完結。最後火有一場哺乳的夢,夢中他反覆吸吮女性的乳頭,她們竟是他母親的重重疊影。小說到此重新肯定了孕育生命所需的「母性」,不只顯出火的自大以至他的脆弱,更暗示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可如此比擬。可以說,它提出了一種循環、對等的關係想像,也是女性觀點的回歸。
女性的虛空身體
如果〈種植上帝〉是納西瑟斯式的男性敘事,隨後的〈灰霧〉和〈以太之臍〉,視點則挪回到女性身上。然而,故事仍然離不開女性在關係裡被貶抑的結果,讀者彷彿只是以女性的視點重新驗證一次。
〈灰霧〉的女主角灰灰,有一個經已離開了的對象林火,從名字可以看出與〈種植上帝〉的關聯。灰灰遇上林火,緣於把自己藏於關係裡的渴望,但從林火的角度看,他遇上的是一棵枯萎了一半的植物,他想給她澆水和施肥。植物的意象於此再次現身,內裡所表達的仍然是一種傾斜的關係,沒有看見對方作為人的完整性,兩人的吻只是「把她的嘴接到自己的嘴巴上」(頁25)。
更令人在意的設定是,灰灰是個吃得愈多身體愈瘦削、身體愈肥胖內裡愈虛無的人,旁人看來的體態變化,實則是慾望的反向回饋,慾望的「滿足」反過來是一種蠶食,「過份滿足」的形態其實是虛空的表現。關於進食與情感關係的聯連,小說透過營養師的說話如此道:
「『許多前來諮詢的顧客,向我要求各種餐單,他們急欲控制自己的食慾,成為更美味的人。他們可能知道,也有可能不曉得,他們想要的是被愛,但他們必定沒有發現,他真正的慾求是,被吃,被狠狠地吞噬,以填滿他們長久以來的空虛和匱乏。』」(頁28)
體態作為性吸引力固然是對女性的商品化規範,蠻有趣的是,香港的口語也確實以「食」比擬關係的交會,譬如「食女」就是就指與女性發展關係。只是,灰灰所慾求的根本不是令人哭笑不得的「體態美」,也不是被吃的慾求;種種遭到誤會卻又無法言明自身的境況,是灰灰與他人之間無法調和的鴻溝。她既無法迎合他人的期待,也無法自關係中真正滿足,只能繼續跟內在的影子相處。
「有沒有一些女人的身體,能一直完整?」
要問小說集中最顯然而且具主題色彩的女性筆觸,當屬〈以太之臍〉中以太問母親「那麼,有沒有一些女人的身體,能一直完整?」(36頁)。兩代女性的對答儼如命運輪盤,而母親這樣回答:「你有見過不開也不榭的花嗎?」——「含苞待放」,一種性化的女性形象,終將指向女性被削去的一角。
小說一再呈現這個「完整」的問題,無論是給予以太痛苦的阿火(又是他!),或是要以太填滿象徵婚姻的指環的木,都一一指向女性無法一直完整的命途,如小說所言:「終有一天,會像其他女人那樣心悅誠服,臉帶微笑地迎接噩運像幸福那樣降臨到自己身上。」(頁54)。相比前兩篇小說,〈以太之臍〉嘗試給予女性另一個可能,即木和他的房子與婚姻,一個「不具備刺傷她的特質」的男人。然而,這樣便足夠了嗎?這種關係,就能令人滿足如婚姻的誓詞與承諾?
以太所慾求的,於小說中表達的形式是外婆給予她的擁抱,把頭埋進肚腹裡的擁抱。大概因為那是純粹的贈予。無論阿火或是木,都不曾給予她這種安在的體驗,兩者對以太來說都是剝奪,無法在傾斜的關係中得到真正的溫柔,和愛。故事最後,以太默默接受了婚姻的命途,並且像很多結婚女性一樣,感到寂寞,感到一種角色降臨在她身上,而不是她自己。如果這三篇小說分別指出女性的寂寞處境,想來就是因為找不到一條通往自己的路徑。
傷害終將劃過,然後……
最後一篇小說、佔了全書一半篇幅的〈人皮刺繡〉,可說是女性婚後生活的續寫。更恰當的形容是,小說嘗試面向、打開關係裡的傷害痕跡,走過前三篇小說的默默承受後,它希望再走一段療癒的過程,方法就是朝向自身。
毫不意外,〈人皮刺繡〉裡女性敘事者的婚後生活並不愉快,故事結構由她離開丈夫,到遠方城市藉販賣「故事」給一名退休社會學教授維生開始。關係的傷痛首先來自她的童年,父親有另一頭家,母親知悉卻不願揭穿,家庭的虛幻外表使她把這種「維持穩定」的關係想像內置到自己心裡,只能透過夢來解決內心衝突,最後甚至以不再記得任何夢的方式,切斷跟內心衝突的連繫。
其次是,女主角以「責任」來理解她跟丈夫保文陳之間的關係,一如她對母親、對原生家庭那些不能說穿的「責任」。因為「維持穩定」,對婚姻關係的懷疑與不適,要麼帶給她罪疚的感覺,要麼只能以大量的內心讀白呈現出來;丈夫卻視而不見,甚至形容她「這是病,你要去看醫生」(頁99),對憂鬱的否定最終成為了這段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令人想起西西的〈感冒〉)。
在〈人皮刺繡〉的女性敘事者身上,我們彷彿可以看到前三篇小說的女性角色——默默承受、無法與外界接洽、在關係裡受傷。在她與母親之間,甚至可以看到一種女性命運的承繼,因為許多年來,女性都被視為家庭內部的核心,她尤其不能離去,非像她父那樣,有另一頭家,擁有離開的默許。「她」在各種角色裡被傷害纏繞,首先是女兒,然後是妻子。
其實她想要離開,或者很多人(不論男女)都想離開,離開原生家庭,離開變了質的關係,一如協助她到遠方城市的移民顧問鯨所說:「起碼在離開的途中,有短暫的自由的瞬間。」(頁116)。然而,小說想要表達的正正是「往外走」的徒勞無功,離開是一種幻覺,女主角透過不斷離開而壓抑的種種傷害,最終又傷害了自己。
小說裡名為「人皮刺繡」的手藝,即「刺青/紋身」,就是如何面對這些傷害的比喻。引用小說裡的說法:「刺青是確認痛苦,創造傷口,然後釋放痛苦的過程。」(頁174),一如「敘事治療」的過程,刺青師接收客戶的故事,轉化為一個圖案,然後刺在在客戶的皮層上;客戶需要對自己和對方坦誠,那些痛苦的意義才能夠言說出來,藉著轉化達致療癒。唯有誠實,才能建構關係的橋樑。
若「往外走」建基於虛幻,「往內走」或許才是她所需要的療癒。再不是那個默默承受、在關係裡受傷的「她」,而是通過誠實跟自己和他人建構關係,即便這意味著分離,以至分離所帶來的震撼。「沒有謊言/就沒有通向彼此的必要的路徑」(後記,頁233),這或許是對的,人的相處不免如此;但沒有謊言,她至少通向了自己,那必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