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傷口上沒有安全地方——評《給我一個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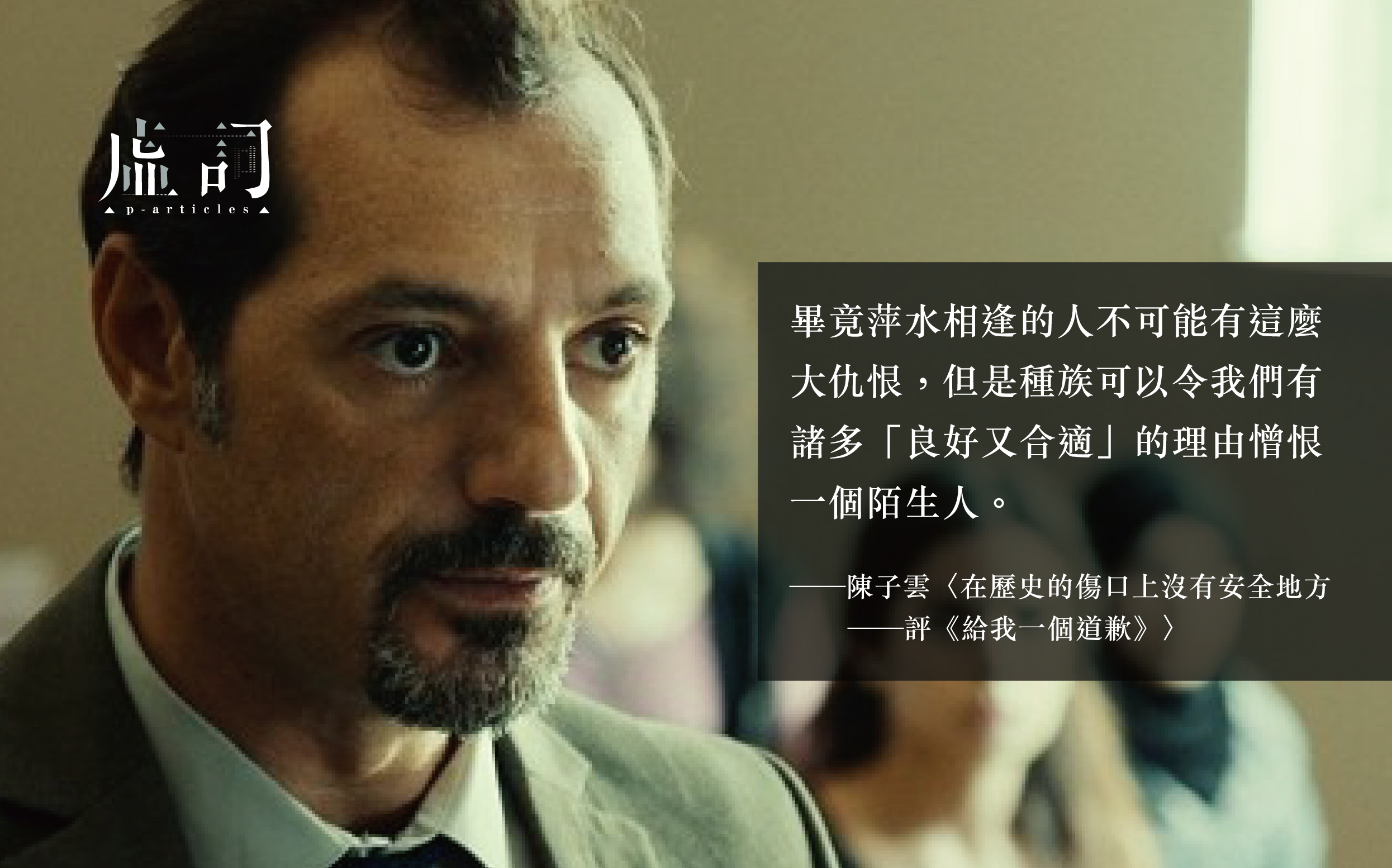
「在歷史的傷口上沒有安全地方。」最近電影《天使墮人間》(Jupiter's Moon)的一句對白頗為觸動我,尤其是昨夜看完黎巴嫩反思內戰傷痕的電影《給我一個道歉》(The Insult),如何以影像、戲劇創作回應或遠或近的歷史,值得閱讀。
在小說〈拋錨〉中,瑞士劇作家杜倫馬特(Dürrenmatt)為筆下男主角提帕斯安排一個身份:紡織廠的總代表,紡織是絲線的總和,若看仔細,人世間種種個體的遇合、恩怨到集體的國仇家恨,有如絲線交錯,愈是厚積,看上去愈難進入。有趣的是,同樣嘗試抽絲剝繭,《天》以奇幻元素回應歐洲難民潮,《給》則以實在且通俗的法庭戲回應內戰傷痕及政治正確的問題。
敘利亞爆發內戰,少年雅利安與父親冒險偷渡到匈牙利,意外獲得異能。當一個人陷入無國籍(statelessness)狀態,意味在歐洲大陸上他沒有身份,沒有歷史,難以被任何一方妥善收容和處理。和少年相遇的史登醫生,很難不教人想起史高西斯鏡頭下的耶穌與猶大,都是充滿情緒,互相質疑利用最後卻也是從對方的眼中映照自身,劇情寫少年的父親還是個木匠,他父親卻遭誤認為發動襲擊的恐怖份子。當我們一直以為帶來麻煩、搶奪工作與資源還帶來恐襲的難民當中竟有基督,那該怎樣面對這位既神聖又平凡的他者?

《天使墮人間》劇照
有人如史登醫生從利用他者的大能到後來接受救贖,也有人如警察賴斯洛堅拒不信奇蹟的可能,偏執狂般要把難民視為入侵國土的惡棍,不惜一再開槍擊落少年。在這個時代,信甚麼不信甚麼似乎各有堅定立場,因為站穩陣地就不必多花心思理解他人,甚至也不再抬頭看全人類共同擁有的一片天空。是不是這時代愈蠻不講理,愈把持門戶之見,愈要「離地」跨過界限去對抗?
少年的飄浮具現了超然於地上各種界限的良好願望,導演門多佐(Kornél Mundruczó)明顯精心拍他數次展現異能的場面,善用光影,雅利安從公寓緩緩下降地面,鏡頭拍他投映在公寓外牆的影子。在老婦人家中展現的那次則是在空中旋轉,他背對睡房的水晶燈,因為背光他變成一團黑暗,人在轉鏡頭也在轉。當然還有最深刻,也最應發揮飄浮的本色的上升,城市景物盡收眼底,卻是出於驚險逃生而離地。他作為一個身負異能的難民,被迫飛升同時意味他無法著陸,在歷史傷口上沒有安全地方,少年的命運最後竟與一個地上蒙著眼數數字的小孩緊緊扣連。畢竟奇幻元素再怎樣添加,回到現實去,歐洲難民潮背後深遠的歷史因素,它確實來到歐洲大陸上,求生的欲,久遠的恨,如何不簡單粗暴將他者劃分為恐怖份子或予取予求之人?門多佐寫一個會飛的難民,來問歐洲人準備好了沒,準備好就睜開眼睛。儘管在觀看電影期間,經常看到導演多半為炫技而作出的長時間手搖鏡頭,不過正如他的前作《狗眼看人間》一樣,他著迷於奇幻題材,看那一大群狗隻追著女孩走的場面就知道他樂於追求拍攝難度,但奇幻來到這次非常沉重又現實的難民潮主題,他似乎用對了。
至於在《給》片,沒有人會飛,但你見到一再以航拍鏡呈現貝魯特的城市景觀,除了感到此片雖探討敏感政治議題卻似乎資金充裕,還了解導演試圖以兩家人的故事說起這個國家至今仍未解決的族群衝突。「在歷史傷口上沒有安全地方」同樣適合作為這電影的註腳,不但不安全,還隨處都是火藥庫,爆發起來誤傷無辜。
保守派的黎巴嫩人東尼與巴勒斯坦人耶辛發生爭執,本應是良好意願的行動,在各有前塵的兩人眼中俱被視為挑釁。誰出言侮辱了誰,誰打傷了誰,本來是個人層面的爭執,同樣因為兩人放不下的民族傷痕與心結,被置於法庭上辯論。從個人到公共層面,兩人心理逐漸因外力影響生起變化,可以說是透過法庭戲這個類型,來讓兩個男主角經歷一場同情共感之旅,試著理解才有和解的可能,法庭在這裡不是尋找真相的場所,反而是讓族群(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基督徒)各自陳述自身歷史傷痕的場所,一場爭執的「真相」源於兩人,甚至是今天世界下的你與我都曾經面對的,不同時代不同社會都有過的衝突。

《給我一個道歉》劇照
電影儘管拍得頗為通俗,反覆出現的close up就是想觀眾代入戲中角色的情緒,但是劇本拍來層次豐富,適當留下懸念。一開始我們只知道東尼不是土生土長貝魯特人,他有一個即使復興過來卻不想回去的家鄉。他支持保守政黨,支持把巴勒斯坦人驅趕出去,這應該與他過去有關,直到他遇見工頭耶辛,他對一個工頭的反應激烈之大,可以合理推測這與國族身份有關。畢竟萍水相逢的人不可能有這麼大仇恨,但是種族可以令我們有諸多「良好又合適」的理由憎恨一個陌生人。來到法庭戲主導之後,法庭上有兩個主角、他們的家人與朋友、雙方律師原來是父女對陣、加上法庭最外緣的軍人與記者,層層疊合成一宗已經不再純粹、也不應純粹的審訊。
為了要一個人道歉怎會變得如此艱難,甚至牽扯出自己最不願面對的童年陰影?這大概是東尼在審訊時的想法吧。相信耶辛也面對著,審訊令兩人或主動或被動道出的身份與種族歷史,猶如翻口袋般,讓積塵抖落。惟有在這層面上的同情共感,族群中的個體才有可能認識、尊重對方?然而結局的理想,正正襯托出為了達致這個結局,已經有許多傷害形成,包括耶辛被解僱、那個被車撞至昏迷的送薄餅車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是說,為了平息這一波,卻又不慎引起另一波的恩怨和衝突?《給》好看在它使人看見一張網,前陣子看文晏《嘉年華》也很能感受到「網」的存在。
絲線縱橫交錯,歷史傷口之上作為一個人,也許只能像〈拋錨〉的主角一樣,惟有在意外的狀態下,才可走進善惡的紡織之中。一如無端獲得異能的雅利安,一如偶然遇見耶辛的東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