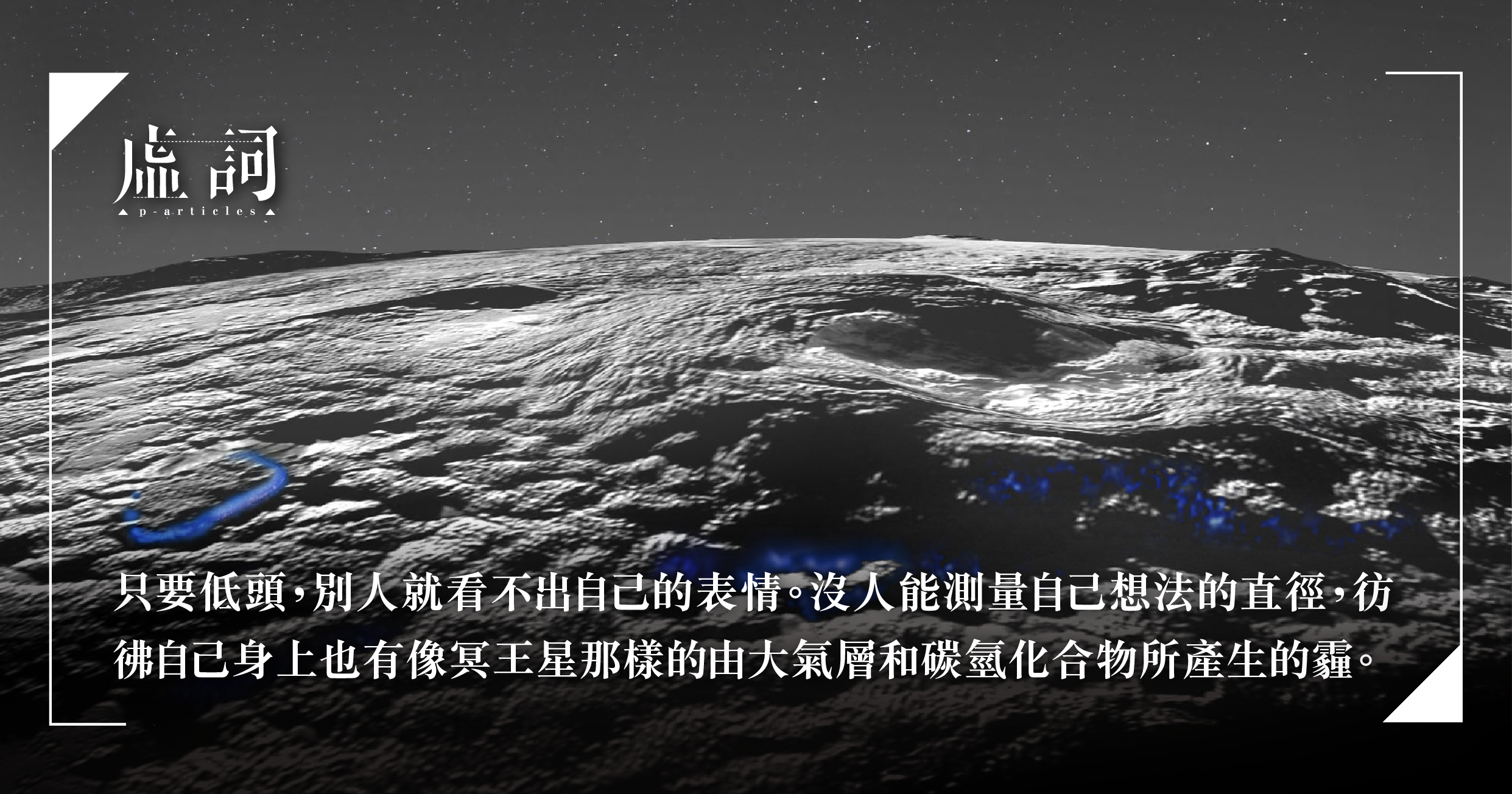「不談不會死的,我不想談這些,我們都不在那。」她還想説,他又不是香港人,爲什麽要在意海島上的事情。 他沮喪地說:「我們都是沙子,海水遲早是要漫過來的。」 (閱讀更多)
千年之宅
老人將麻雀的傷癒的叫聲視之為大宅對他的讚賞,每個早上,他向小鳥訴說家族偉大的歷史——他們從遙遠的地方來,驅趕走吃人的老虎,通過自身的勤奮與智慧,買下大量農地,在上天眷顧的年份裡,迅速累積了巨大的財富,然後,在這塊風水寶地上興建了這座大宅。在書架上那些字跡已難以辨認的書裡,記載著家族每一代人為這座城市所做出的功續,戰勝鼠疫、修葺神廟、捐助孤兒、舉辦盛典⋯⋯除了一件事。在老人還是小孩的時候,這座大宅已經是現在這副模樣,他曾害怕樓梯,甚至是整座大宅的塌陷,母親按撫他說,太過漫長的歷史已經停止前進,這裡只會永遠衰老,而不能死亡。 (閱讀更多)
【字遊行・波羅的海】心中法羅島
座落波羅的海的法羅島,憑海蝕柱馳名,是海蝕柱在瑞典境內最集中的地方,惟得專誠從斯德哥爾摩輾轉到維斯比,租車後出發航向法羅島的輪渡,訪尋英瑪褒曼在法羅島取景拍攝電影的足跡。 (閱讀更多)
【虛詞・每次冥王星靠近的時分】冥王星的生死神話
中、日、韓都將Pluto譯為冥王星,顯然是承繼了天王星、海王星的命名法。有趣的是,越南語卻將之譯為「閻王星」(Sao Diêm Vương),這顯然是將西洋神話與佛教傳說對應了起來。閻王一詞來自梵語閻摩羅闍(Yamaraja),本義為雙王。婆羅門教中,閻摩乃是日神之子,娶龍鳳胎姊妹閻糜(Yami)為妻。閻摩為了替人類尋找到達天界之路,自願死亡,因此主掌冥界。他常帶著兩條狼狗在人間巡遊,將死者的靈魂接引到天界。不難發現,人類早期神話中對於死神、冥王都不吝「賜予」一個伴侶,普路托如此,閻摩如此。巴比倫的女性冥王埃列什基伽勒(Ereshkigal)的丈夫為疫神奈伽爾(Nergal),古埃及冥王奧西里斯(Osiris)之妻為魔法女神伊西斯(Isis),中國先秦神話中北方天帝顓頊的神佐玄冥(或玄武)則是龜蛇合體,有「媾精」之象。至於普路托的搶婚,也非出於瞬間的情慾爆發;作為死亡化身的他,卻仰慕象徵著春天生機的小女仙。這大抵是基於先民「生死同構」的觀念:生命與死亡只隔著一扇門,悟得此理,就能推開這道門,「死而復蘇」。 (閱讀更多)
【佬訊專欄】通粉
最基本的港式通粉,是放入雞湯或豬骨湯,佬編覺得以澳牛的出品最好。Next level的話,就是番茄湯底的通粉,佬編覺得配牛肉最滋味。中環勝香園的茄牛通遠近馳名,不過上環法文古書店Indosiam的老闆Yves Azemar,就曾經說過他們只用罐頭番茄(雖然是地捫牌)比較削,佬編不得不同意。自己喜愛的茄牛通version,是用茄膏(或任何番茄湯底)做base,加入大量新鮮番茄和一點糖熬制,再加入用豉油炆過的牛腩或牛肋條粒同煮,埋尾還要打入一隻生蛋poach兩三分鐘。這樣的茄牛通,醇厚鮮美,吸滿湯汁的通粉和poached egg,配凍奶茶或凍鴦,是早餐的最高享受。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