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AL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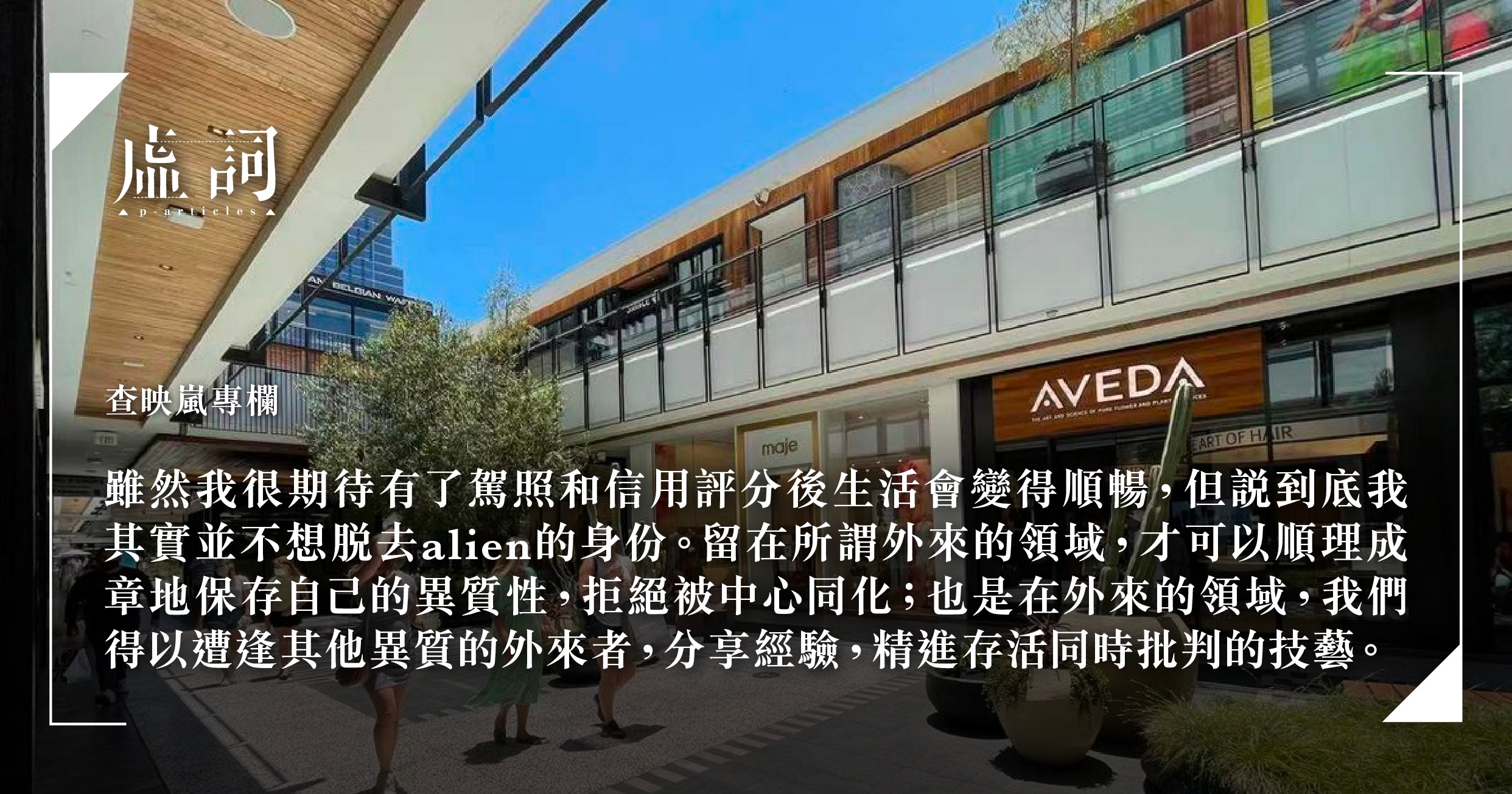
316487294_555675483049823_7839930180371027655_n.jpg
最近,我終於成功申請到第一張美國信用卡,又在加州車管局(DMV)辦好申請車牌的手續。在這邊,車牌也當成身份證用,所以考到車牌後我就有本地身份證了,又可以把外來人的印記多洗刷一點點。
當然,想要成為真正的本地人,目前還是遙遙無期。拿到信用卡後至少要過六個月,才會有屬於我的「信用評分」,然後不知要過多久,才能把評分建立到一個社會普遍接納的標準。在此之前,我只會是一個在社會上沒有信用的外來人,一個不時被要求提供I-94出入境紀錄的alien。官方語言中的外來人和電影中的異形一樣是「alien」,想來也不無道理,我好像從另一副身體移植過來的器官,最後到底會完全同化,還是會引起排斥反應,危害暫時容納我的新身體,目前是未知之數。
說起異形,最近我還深深覺得,講英文的自己是另一個人,像有異形寄生在體內,在英語環境牠能操控宿主,展示全然不同的人格。講英文的我,理性,有禮,正經八八,不會大小聲,不會胡言亂語,政治很正確。似乎異形想要扮成模範生的樣子,讓人類放下戒心,而動機不明。這陣子在三藩市,跟很多香港朋友碰面聊天,一講廣東話,馬上奪回身體的主權,浸潤在最熟悉的文化中,可以隨隨便便講不經大腦的話,竟覺是久違了的自由滋味。
畢竟自由和不自由,不僅受政權和法律所限,也有語言的、文化的、不成文的、難以觸摸的規範。我的朋友知里,在某些方面是很典型的日本人,習慣體貼別人的需要,也很小心不造成他人的困擾。最近她們家辦感恩節派對,一幫同學吃完飯一起唱卡拉OK,隔天她們的業主過來拿包裹時說昨天好像很熱鬧很開心啊,知里就擔心,那會不會是曲線提出派對有騷擾到人家?美國人不同日本人,少有用這樣迂迴的表達方式,可是對我們而言,身在美國,那些構成禮貌和尊重的邊界始終是難以掌握的。要不直接無視、隨便撞板,要不一點一點的,以來自邊陲之身,摸索中心的規條——可是那個小心翼翼的狀態,實際上就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為了在中心存活而捨棄的自由。
認真想想,雖然我很期待有了駕照和信用評分後生活會變得順暢,但說到底我其實並不想脫去alien的身份。留在所謂外來的領域,才可以順理成章地保存自己的異質性,拒絕被中心同化;也是在外來的領域,我們得以遭逢其他異質的外來者,分享經驗,精進存活同時批判的技藝。堅持異常,提出異議,擁抱異識,或許就是在這世道be a good alien的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