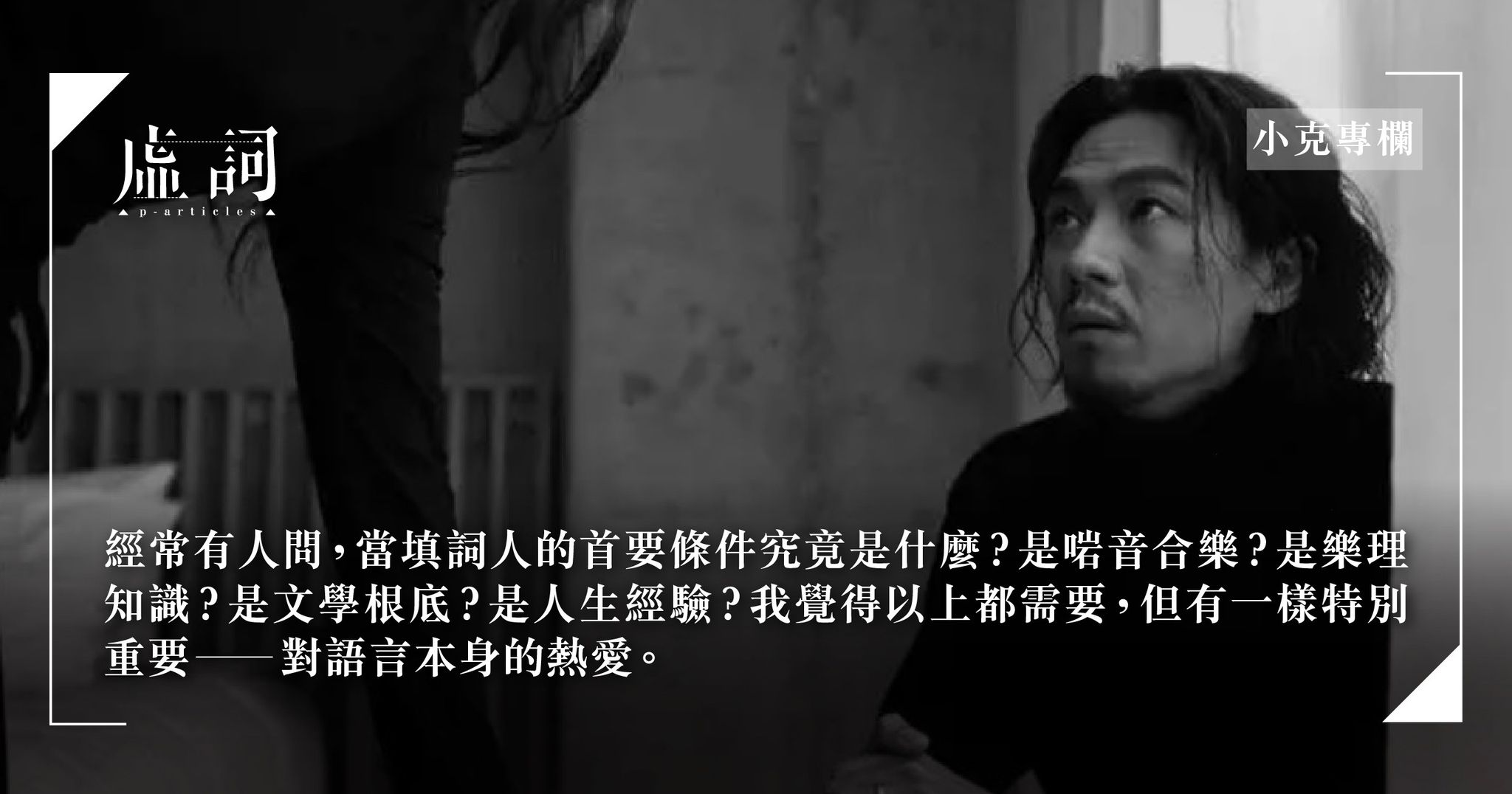【小克專欄】關於填詞的100件事(七)
15. 靚eng韻
上期收筆之際,梁栢堅突然跟我說:「這個『車』字韻不是最難韻腳,還有一個更難!」他說的是「靚」~eng韻,舉例夏金城的《為了靚靚》。的確,單是「靚」的同韻調單字,只有「柄」、「鏡」、「掟」和「正」;而此韻腳包含了大量廣東口語字眼,如「靚」和「掟」字本身就是,其餘異調字中,有很多都是從原本「~ing」韻口語化變成「~eng」音,例如「聲」正音是「sing」,但可變成口語「seng」,還有「驚」、「輕」、「聽」、「精」、「請」、「醒」、「頂」、「贏」、「靈」、「平」、「成」、「艇」、「領」、「嶺」、「命」、「淨」、「訂」皆是。
我們會說這個小朋友「精jeng 乖」不會說「精jing 乖」,但又會說「精jing靈」不會說「精jeng靈」;會說「條友好醒sing」不會說「條友好醒seng」,會說「咁早醒seng咗」不會說「咁早醒sing咗」;會說「首歌好聽teng」不會說「首歌好聽ting」。前年《風靈物語》錄音時監製問我副歌尾句「細聽風鈴內 響徹記憶未朦」內「聽」字應該唱「ting」抑或「teng」?我說應該唱「ting」,比較優雅,但Jer說如果唱「ting」的話,那應該是第3聲不是第1聲啊!我說:也不一定的,這字三音皆有,也可以唸成第1聲的,很多舊歌如《我和春天有個約會》中「夜闌人靜處/當聽到/這一闋幽幽的saxophone」,或《遙遠的她》中「望向她/卻聽到她說不要相約縱使分隔相愛不會害怕」,都是唱成第1聲「ting」的。那麼傷感的情歌,如忽然唱成「teng」會有違和感。《風靈物語》那句,當然是「ting」才能表達那種靜謐中傳來鈴聲的感覺。
廣東話就是如此奧妙,例如我們會說「佢成seng日都係咁」,但亦有人說「佢成sing日都係咁」;可以說「請ching上番行人路」亦可以說「請cheng上番行人路」。如此細微的語言習慣,必定要在本城土生土長的人才懂!所以經常有人問,當填詞人的首要條件究竟是什麼?是啱音合樂?是樂理知識?是文學根底?是人生經驗?我覺得以上都需要,但有一樣特別重要――對語言本身的熱愛。以上談到的一字雙音甚至三音,都是長年聽廣東話和說廣東話所儲下來的經驗,是對母語有高度熱愛,從而放諸歌詞內。黃偉文有次說:「唔鍾意廣東話嘅人真係填唔到廣東詞!」――關鍵是要極「愛」廣東話,不是只「懂」廣東話。
16. 口語入詞
引伸談一下口語入詞。都說廣東歌詞的最大特色是其「三及第」――文言、書面語及口語。「三及第」並非新鮮事,亦非廣東歌獨有,早在宋代已有夾雜文言、白話和方言的詩詞,直至晚清都有「三及第」書寫。至於「三及第」在香港流行曲的運用,黃志華、朱耀偉等老師們早有講述,可找他們的書來研究。
如何把「三及第」中的口語順利入詞,是我非常有興趣的項目。由小時候聽仙杜拉的《啼笑姻緣》(年輕人請試聽,第一段verse已經是三及第的經典示範)進展到許冠傑/黎彼德的全口語流行曲,黃霑的半口語,甚至後來黃偉文企圖為全口語歌詞平反的「新廣東歌運動」(其中重要作品是李彩華的《你唔愛我啦》),當時只是個聽眾,每覺有趣,卻未知難處;直至入行後自己試一次,才知全口語詞作之難。
我第一次寫全口語歌詞(改詞不算),應該是周仔的《覺醒字幕組》,「哪」、「沒」、「的」、「了」全部變成「邊」、「無」、「嘅」、「未」,填到嘔血!亦其實未竟全功,例如「打機先可制勝出奇」和「世界仲繼續有大騙局縛綁」等等,我哋平時都唔會咁講嘢(下集《灰人》直頭寫到嘔血之餘亦唱到嘔泡)。難在習慣了用書面語入詞,有時候收到demo聽兩、三次已大約知某幾句應該如何落筆,「我曾經在乜乜的乜乜與你走過」之類,你要變成全口語,即是要把「在」變「喺」、「的」變「嘅」、「與」變「同」、「走」變「行」,基本上兩者完全不同聲調,須改用另一套「口語思維」去重新構思。而且帶有口語的歌到今天仍讓人覺得是「通俗」或「低俗」,尤其寫情歌,放一兩個口語字詞在verse還可以,放在chorus hookline是高危行為,除非你想到一條絕橋,可以鋪定紅地氈讓口語名正言順踏入書面語(所謂正規中文)的大雅之堂,否則會被門口實Q趕番出去。所以,《是但求其愛》其實是一場非常難得的雜交,我都唔記得點樣飲大兩杯符符碌碌撞到出嚟……不過at the end都逃唔過有人話「尾句『落入五蘊』忽然用佛教詞語好扮嘢好突兀!」等評語,可見聽眾通常慣於針對個別字眼,根本不會對整體詞意宏觀地領會。
所以,若說全口語歌詞難,偶有口語入詞其實更難,因為當中需要對「語言美學」有所考慮,更要猜想聽眾的美學品味(通常與你不一樣)。如何在黑白山水中滲入一、兩點螢光粉紅?畫龍點睛還是畫蛇添足?好難拿捏。可與不可,與其說是靠技巧,不如說是種詞感和直覺。
《鏡中鏡》中有「畀畀心」、「姜B」及「才回望十歲舊時肥仔」,大把人覺得是一窩粥內的三粒老鼠屎。首先,我知道姜濤很想把前兩者放到歌裡面,「姜B」是個名詞無得郁,「畀畀心」難道改成「給給心」?當然可以變成「心形手勢」之類,但我覺得放在那個位置用作build up最合適。至於「肥仔」,就牽涉剛才提到詞人對語言的美學/品味問題。「肥仔」書面語是什麼?「胖子」,首先,唔啱音;但就算「胖子」啱音,我依然會用番「肥仔」。「肥仔」有種親切感,再加上「舊時」在前,會即時picture到自己認識的某鄰居或某舊同學。「肥仔」、「肥婆」、「肥妹」、「肥佬」,於舊香港根本從不帶褒貶,只是非常casual的一個客觀形容,跟「高佬」、「矮仔」、「瘦骨仙」無異,都是成長中不可劃缺的代名詞。而歌詞去到這位置,以一個非常casual/old school的形容、也是港人熟識的字眼,即時轉入「童年被欺凌」、「尋找自愛的鑰匙」、甚至是「治癒內在小孩」這麼嚴肅的命題,甚至是全曲最重要的關鍵轉折,我覺得非常dramatic,亦非常powerful;那種power,並非「胖子」所能提供,因為它帶有一種濃烈的親和力,涉及童年回憶、情懷、情感,是屬於這個城市、是我們生活中無可取替的兩個字!「風褸」尚可變「風衣」,「櫃桶」且可變「抽屜」,但「肥仔」,只能是「肥仔」!正如《問我》的尾句「講一聲/我係我」,不能改成「我是我」!正正是因為「我係我」!我們才會說「我係我」――「面對世界一切/哪怕會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這就是我堅持用「肥仔」的最大理由!這些語言習俗可能很快便失傳,不要等到某天在銅鑼灣行街時再也聽不到「入聲」才懂珍惜。
17. 口語背後
在口語背後,是美學,是品味,也是一種對傳統地方文化的尊重,是對語言本身的一種堅持,和愛。這也是香港流行歌詞,甚或各種流行文化藝術最珍貴的東西,一旦失去,靈魂便抽掉了。有次,《張氏情歌》派台後,陳奕迅跟我說最喜歡裡面的「或姓章姓蔣姓歐陽」及「或姓高姓蘇姓司徒」兩句。我問原因,他說因為只有廣東話會把「歐陽」和「司徒」說成「歐陽yeung2」和「司徒to2」,即是由「陽平」升為「陰上」。他跟我同齡,我們小學時會以姓氏稱呼同學――阿陳、阿黃、阿林、歐陽、司徒,尾音全部扯高變第2聲「陰上」;直至長大了,這習慣其實無變,會把同事名例如David中的vid唸成「陰上」,就如covid中的vid也如此,又或Sunny唸作Sun「ni2」。可見口語入詞,不單單是口語「用字」,有時也會把口語的「聲調」習慣入詞。
又例如《我也難過的》裡面有句「為何那諷刺是未能睡」,「諷刺」中的「諷」,正音是第3聲「陰去」,但旋律卻應該是第2聲是「陰上」。我聽demo時覺得旋律有點懷舊,以前的人真的會把「諷fung3刺」唸成「諷fung2刺」的,想想你是唸徐小鳳fung6定徐小鳳fun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