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碎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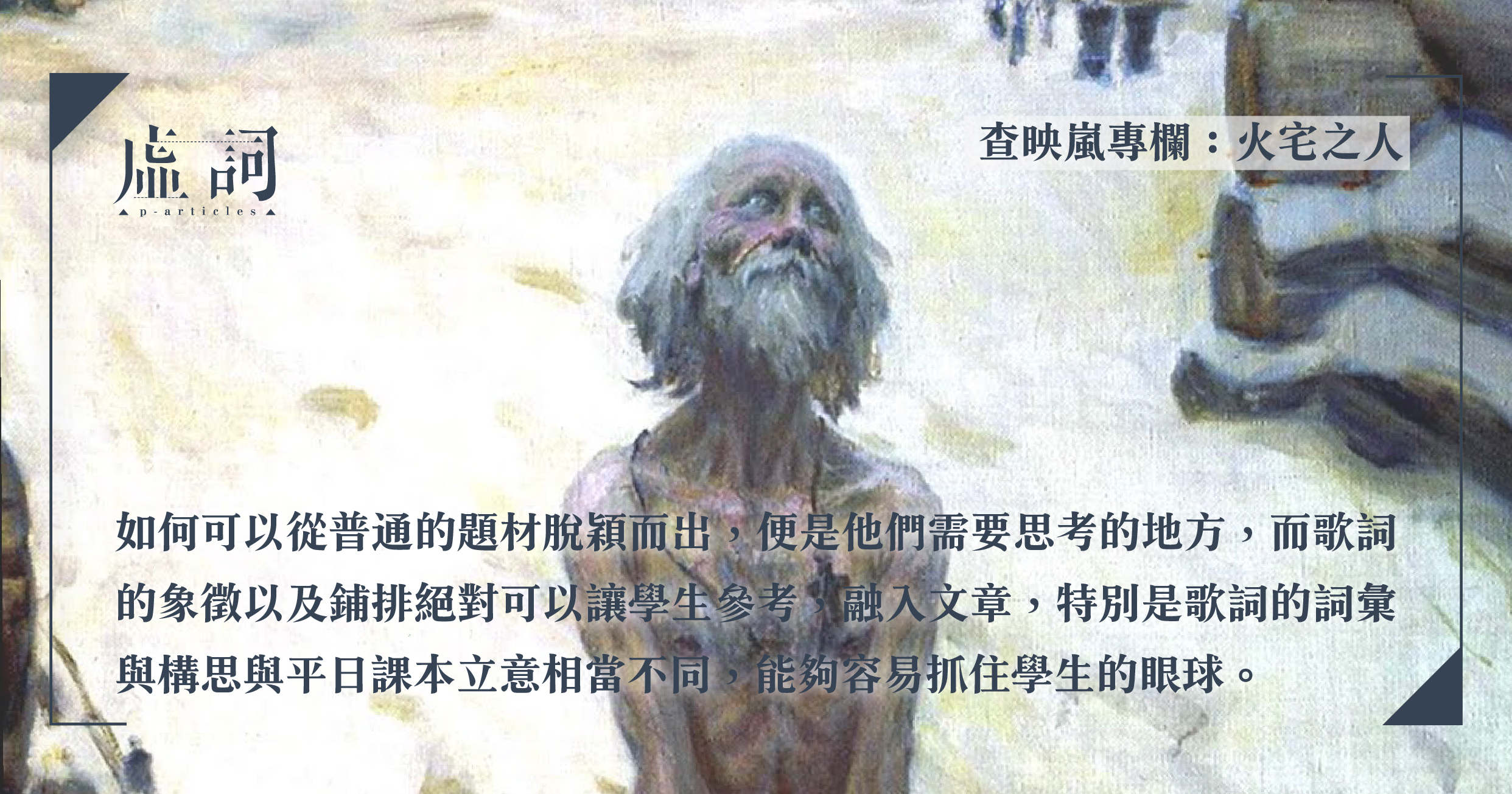
271826334_678725369963875_6860634492954714247_n (1).jpg
在我反反覆覆的移居生涯中,有兩個讓我知道自己終於安頓下來的指標:一是最初的新鮮感逐漸褪去,間或感到厭膩;二是看到區內的碎屑人時,熟悉得錯覺是鄰里。
碎屑人當然是我胡亂起的名字。比較客氣的稱呼可能是「怪人」、「遊民」;粗鄙而普遍一點的,會是「神經病」、「黐線佬」(雖然實際上他們不一定有精神障礙);有文藝傾向的人較可能稱他們為「零餘者」,這個名字相對廣泛而抽象;近年香港流行的稱謂是「白卡」——即殘疾人士登記證的俗稱——實際上「殘疾」還涵蓋聽覺和視覺受損、肢體傷殘、言語障礙、弱智、自閉症、器官殘障、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特殊學習困難,然而現在普遍的用法就是將白卡等同精神病,甚至是泛指不合常理、脫出常軌的人或物。
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都曾寫過這一路人物,在斯拉夫文化中,他們是「聖愚 (Юродство) 」。聖愚往往瘦如人形骷髏,有些戴著頸鐐或腳鐐,在大街上赤身裸體、自言自語,有時突然抽搐、大吼大叫。頑劣的小孩以捉弄他們為樂,但更多人視他們為虔信者、認為發瘋是聖靈降臨的時刻,,因此會敬畏地傾聽神諭;也有一種說法是,聖愚是道德上無可挑剔、接近神聖的存在,他們因此故意以瘋癲行跡來規避凡人的讚美。
在現代社會,「正常者」通過學校、職場、家庭等,進入大大小小的群組,而碎屑人則是分組活動上被挑剩的餘數,在群居社會佔不到位置,單丁存活,如同掉落在沙發狹縫中的餅乾屑——只有人際關係完全斷裂,沒有任何支援網絡的人,才會成為碎屑。正常人對碎屑人的態度不一,但一般都相信最好的選擇是修正這些異常。
現代碎屑人的一個特徵:似乎整天在來回行走,既不工作,也無消遣,就只是走來走去,重重覆覆,活像由一堆代碼組成用以妝點虛擬世界的無意識NPC。以前在西環常常見到的「花花哥」就是一例,年紀大概有半百吧,頂著一頭觸目金髮,愛穿桃紅粉紅以及一切花裡花俏的衣裳,大肚腩卻完全不加掩飾,渾身散發和打扮完全不相稱的厭世感;總見他在地鐵站扶手電梯上上落落,也見過他在站旁的小花園坐著發呆。如今我住的S鎮上,因各種原因有許多人無家,大街上也就徘徊著諸多的碎屑人,其中最觸目的一位我稱為「耶穌哥」。耶穌哥的打扮低調,總是像姜濤那樣穿全黑,但是和一部巨型手推車如同連體,每天在大街上來回疾走。本來無家者將所有家當帶在身上也很常見,但他的手推車配備包括一台電腦、一台大喇叭,以及寫著「Jesus is my Lord」的兩塊軟墊。看起來是想向世界傳福音的態勢,但我猜他的自我設定是「小鎮的特約DJ」,因此每天在街上狂炸各種迷幻派對音樂,將噪音從街頭推送到街尾、再推送回去街頭,大喇叭的轟聲像一把烈火,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燒滅一切雜音。我最好奇的是他如何解決電腦和喇叭充電的問題——大概當小鎮安靜,就是他在充電的時候。
在這裡,碎屑人身處一個割裂的時空,和一般的時空毫無交疊。某個人們竊取冬陽微溫的下午,有碎屑人在遠處厲聲叫喊著什麼,久久不竭。語言如捱撞報廢已經不成形狀的破車,無能承載意義,人們耳邊迴響的只是某種難以辨認的動物吼聲。我數次環顧四周,看不見碎屑人的身影,只見路邊幾個喝咖啡的靚麗女人彷彿絲毫未覺,一路談笑。偶爾會這樣,碎屑人試圖穿過透明的區隔,過來這一邊,想要拿一張鈔票,或者,只是想讓人看見;但正常者畢竟是訓練有素的一群,他們精於迴避眼神、繞遠路、自動過濾雜音,因此碎屑人鮮少突圍成功。除了因爲世界的光滑、清潔、完整,需要正常者合力保持,或許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不過是徘徊在狹縫邊緣勉力不掉落的一群,因此迴避無比接近的碎屑人宇宙,其實僅僅是生存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