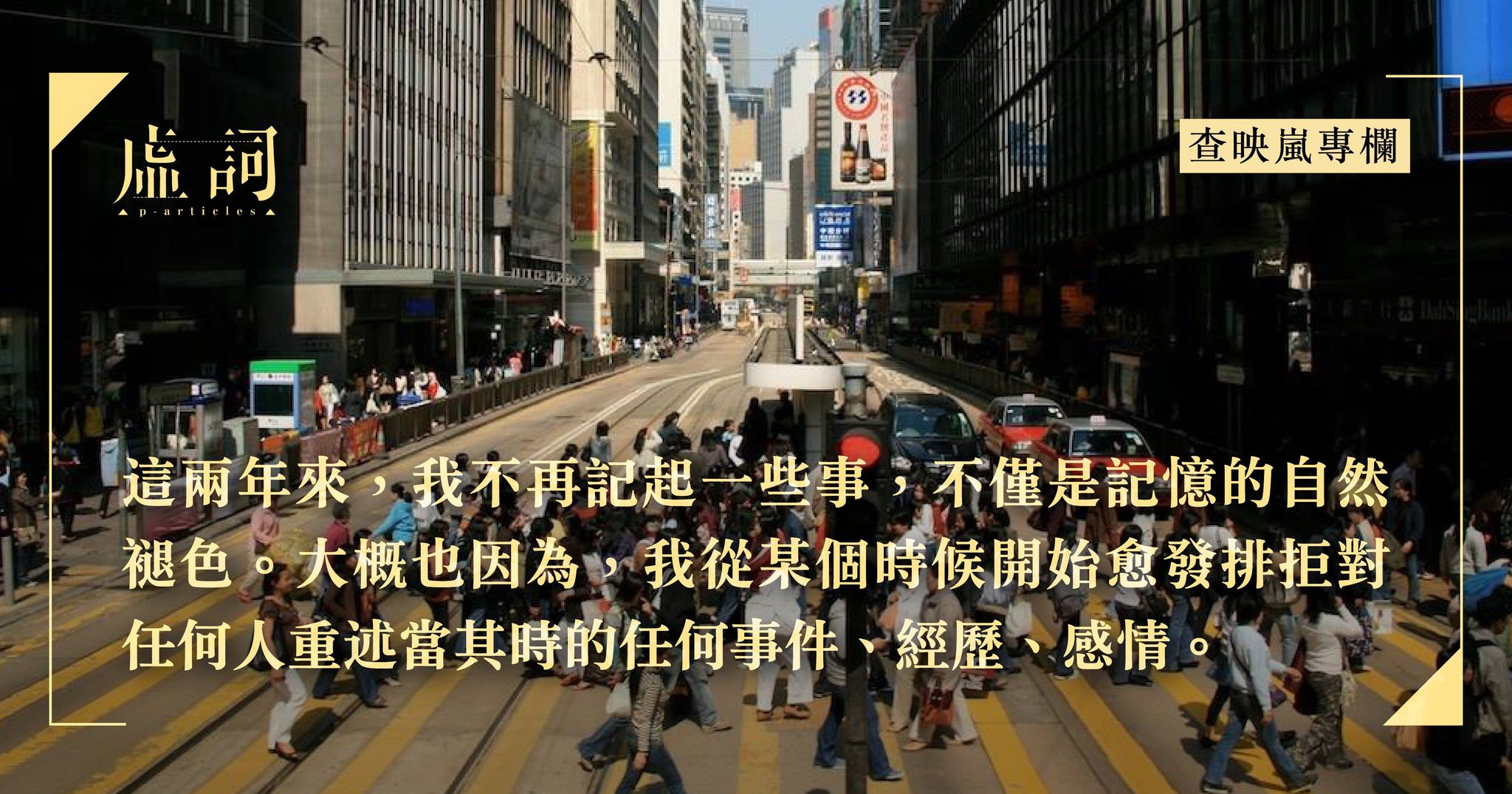【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一個晴朗日子
我將一直記住那個過於晴朗的日子。尋常的六月天,幾近無雲,陽光毒辣。我從中環站沿雲咸街、下亞厘畢道走向山上,熱得錯以為自己是焗爐裡的烤雞,不到十分鐘,油脂已開始溶化,終於一副狼狽相地抵達美國領事館。
這是我預約辦理簽證的一天,登記時點選了最晚的時段,早上九點四十五分。前一夜緊張失眠,深怕遲到,又怕未能通過面試,睜眼到清晨,無聊至極便滑手機,竟見蘋果五高層被捕的消息。照片中的人,雙手被反銬在背後,眼睛異樣的冷靜,你便知曉,這一切事態,他們老早了然於心,不存半點僥倖之心,只是坦然迎向預想好的路。而我偏偏選中這個日子,張羅離開的事,小心翼翼地說服一個陌生國家,我是一個可以信賴的入境者,不懷任何惡意。
說不出是什麼感覺,大概有怒,又自覺背棄了一些人,卻像在遙遙回望已過之事,一種怪異的既視感如濃重霧靄,稀釋了感覺。一列失控的火車沿軌疾馳,途經之處所有的毀壞與傷害,皆按照預言一一應驗。眼前的災難無法挑起極端的憤恨哀怒,大概因為見證者心知,前方還有更大的浩劫要來,世界的崩塌尚未完成,我們還在屏息靜待。沒有人知道還需要忍耐多少的失去。
排隊約一小時後,終於順利完成面試。因為睏與熱,整個人瀕臨廢掉,昏眩中坐上10號巴士,是我沒搭乘過的路線。無念想地看向窗外,眼前竟出現一些熟悉的街角與建物——巴士從中環舊立會,駛向軍器廠街口、皇后大道東。已經許久不曾重溫這條路線;那些久未憶起的,刺鼻的煙霧,橫亙著路障的街口,刺穿嚴實護裝的眼神,縈繞的歌聲,濃稠的情緒,突然競相來襲,讓我無防備地重返一個久遠的創痛時空。
這兩年來,我不再記起一些事,不僅是記憶的自然褪色。大概也因為,我從某個時候開始愈發排拒對任何人重述當其時的任何事件、經歷、感情。有一段日子,我反複認知到,一些生命已被毀壞而我依舊安然無恙,因此任何述說都是輕率的褻瀆。一個黑洞降生,純粹的靜默吞食了關於那年的一切。
在那天之後一個月,《時代革命》在康城放映的消息傳來。夜裡我在另一輛巴士上,點開當天上線的預告片。如此才明瞭,在街道上度過的每個分秒,早就蝕進骨頭裡。自己和城市早就變了樣,但又好像有一部份的靈魂分離出來,始終黏附在那個時空,因此有時會覺得,自己的心還是當時的模樣。記憶從不曾消散,失掉時序的回憶被分割得細碎,但那些碎塊,一片都沒有丟掉,一直靜靜在浮游。
它們總是在那裡的,但終歸必須偶爾被召喚、擦拭,如此方不會在廢棄之中,悄悄變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