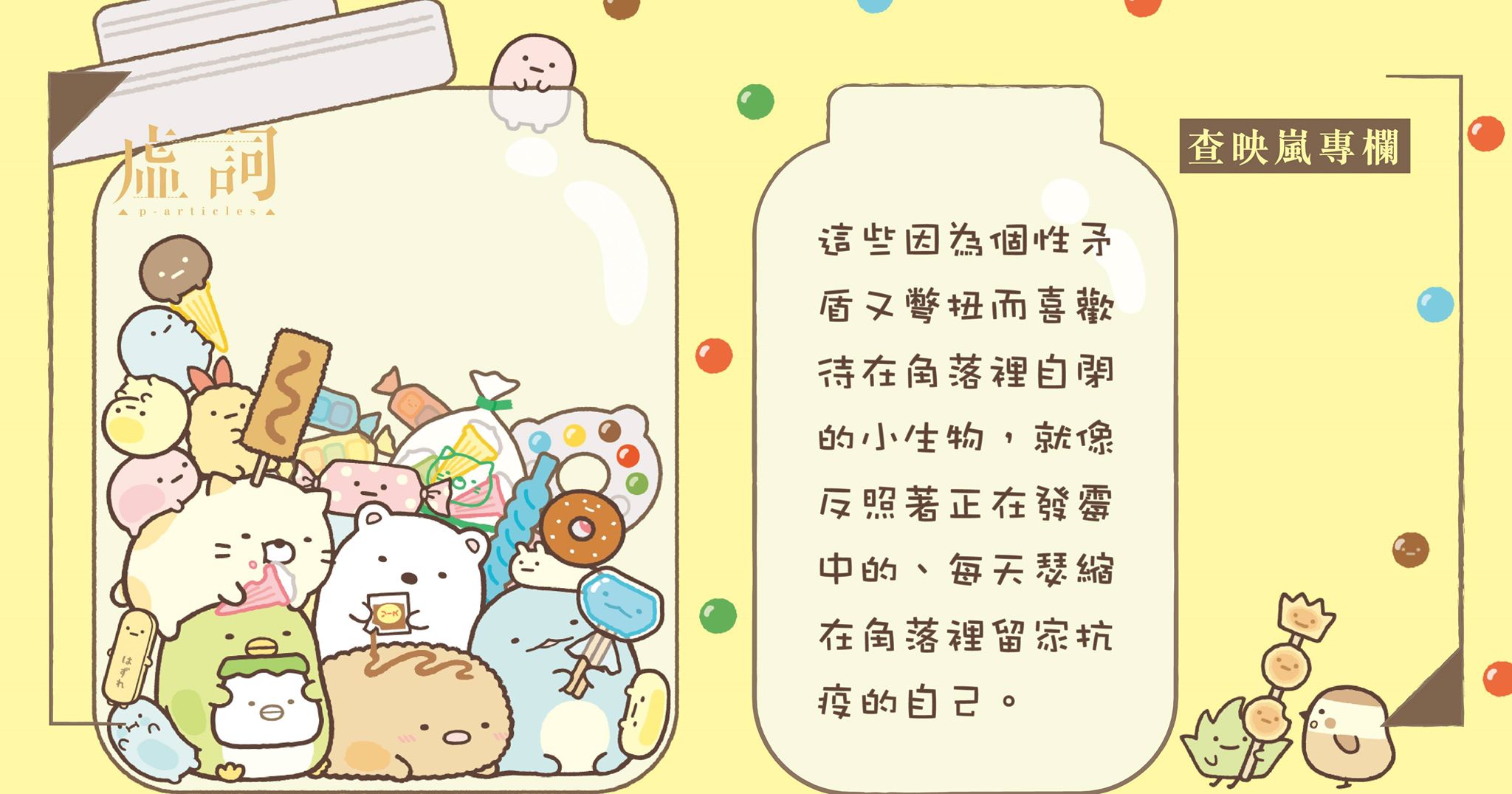【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像角落生物一樣活著
兩天前,我因為要覆診而久違地跑到九龍去,一不小心就從一家精品店將炸蝦尾帶回家,回去還給牠找了個舒適角落待著,自己一個在那邊美滋滋了半天。
想起來,如果我是早兩個月被圈粉,大概在《角落小夥伴電影版:魔法繪本裡的新朋友》上畫時就衝去戲院看了,不用現在後悔不已,瘋狂搜刮各種角落小夥伴精品小物泄憤。兩星期間,我已經買下了貼紙、膠紙、擦膠、儲物袋、水樽、毛巾還有炸蝦尾公仔;電腦的桌布換成牠們在咖啡廳吃點心的畫面;也積極考慮將社交媒體大頭貼換成小夥伴之一。明顯已經病得不輕,走上了狂迷的路。
角落小夥伴幾個主角都圓碌碌胖呼呼的,可愛當然可愛,但實在說不上很有特色;可是一旦湊在一起,成為一個小小部落,治癒度馬上急升;加上細緻而萌點滿滿的人設,更加令此作成為2020專屬的NO.1卡通。怕冷的北極熊、偽裝成蜥蜴的恐龍、實際上是河童的綠色企鵝、永遠被吃剩的炸豬扒邊和炸蝦尾.... 這些因為個性矛盾又彆扭而喜歡待在角落裡自閉的小生物,就像反照著正在發霉中的、每天瑟縮在角落裡留家抗疫的自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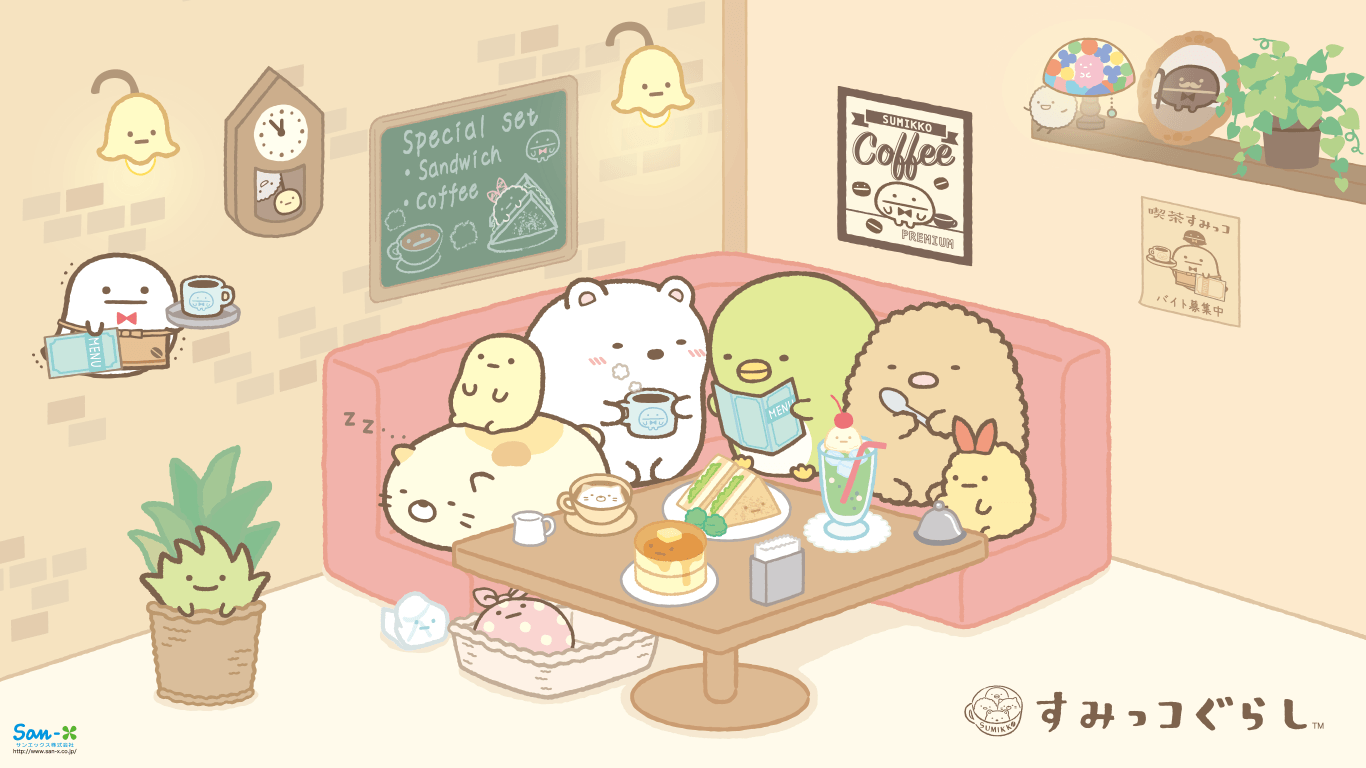
不能上健身房、不能上電影院、不能和朋友吃飯、不能旅行的角落生物日子,不知還要持續多久。這段時間,除了Netflix和其他日韓劇網(剛看完懸疑韓劇《十匙一飯》,準備開始重溫經典《悠長假期》),我的好朋友還有一堆之前買了沒空玩的電子遊戲。我這個從未擁有過遊戲機的中年女人當然不是典型的遊戲玩家(gamer),幾年前入坑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在衛報上讀到一篇文章,宣告電子遊戲可能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敘事媒介,而優秀的數位文學已經出現,我由此接觸到獨立遊戲的世界,並且因為想著要在雜誌做一期數位文學的專題而認真研究起來。最後專題沒有做成,我卻成為了一個非典型玩家,體驗了許多有趣的遊戲,像是《Her Story》(重組案情的偵探遊戲,又似是互動電影)、極低成本而爆紅的關員模擬遊戲《Papers, Please》、顛覆遊戲慣常操作的後設遊戲《The Stanley Parable》、偽裝成戀愛育成遊戲的心理恐怖作品《心跳文學部》、盛載台灣白色恐怖痛史的台灣作品《返校》…
最近,因為長期宅在家的關係,總算玩完了銷量達七十萬的獨立遊戲神作《Gone Home》,然後又在查找遊戲評析時後知後覺地發現,我最喜歡的這種遊戲類型原來被戲稱為「行走模擬器 (walking simulator)」——「行走模擬器」從誕生於「玩家門」爭議後續的蔑稱,漸漸變成常見於大眾媒體的語彙,這一個名字的變化跟法國繪畫中的印象派和野獸派不無相似之處。這類遊戲的共通點是多以第一身視角在遊戲環境中行走,多要求玩家細閱或細聽文本、著重氛圍敘事 (atmospheric storytelling),有時涉及大量針對環境的探索以達到解謎的目的,也有時是僅以角色的移動推進故事。
這些作品背離傳統遊戲中的戰爭或競爭邏輯,一些硬核玩家認為這些缺乏遊戲性的作品不配稱為遊戲,只能算是視覺小說、影像或互動藝術。雖然備受爭議,但自2012-13年《Dear Esther》、《Gone Home》、《The Stanley Parable》幾個成功作品推出後,行走摸擬器迎來了黃金五年;然而到了2017年,因為《Dear Esther》的開發商遣散所有員工並被收購,一些論者急忙宣布這個類型的沒落甚至終結。可是,如果說行走模擬器已死,我卻覺得2020年理應成為它復活的一年。在個體移動被規限的新常態中,這些遊戲容許我們進入異域行走,如同隨意門,它讓我們蹦入伏見稻荷大社(《Exploring Fushimi Inari》)、盛夏的日本鄉下小鎮(《Nostalgic Train》)、冰島的黑沙灘(《Mýrdalssandur, Iceland》)、英格蘭西部小鎮(《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身處這些逼真的3D環境,我們甚至可以無視遊戲性甚至敘事,單純而隨意地遊走探索,如同我們曾經熟悉的旅行一樣。
在疫症看不到盡頭的日子,暫時也只能以如此望梅止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