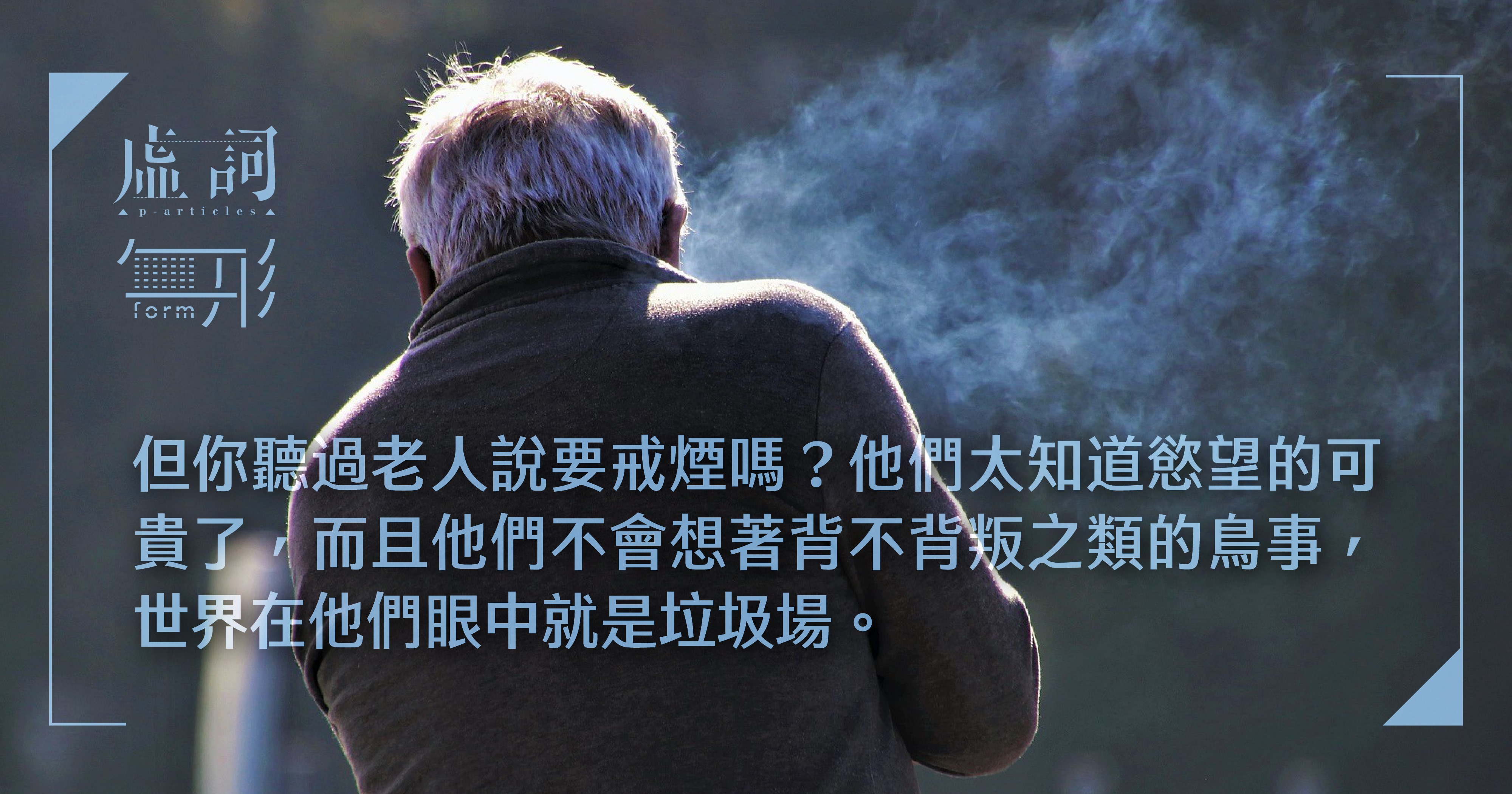【無形.見字__】見字戒戒煙
台灣清大有幾個吸煙區,大部份都在些鳥不生蛋的地方,停車場後面,垃圾房附近,但我也不能要求甚麼,一家大學有吸煙區已經對煙民釋出了最起碼的尊重,更何況我最常去的吸煙區位置不錯。人文社會學院的吸煙區是全棟建築最有活力的地方,教授或是碩博士生一天到晚泡在那裡,罵這個罵那個,一邊展示批判精神一邊把自己抽到神志不清。
吸煙區是個神奇的地方,因為人社院的人全都身懷絕技,語言對文科生來講就是積木,想怎麼拼就怎麼拼,於是這裡充斥著各種自稱戒煙的人。有人戒抽紙煙,這可以理解,但有人戒買煙,戒買火機,這就有點不明所以了。有次我吃太飽肚痛趕著去拉屎,十分鐘後回來發現自己漏在那裡的半包煙已被分乾抽淨,一群剛剛自稱在戒煙的人笑嘻嘻地望著我。自此我相信,清大吸煙區是走共產主義的。
問:嘴上說戒煙的人與共產主義者有甚麼相同之處?
答:他們都是些不尊重自己慾望的人。
說自己不再抽煙的人跟自願上山下鄉的人一樣,很快就會形容枯槁,看到有逃跑的苗頭就不會放過。世界已經非常淒慘,何苦還要欺騙自己呢。羅蘭巴特講過一段話很值得細味:他的夢想是在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裡移植一些中產階級生活藝術的魅力,難道把中產階級文化當作異國情調去享受也不可能嗎?
不過其實也可以理解,嘴上說戒煙的人們都想要變好,只要問他們為甚麼戒煙,他們就會像開清單一樣背誦器官的名稱:肺、胃、喉嚨、鼻腔、性器官,諸如此類。好像沒了那根小小的白色軟管,器官就能神乎其技地起死回生。你知道甚麼也能讓身體變好嗎?上山下鄉。
那都是想要讓身體變得更好的慾望,看太多Netflix或動畫了,裡頭個個八塊腹肌,能跑能跳能上游艇能左擁右抱,挽弓三百斤外加龍舟掛鼓。健身工業已經席捲全球,無人能敵,隨後就是瑜珈甚麼的,人人都說著只有肌肉不會背叛你,像個青春期女生痛哭流涕說不願再愛了。其實人到了六十幾歲後,因為長年過度訓練肌肉,腰背都會受損,在體態萎縮時痛得生不如死。
而退休才是真正需要戒煙的年齡,但你聽過老人說要戒煙嗎?他們太知道慾望的可貴了,而且他們不會想著背不背叛之類的鳥事,世界在他們眼中就是垃圾場,不用白色小軟筒把自己的靈魂抽乾還有甚麼意義?慾望最根本的元素,並不是想要向上變得更好,而是不想要被干擾,不想要被壓抑,被一連串狗屁倒灶的規條綁架。每次在吸煙區聽見一群猴子說戒這戒那,我都把煙丟過去,像在動物園丟香蕉。
我的好友老蕭,我剛來台灣時他的胃病已經嚴重得要死,接受訪問時記者還稱他病氣少年。他的喉嚨無時無刻都在胃食道逆流,活像beatbox。但他從來沒說過要戒煙,也沒聽他壓抑自己慾望還甚麼的,遊戲照打,KTV照去,最近他拿了我整年薪水總和的補助金,可以繼續寫小說跟出書。在清大吸煙區裡說自己戒煙的人一整天昏昏欲睡,沒事就說自己好累沒精神,好像上山下鄉時看著天空自言自語,然後又在偷我的煙抽時兩眼放光。菲利普.羅斯有本小說叫《我嫁了一個共產黨員》,又冗長又無聊,但有句話很棒:資本主義可行,因為它建立在人類自私自利的事實上,而共產主義不行,因為它建立在人類手足情深的神話上。而且那個神話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他們要說服人民相信,還得先把人擺到西伯利亞去。
人可以討厭二手煙,沒有問題,甚至可以叫我們滾蛋,去後巷或者垃圾房去,這都沒關係,這是我們應得的,壞習慣應該在壞的地方進行,人也不應該一邊演講一邊挖鼻孔。二手煙很差,二手的共產主義很差,大家都懂。但人絕不應該叫別人戒煙,這是情緒勒索,全是健身工業和現代醫學的陰影,像是長輩跑到你的房間裡評頭品足嫌三嫌四,又說這都是為你好。人甚至不應該說自己在戒煙,更不應該一邊說自己在戒煙一邊在吸煙區共產別人的煙。你是甚麼?健康告示牌嗎?「我在戒煙」是一個開啟話題的方法,而我拒絕再屈服於這些話語之下,不再回應「為甚麼」,不想再聽一長串的器官舉隅。後來我都這樣回應:抱歉,我戒戒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