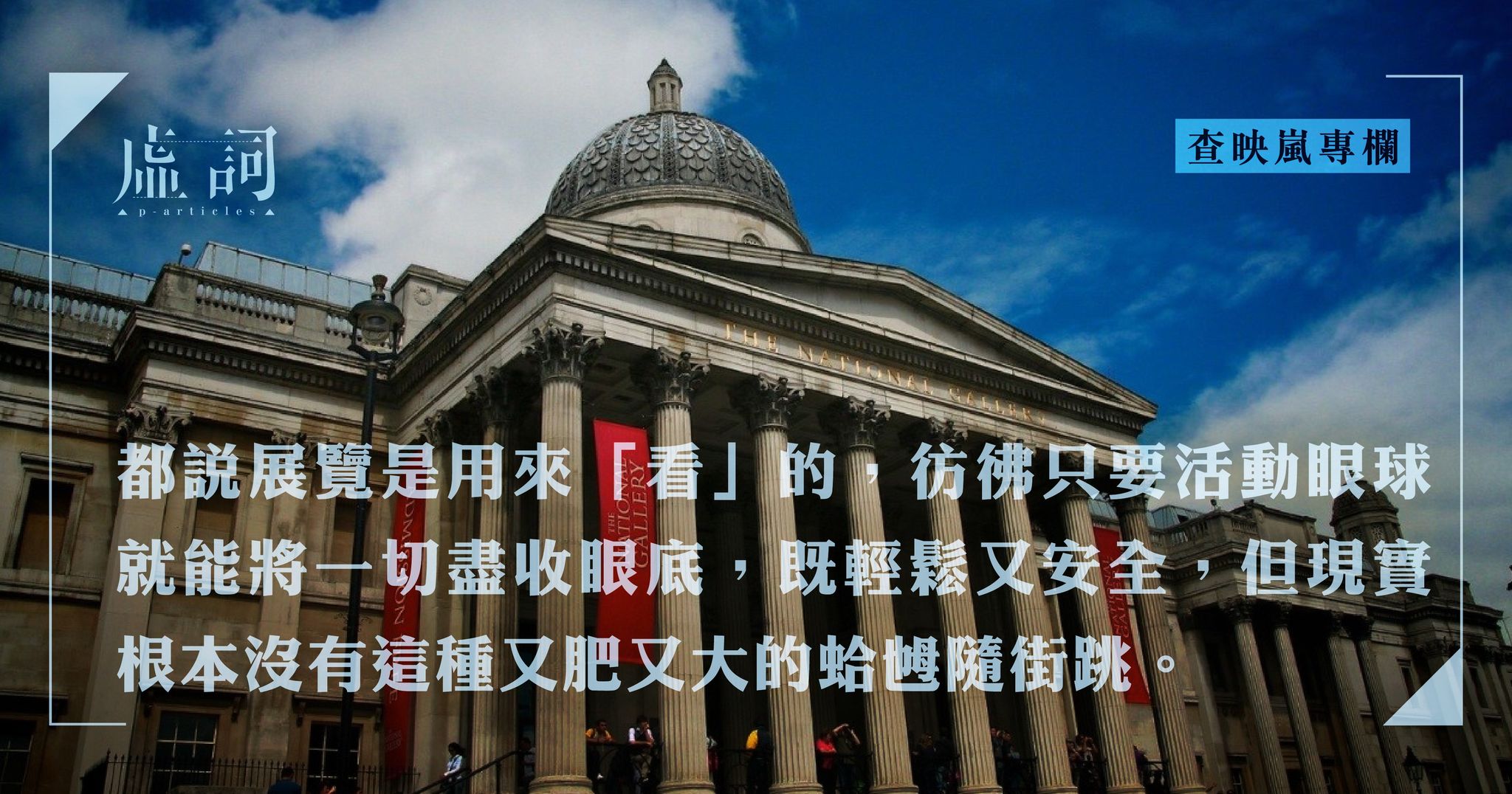【查映嵐專欄:火宅之人】做一日泥工
上周總算擠出時間看了藝術館的波提切利展。原本空出兩小時看展的,卻一如既往地遲起床遲出門,時間給砍去一半,就想可能要再來一回吧;結果展覽比我想像的小,人也沒有我預期的多,時間居然甚充裕,真是稀罕。
都說展覽是用來「看」的,彷彿只要活動眼球就能將一切盡收眼底,既輕鬆又安全,但現實根本沒有這種又肥又大的蛤乸隨街跳。巴黎羅浮宮、倫敦國家藝廊、馬德里普拉多美術館、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隨便挑一座世界級的美術館,都是體力大挑戰,比如冬宮,據說展覽路線有三十公里長,足夠讓村上春樹跑四分之三場馬拉松,沒有專人訓練的家庭觀眾光是走畢全程已經累死。不然去看那些當代雙年展、三年展、十年展吧;近年都流行放大量流動影像作品,參觀時也很可能要等影片演到尾才能從頭開始看一次,真要仔細、完整地看展覽的話,根本就是挑戰人類的體能和腦力極限。
歐洲的旗艦級美術館,大概從九十年代開始流行搞「超級大展(Blockbuster exhibition)」,反正就是荷里活大片的概念,策劃時間以年計算,投資額大(動輒超過百萬美元),運氣好的話收益也高,看這種展覽也往往累過擔泥。不用說,要保證不會出現入不敷支的災難,這種展覽的主角一定是名震天下的巨匠;畢加索、馬諦斯、草間彌生都是近年成功吸引數以十萬觀眾的名字,而這當中自然少不了梵高——宇宙最受歡迎藝術家(我猜測)。十年前,我還住在倫敦的時候,就曾看過皇家學院的梵高大展《The Real Van Gogh》。它real在哪裡呢,就是策展方以梵高的私人書信打開一些觀看作品的新角度,因此展覽不但擠迫得像年宵,更好死不死有大量巴掌大的褪色信件與畫作一併展出,簡直像在嘲諷現代人的視力。當年歷盡艱辛地看的展覽,到了今天只剩下在湧動人頭之間勉強辨認梵高筆跡的模糊印象。
這種展覽必定配以大型的宣傳活動,媒體和車站廣告總會不斷提醒你要預早上網訂票。我自己因為反應慢而且記憶力早衰,從未試過記得在預售期訂票,到開展後忽然想起,已經什麼都不剩了,只能親身跑去美術館門前排隊,所以在我腦海中所有超級大展均附贈排隊的記憶。其中一次是2010年巴黎 Grand Palais 的莫內大展,當時湊巧有香港朋友過來倫敦玩,便跟他說好一同去巴黎玩幾天,另一個重要任務當然就是看展。在巴黎,平日只要去 Musée d’Orsay 或 l’Orangerie,莫內想看多少就有多少;只是 Grand Palais 那次展覽的規模非比尋常,共展出160幅莫內作品,就算是在巴黎也很罕見,因此預售票早早售罄。當天我清晨便從hostel出發,抵達時隊伍不算很長,大概等了個多小時吧,展館開放後不久便進了場。因為人太多,進去後非得像吃自助餐一般,沿著自然形成的動線緩慢前進。最記得是展覽之大超乎想像——明明人家場地名字就叫 Grand Palais,我卻沒眼光地以為就是平常大概十個展廳的規模。看了兩三小時,感覺應該快完了吧,竟發現這才過了一半,最後幾個展廳幾乎是小跑著看,卻還是讓約好中午在龐比度集合的朋友等我許久。
不過,要數最誇張的一次,一定是在倫敦看達文西。當年從十一月開展就很想看,但每次經過都嫌排隊的人多,結果拖到第二年的一月底、在展期最後一周才去,也就是人潮達到巔峰的幾天。這種時候總是為自己的愚蠢再吃一驚。那個展覽的主題是達文西的米蘭時期,除了驚人地借到一些鎮館級的名作如 《抱銀貂的女子》和《美麗的費隆妮葉夫人》,又展出大量極罕的紙本素描,脆弱的紙本可不能經常展出;而這些還不是亮點,整個展覽的噱頭是兩個版本的《岩間聖母》歷史性地同時展出。這兩幅題目相同的大型油畫分別藏於倫敦國家藝廊和巴黎羅浮宮,因為作畫時間相距幾年,就算在達文西在世時兩幅畫都不曾打照面,而他們居然從羅浮宮借來了另一幅,所以那真的是大展中的大展。
我認真上網爬文,得知要在清晨七點半前加入隊列才有望買到票,於是在那宿命的一天史無前例地(除了趕廉價航班)五點五十分起床。倫敦的一月雖不至於冰天雪地,但那種陰冷也不能小看,因此我先套上絲襪再穿牛仔褲,上身罩三層衣服再穿厚大衣和圍巾,另多帶一條毛冷圍巾遮頭面;又因不想久站,我把房間的鋁製垃圾桶和一個咕o臣裝進宜家大膠袋中一併帶上。清晨七點不到,在日出前的薄霧中加入隊伍,因為怪不好意思的,花了好一點時間才鼓起勇氣將垃圾桶和咕o臣組合成櫈仔坐下,隊伍中的一些鄰居紛紛表示佩服。排在我後面的兩個男人一直在聊天,後來我才發現他們原來素不相識。其中一個滿活潑的三十來歲男子跑到前面數人頭,不久回來報告說我們的位置是二百多,應該沒問題。排了一個多小時之後,一個女人匆匆來到接力,男人趕忙去銀行上班,原來他們兩夫妻都沒有請假,打算就這樣輪流排隊。倫敦人畢竟是很有效率的也很精打細算的。
就這樣,從六點多開始,我們這幾個人輪流上廁所、幫對方買熱飲,儼然是好戰友了。但最重要還是我後面再後面的老伯,他把自己整個人生都講了一遍來娛賓:68歲的他是牛津郡人,兩年前從倫敦交通工程部退休,有個兩歲的小孫子,有個牛津大學抹大拉學院畢業的姐夫.... 甚至還扯到英國戰後的食物配給制度,可知我們真的排隊排了極久。事實上,我們到中午,等了五個多小時,腳趾全凍僵了,才總算買到票,那一刻我簡直想回頭跟戰友們擊掌慶祝,可是大家在不同的櫃枱買好票就默默散去了,後來在展覽中也沒有碰面。百年修來同船渡,一同在凜冽寒風中排隊五小時的緣份又是花了多久修來呢?
這些我都珍而重之地記下了。要是日後我成為什麼大人物,被好事者問到曾否為藝術犧牲,這就是我要搬出來讓他閉嘴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