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follow me】書寫時代,文學的回音——訪問李智良(下)
文藝Follow Me | by 李卓謙 | 2021-0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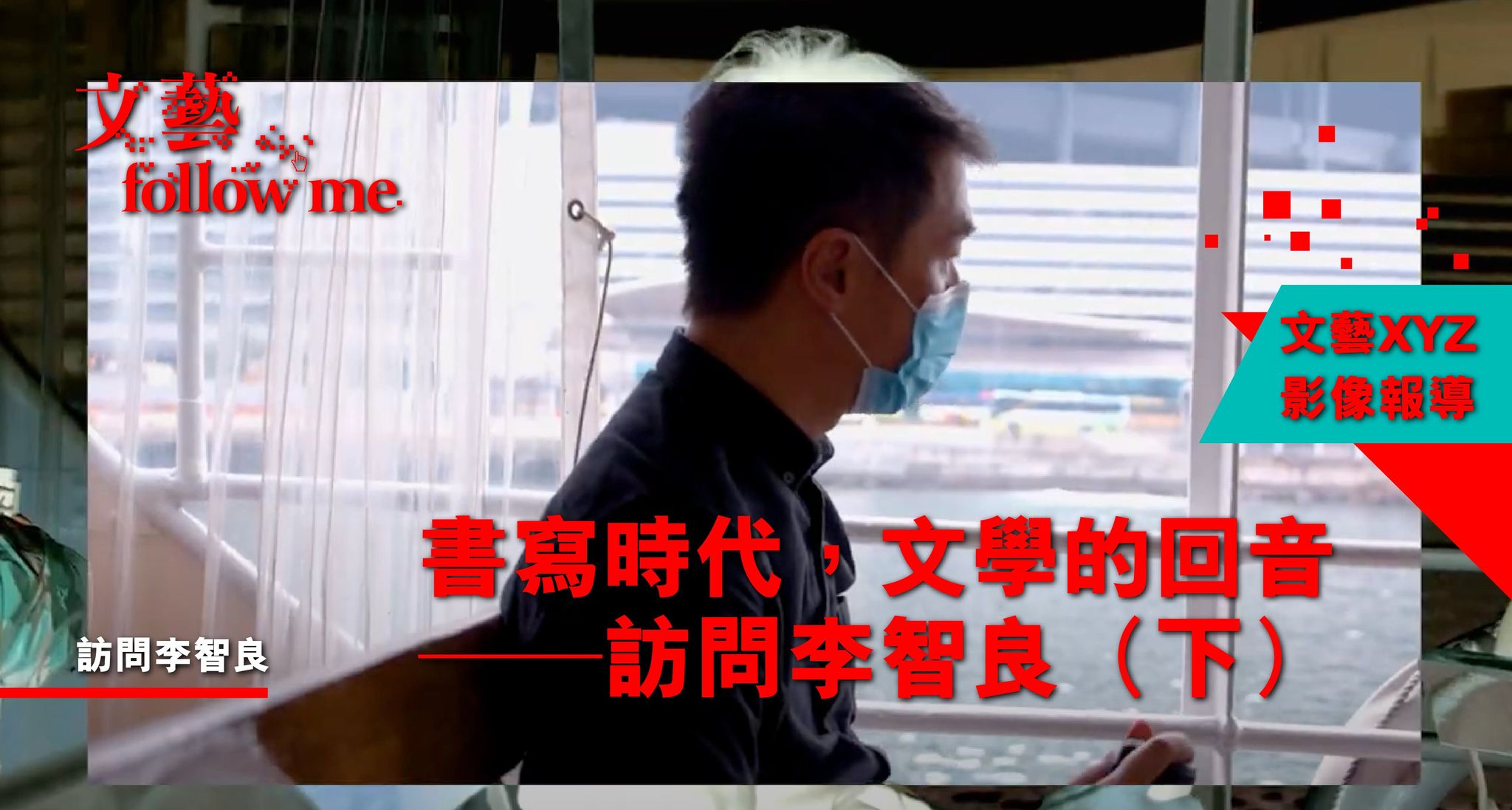
126510224_413378693368921_5136698798051507846_n.jpg
2019至2020年,香港經歷持續一年多的抗爭運動,曾經寫滿城市每個角落的標語如今雖被白油漆去,但訊息仍然烙在過路人的眼底。文學從來不是與政治無關,面對重大社會事件,詩人、作家自不然以創作回應,無論直接或間接,這一年間發生的事,都會是寫作者繞不過去的關卡。
然而,怎樣才叫回應社會、回應歷史,是個複雜的問題,距離如何拿捏,寫作者與被寫作者(如角色有原型)的關係,作者的權力等等,不是一時三刻能釐清,再加上,坊間以至學者有其對歷史的紀錄、保存、整理,文學又有什麼位置?
李智良認為作家較強調個人經歷,不一定將「大歷史」納入創作才叫回應歷史,「在這時勢下的真實情感、生活質感、遇到的人和事,我們日常生活很多細緻的感覺,都不是與歷史無關。」鑽進主流歷史以外的縫隙,展開對世界的描述與觀察,都是小說詩歌甚至藝術創作的可能所在。
文學如何回應
黃碧雲於2018年出版的《盧麒之死》引起過廣泛討論關注,當時是2016旺角騷動後兩年而反送中尚未發生,本書圍繞1966年由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引起九龍騷動,為首示威者青年盧麒被發現吊死於徙置區單位,死因存疑——「我們都害怕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我們沒有從歷史明白甚麼,除了情感。」(黃碧雲語)「原因不明」四個字,今時今日勾起我們太多聯想。
黃碧雲的書展示她對香港歷史的關注,大量挪用報章、檔案、報告、論文等史料,甚至遠赴英國查找檔案,雖然如此,李智良認為它仍然是「小說感很強的創作」,「她所關注,盧麒及其身邊年青人當中的情感關係,雖然我們稱之為社會事件,但它是由不同人的遭遇,無論是基於理想抑或巧合——有其內在動因——而倦入這場運動,當中有很強的情感面向。」
而使這本書與一般的歷史檔案、紀錄區別開來的,是書中的語言,「小說成功有部分因為她將原本是英文的資料,在翻譯過程中呈現語言上的跳躍,這種語言美感又能嵌入她原本的小說語言中,這已經不是狹義歷史家會做的事,小說家才會想到這樣做。」
「當然我作為讀者,我會期望黃碧雲在這小說中,將每個引用的資料都標明出處,那樣我覺得更加有趣,至少我會很好奇。」在小說中引用二手資料也是李智良的慣常做法,那是基於他對寫作倫理的思考,「如果我只為自己要寫故事,去採訪他人、拿別人的故事來用,當中權力是否平等呢?有沒有令對方都有種……說得偉大些叫『充權』,有沒有令對方的聲音被聽見,有很多考慮我自己還未拿捏到準則,所以會用二手資料,亦會標明出處,有種開放原碼(open source)的感覺。」
香港文學的位置
歷史告訴我們,極權的影響可以滲透到生活每個層面,它首先搗毀的是政治制度、選舉制度,然後是教育,之後可能是出版、語言、文化。所謂「大灣區文學」在近幾年偶有耳聞,文學可能有天也會成為爭奪的場域,智良認為那不全是文化政治的包圍,「商業社會本身的運作已經在把你淘汰,發行商大書店本身就是一條龍操作,在文化領域的佔有率覆蓋率比起獨立出版團體大很多,問題是我們怎樣在這巨大的不平衡中拉近差距。」
智良認為香港文學不能太故步自封,「要跟香港本位的文化歷史論述有更多有機結合,而不只是維持一個自己的文學圈,令到更多人可通過文學找回香港經驗。」智良期望有更多不同經驗能被納入香港文學的體系中,例如少數族裔、文化資源沒那麼強勢的聲音或創作,「香港經驗不是只有廣東話,香港不是只有華裔或白人,如果說寫廣東話才叫香港文學其實是自己限制自己。」
他提醒我們卡夫卡的經驗,一位使用帝國語言(德語)創作的捷克猶太人,「他在德語中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語法很奇怪,但正是這種奇怪的書寫方式,某程度好像hack進了主導語言中,令到德語出現變異,這是他成功爆破開的文化空間。有時我覺得香港文學,跟整個大範圍裡的華語書寫,都可以是這種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