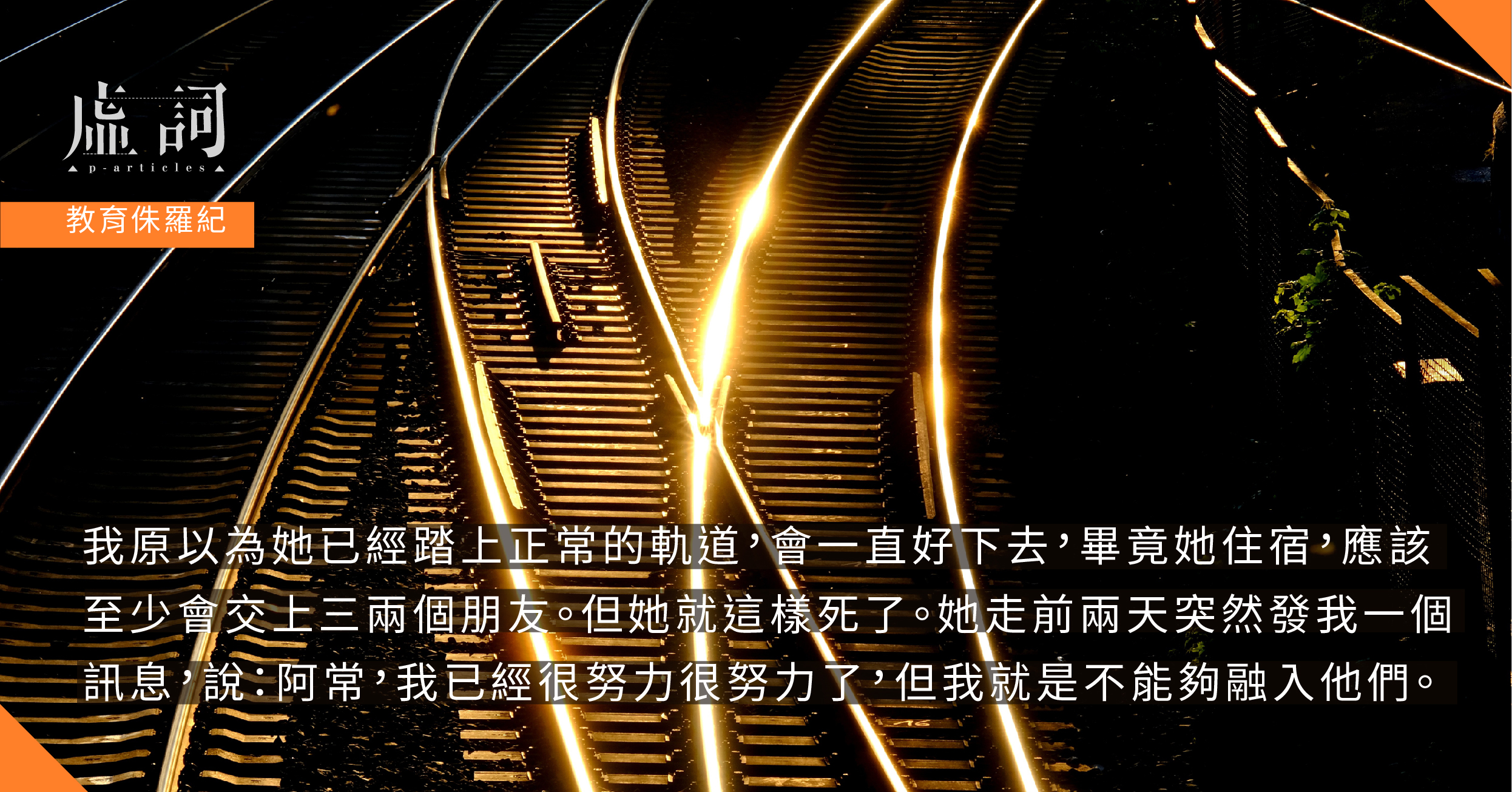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學生成長】失群的雛鳥
「(本報訊)今早十時正,大學一年級生於沙田火車站跳軌身亡⋯⋯」我一面讀著瑤的死訊,一面哼流行曲。車窗外是幾幢外牆剝落的唐樓。一群雛鳥在空調上棲息,只有一隻麻雀不斷繞著附近的樹飛。
我和瑤中四開始交往。其實我由中一至中三也從未與瑤碰過面,畢竟我朋友多,鮮會主動認識其他班別的朋友。她束馬尾,頭髮梳得整齊,瀏海未及眉,活脫脫是個恪守校規的乖學生。開學首天她主動坐在我旁,向我鞠躬,微笑並以稍微沙啞的聲音道:你好,我是瑤。我有禮地點頭,心想這個女孩真是傻。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起來,談些無聊的——大概我們之間就不可能有甚麼有趣的對話——然後慢慢熟絡起來。
瑤經常借筆記給我,又跟我分享小吃,沒甚麼不好,但就是太乖,乖得有點笨拙,不懂轉彎,有時好心做壞事,整天繞著耶穌的道理走。
那時全校最麻煩的Miss Lee教我班英文。她就是那種每天化濃妝、盤髻、穿高跟鞋上班,未踏進課室便用尖利的高音說good morning class的老師。每當有人發出聲音,她就用校簿大力拍枱,嚷shut up naughty kids。有一次Miss Lee拍枱,阿明站起來說,好喇喎老嘢,你拍夠枱未,惹得同學格格大笑。Miss Lee立即冒起火來,赤臉,嚷shut up。之後阿明繼續和老師「嘴炮」,Miss Lee不夠聰明,不懂回擊,便使出女人的絕招——可憐地哭。下課後,我看見瑤悄悄地走到外面給Miss Lee遞上紙巾。那時好像只有我看到這情景。我沒跟她説什麼,只是覺得她人很好,但就是有點多管閒事。
有一陣子「碟仙」遊戲十分流行,班上的同學總圍攏在課室的角落悄悄地玩。其實我心裡是有點恐懼的,但因為幾乎所有同學都一起玩,我當然也參與。他們在白紙中央畫一個腦門突起的骷髏頭骨,然後用裝蘸的白色碟子在骷髏臉上畫眼睛和嘴巴,再以數字圍著骷髏頭骨,最後把碟子放在頭骨嘴巴上,向神靈叩問。最調皮的阿明發出詭異的叫聲,班上的女同學便咿呀鬼叫,在課室的沙發上亂跳。這時,瑤悄悄走來,搔著頭,溫和地道,抱歉,你們玩這個可能會使同學遇見邪靈,引致不安,你們還是不要玩這個吧。阿明隨便拋出一句,我知,我知你講耶穌,然後繼續玩。瑤只有呆呆地回到座位。瑤就是這樣,太乖,又太多事,像一隻雛鳥,時而向其他雀鳥吱吱叫,顯得有點愚笨。
偶而瑤也會參與班會活動,但我想對其他人來說,瑤來與不來並沒什麼分別。每回玩「真心話大冒險」塗改帶指向瑤時,瑤都會笑著推搪,說自己真的沒喜歡任何人,十分沒趣。其他同學也不勉強她,就重新轉動塗改帶,繼續遊戲。瑤便繼續在我們中間蟄伏如透明的鹿,一言不發。我當然十分識趣,即使沒有拍拖也會胡亂編一個故事,譬如自己在小學時追了一個架著黑色粗框眼鏡的圓臉小子多年,有時又會寫千字的情書放在他的抽屜裡,在門外靜觀他的面部變化,然而他不領情,冒出一句「是誰個傻子寫的」,把情書扔進垃圾桶。這故事常逗得同學捧腹大笑,阿明不斷拍掌,讃好啊好啊,而瑤也是跟著笑,靜靜地笑,由吱吱叫的雛鳥變成安靜的麻雀。
放學後我們班經常到附近的公園消磨時間,初時我會拉著瑤一起去玩,但她總是低著頭説母親著她要早點回家,六時半吃晚飯。於是後來我便索性不邀請她,直接跟大伙去公園,反正無人介意瑤來不來。有一次我們在公園不知因為什麼原因談到瑤。阿明説,瑤是個「耶L」,整天講耶穌,又扮乖,擦老師鞋。你看,老師總是對她笑。我心裡其實想為瑤討回公道——她並沒刻意奉承老師,只是她太乖,又不懂轉彎。但當然,我沒把話說出來。
之後一陣子,好些同學終於因玩「碟仙」、「筆仙」等神靈遊戲而「撞鬼」。聽說他們整天都反白目,時而嘔吐,時而不受控地顫慄,弄得同學提心吊膽。幸好我沒有撞邪。瑤知悉這事後,好像社工姑娘般走到同學旁,拍他們的肩,溫柔地安慰他們。大部分同學都只是微笑道謝,唯獨阿明起了很大反應,指著瑤的鼻,瞪著眼說,你不要説風涼話,你又沒有參與我們。
那天放學後我和瑤一起乘巴士回家。途中瑤倚著車窗,悄悄地抽泣。我不知如何是好,便一直按著手機螢幕。突然她別過臉來,怔怔望著我道,阿常,對不起,我想請教你一件事,究竟我做錯了甚麼,使阿明要這樣待我?
我跟她說,阿瑤,你不是做錯,只是你有時太乖。我心底裡其實想説她乖得太愚拙,但最終沒說出來。
瑤愣了愣,又説,阿常,乖有甚麼不好,聖經教我們要聽從神的話,為甚麼阿明不喜歡乖。我想,班上另一位同學阿恆不也是基督徒嘛?又不見他整天講耶穌。但我怕她受傷,因此沒有說話,只是笑了笑。
中學畢業後,我們入讀了同一所大學,但因為所讀學系不同,宿舍又不同,而且我又要忙上莊、參加ocamp、hall events,因此不常聯絡。大學後我甚麼都很好,朋友很多,GPA一直維持在三以上,沒什麼需要憂心。上一次看見瑤已是三個月前的事。那次我在學校飯堂吃飯時,瞥見對面有一群學生圍著垃圾筒抽煙,而中間那個女孩就是瑤。瑤竟然染了一頭金髮,手捏著煙蒂,吹出一輪輪煙圈,教我差點就認不出她來。那時我想,傻妹終於變正常了。
之後我也沒再看見瑤了。我原以為她已經踏上正常的軌道,會一直好下去,畢竟她住宿,應該至少會交上三兩個朋友。但她就這樣死了。她走前兩天突然發我一個訊息,説,阿常,我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但我就是不能夠融入他們。或許她就是一隻懵懂的麻雀,不懂跟著群鳥飛,只會呆呆地待在枝頭,吱吱亂叫,漸漸失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