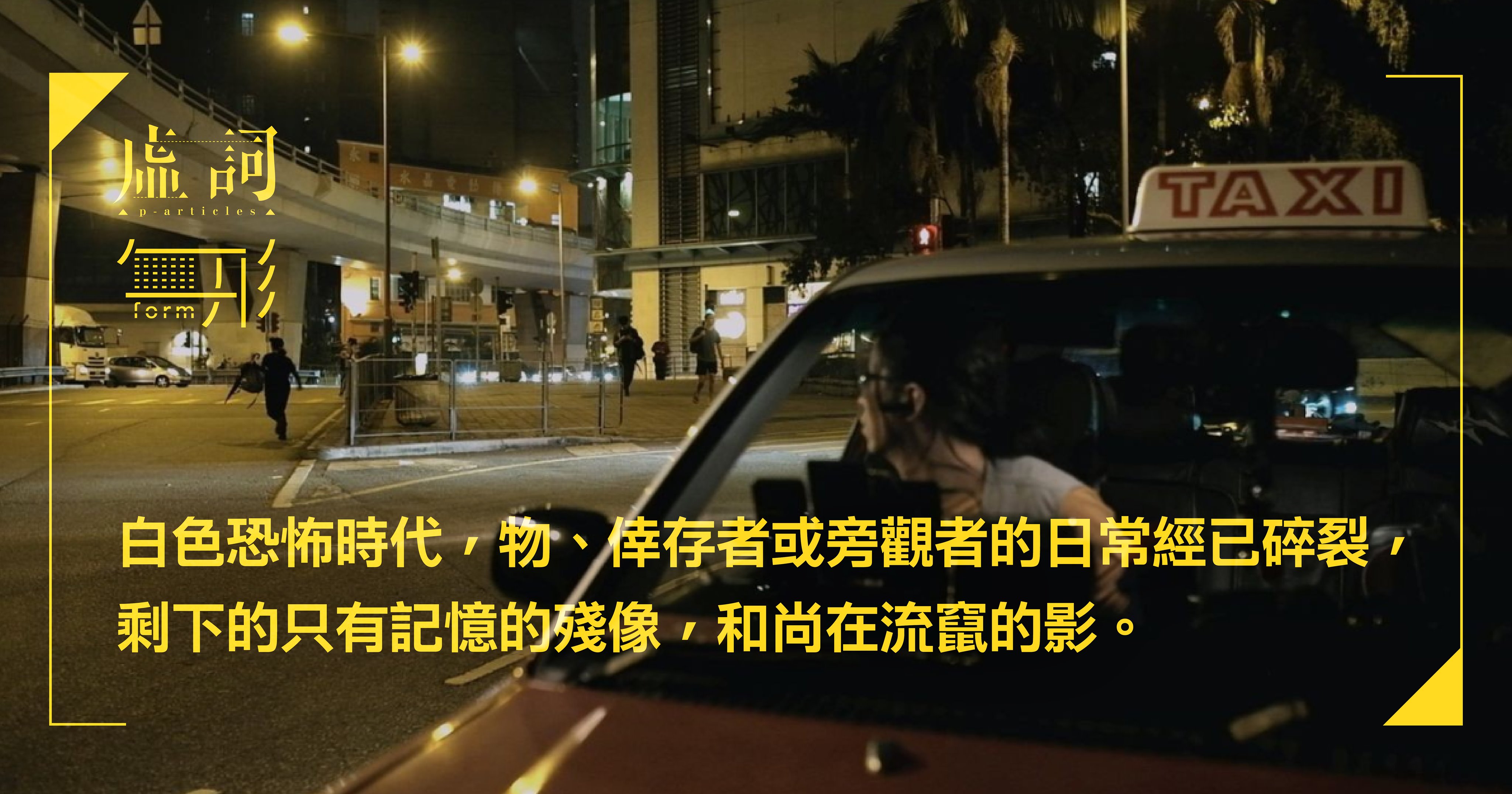【無形.初登無形也不驚】光影殘像,斷裂日常:(後)運動記憶與創傷
街頭硝煙散去,塗鴉痕跡隱沒,然光影殘像仍像幽靈縈繞城市,抗爭記憶在體內傳衍留駐,成為無可消除之傷。《我真係好_鐘意香港系列》從不同角度書寫城市創傷,包括倖存者的愧疚,旁觀者的游離,去與留的掙扎,物的見證,以及惡托邦的想像。本文將以周敬勤《天暗亦明》、姚仲匡《暴動之後,光復之前》和郭臻《夜更》為例,從倖存者、物和旁觀者三個角度,看電影如何回應反修例運動的記憶與後遺的集體創傷。
幽靈迴盪,倖存之傷
「創傷理論」批評家嘉希.卡露思指,創傷不同傷口,它依附思緒而非身體。創傷是二次的:因事件強烈度超出情感負荷,受創者無法全然接納或經驗它;事後,事件或影像才回來糾纏他,這也是佛洛伊德說的「遲發作用」。卡露思亦指出,因記憶只能以碎片形式返回受創者,線性敍事和再現是不可能的。
《天暗亦明》敍述受創女子移居高雄後的情感狀態。電影始於一個燈光忽明忽暗的房間(圖一)。導演以慢鏡和深藍色濾鏡,拍攝她在夜裡用被單蓋過自己,嘗試不讓燈光影響其睡眠,但不果。這房間可被解讀為女子因倖存、離開香港而生的幽閉、壓抑的情感。即使後來男子修理燈膽,房燈仍然載明載滅;無論如何,生活依舊失序。這樣的空間詩學使我想起《尋人啟事》裡姊姊走過迂迴隱閉的樓梯的一幕,那幕同樣以深藍色為基調,與日間的鮮色形成強烈對比,予觀者憂傷恐怖的感覺。《天暗亦明》其後不斷呼應這幕,譬如仰望天空時,女子說「星星有時候亮,有時候暗」,再次點出她和城市失序的狀態。
圖一
創傷有陰魂不散的性質,以執意的複製與回轉不斷困擾主體。運動中抗爭者常面對猝不及防的驚嚇,感官變得異常敏感。稀鬆日常裡,碎裂影像在受創者的體內流淌,任何外物都能擠壓他們,引致內爆。導演以閃回敍事與手搖鏡頭處理女子的創傷。當她在夜市裡用玩具槍
指向氣球時,歷史夢魘、往小巷逃跑、被警察壓在地上的光影殘像返回她的身體。另一幕裡一個小孩用玩具槍指著女子,她一再受驚,是為再度創傷。
短片亦準確刻劃倖存者的愧怍、憂傷和焦慮。在首幕,當屋主問女子來台灣做甚麼,女子欲語還休,房燈瞬即熄滅;女子又多次告訴男子「我並不這樣值得幫」、「其實我並不是那麼好」,盡是無法理順的憂鬱與離開的愧疚。當男子說他知道了她的祕密,她眼神游離,雖未言明,觀者也能感受她對別人知其往事的焦慮,及離開香港的掙扎。影片節奏頗緩慢,多運用長鏡頭,伴以悲憫的音樂,創傷就在異地的日常裡細水長流。
斷裂影像,殘酷物語
當現實沉重婉轉不可說,便只能讓物替我們言說。
《暴動之後,光復之前》導演指他因無法在抗爭期間拍攝,只能拍下事發後散落街頭之物,譬如護目鏡、拆去欄杆、被撕毀的連儂牆,將這些空鏡頭排列成短片。劉以鬯的《動亂》同樣以物作為敘事者書寫運動,裡面的物像對事件懵然不知,無法與世界溝通,譬如電車說「我不知道為甚麼要在此犧牲。這裏邊應該有個理由。我不知道」。
姚的短片裡,死物皆有自己的聲音,會與官方論述角力。銀行外牆的玻璃能反駁「抗爭者暴力」之説,拆開城市華美的外皮,指斥資本主義的結構暴力(圖二);催淚彈殘骸駁回「催淚彈擁有最高權威」的論述,指出抗爭者不會因其後退;有些物更描述抗爭者的情緒。黃藍字體的互換,兩種歷史敍事交鋒,激昂貝多芬四重奏響起。微物影像還原歷史真相,又召喚觀者的憤怒和悲憫。這些物都是感官之物,或曰肉身的變異。沿用黑格爾「自然哲學」的說法,當我們將抗爭的記憶與情感投射於物,它們便變得靈動,成為有情的歷史見證者。
圖二
物即鬼魂。黑白影像,說明事件已成過去。但歷史記憶迴還往復,幽靈般投向物的內核。一幀掛著標語的天橋照片浮現,另一幀群眾人像照片和細雨紛紛的畫面即以紛呈、溶疊形式滲入,彷彿魂兮歸來。另外,四重奏響起時,群眾的呼喊以畫外音形式隱隱滲入,使我想起瑪格麗特·愛特伍<這是我的照片>末句,已浸死的「我」再度返來,事件性的碎片在「現在」不斷回歸受創者。引張美君博士在《幻魅都市》提出的理論,運動過去以後,電影中的無源聲逼令觀者聆聽無法看見的東西;它是後創傷的,如鬼魂般重返歷史現場,訴說抗爭故事,但這並未標誌經驗完結。
比起《天暗亦明》,姚的短片敍事更為破碎、跳躍。用約翰伯格的語言來説,一系列有關物的影像都是從連續時間擷取出來的碎片;蒙太奇鏡頭間存有「空白」與匱缺。短片裡照片溶疊時常常出現裂痕,好像破鏡。線性敍事不可能,一切脫離線性條貫,漫漶向四處溢散,這或許能用來解讀短片碎散敘事結構。作為觀者,我們只得在斷裂的照片中找尋刺點,並隱隱作痛。
時代夾縫游離的旁觀者
抗爭者面對創傷時,旁觀者如何在時代邊緣遊走?
(後)反修例運動的文字和影像大多聚焦熱血的前線抗爭者。電影如《理大圍城》紀錄抗爭者被圍困理大的經驗,以鳥瞰鏡頭反思權力結構與創傷,作家如梁莉姿在《字花》連載的日常運動系列主要書寫抗爭者的街頭抗爭經驗,及在時代邊界游離、垂死掙扎的情感狀態。
《夜更》罕有地以政治立場曖昧的的士司機角度切入,寫實地再現城市小人物/旁觀者如何看待運動,他和抗爭者的傷口在其車途一一攤開。短片先以近鏡拍攝的士司機點煙,吐出一連串流利粗口,寫實地呈現他對運動阻礙維生的不滿,並開展他與三組乘客的互動。第一位乘客是一位「衝衝子」,載她時,他一邊觀看手機直播,一邊碎碎唸。司機座的視鏡象徵他的視角,當他從視鏡看見女孩換上黑衣裝束,他輕輕蹙眉,表情冷硬。從這個用特寫鏡頭拍下的微細動作,就算司機最終沒有道破,我們也能猜到他的生存哲學——維持生計後才談公義理想(圖三)。
圖三
車途行進,我們看見司機更立體的形象。當兩個大媽誤信「前線洩慾天使」一說,他立即糾正她們,她們也不甘示弱,叫他不要盲撐,最後更斥責他是「死黃的」。黃絲認為司機是藍絲,藍絲又覺得他很黃,他就在這樣尷尬的夾縫中游走。
第三組乘客是萍水相蓬的男孩和女孩。導演又以特寫鏡頭拍下司機聆聽男孩暫無居所的對話時目光游離,頭左右移動,時而皺眉的微細表情,隱隱流露他對男孩的惻隱。其後當男孩問他借水,少有地温柔道「後面有新的,取新的吧」。男孩下車後,司機點煙,降下車窗,在黑夜凝看纖瘦的男孩背影變得細小,男孩用借來的清水洗臉,放下背包,躺在公園長椅上(圖四)。電影最後一幕與此境相似:司機點煙,在白天觀看孩子奔跑、結伴,嘴角微微上揚。這些緩慢的觀察式鏡頭,伴以現實雜音和黃耀明「早餐派」,埋藏司機淡淡的同情,以及生活在變態日常的少年之傷(圖五)。
圖四
圖五
司機與女兒通話時,他表示已為女兒打算,供她出國留學,女兒則想留在香港。這段失序的對話,表達父女溝通的不可能,也折射出父親對女兒的愛。這一幕教我想起蘇朗欣<蒜泥白肉>裡「陳師奶」到壁屋監獄探望哥哥的場景:「頭髮短了,眼圈更沉,隔着玻璃他們都沒有把對方看很清楚,和昔日一樣」,他們親密而疏離的關係和《夜更》刻劃的相像。
《夜更》混合了現場錄像,坦誠地呈現城市旁觀者的日常肌理,並折射香港的憂鬱。透過微細的動作及表情,再現小人物在運動中立體的情感狀態,沒有一味批判,也沒有蓋過他者聲音。漫長黑夜裡,我們觀看著司機觀看的視角,面對仍在淌血有傷口而無以接近,一直走到天亮。
白色恐怖時代,物、倖存者或旁觀者的日常經已碎裂,剩下的只有記憶的殘像,和尚在流竄的影。在黯淡無光的夜晚,讓我們細聽宏大敍事以外的歷史見證,凝視埋在亮麗無垢的城市的血淚痕跡,傳遞這一代的記憶及文化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