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旅遊
其他 | by 何福仁 | 2019-0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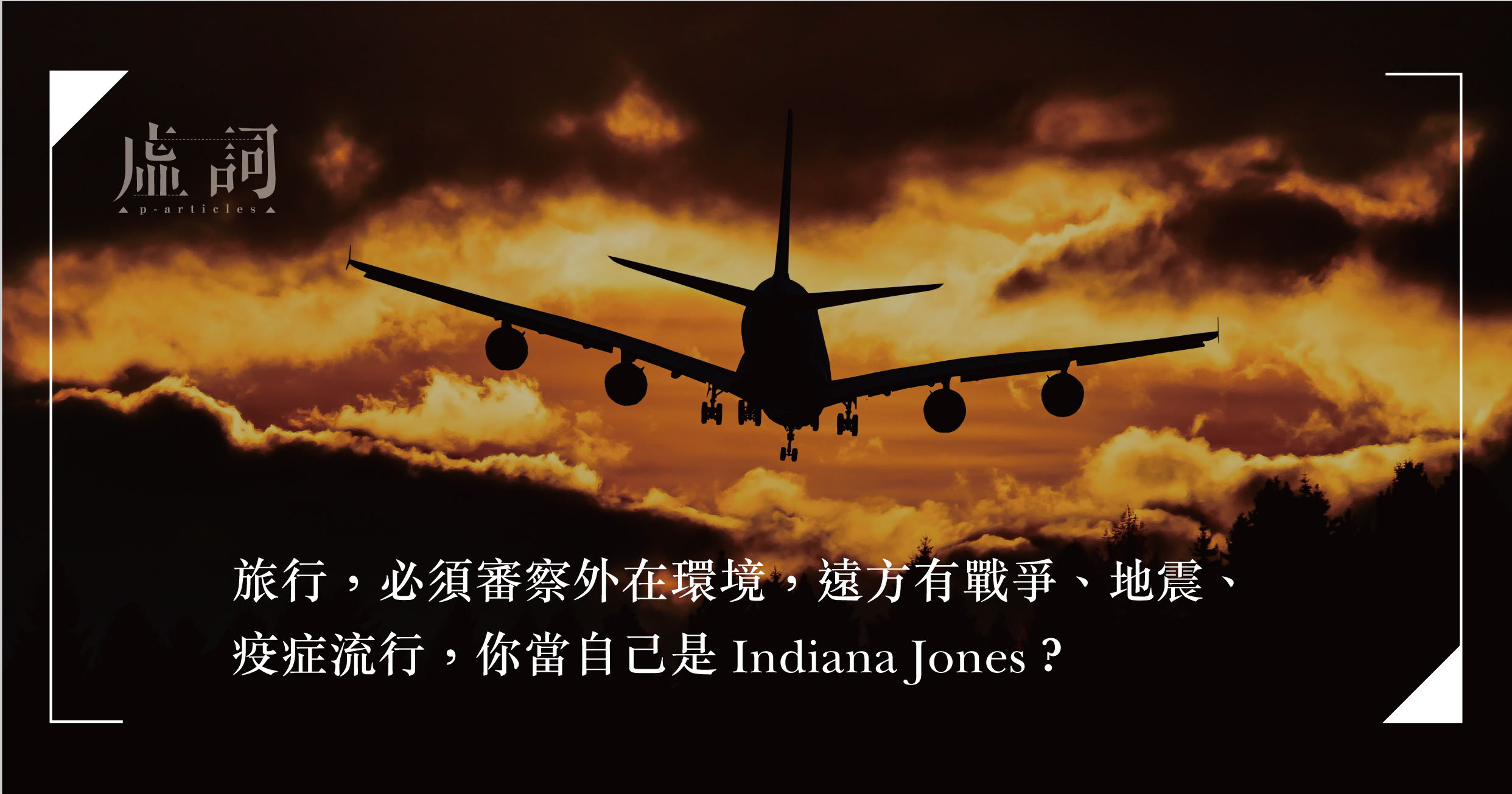
不知哪一位哲學家說過,人類的一切煩惱,源於不肯乖乖地呆在家裡。對了,哲學家大多不喜歡旅行,也不會旅行,他們的旅行,用的是腦袋,而不是雙腿,他們像植物,用腦袋在地上倒樹葱地偷偷移動,他們關心的是時間遠多於空間,那是思考月圓月缺對人類的意義、研究日照的善意來自甚麼的根源、生呢還是死。所以出門時他帶備了各種藥丸,應付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失眠、抑鬱,而往往忘記自己的耳朵和鼻子,牙齒呢,還留在漱口的水杯裡,至於眼睛,別提了,他大後天還要做黄斑裂孔的手術,之後就得伏躺個多月,更不能出門。甚麼是伏躺?Lie face down,明白了?到時,他會理直氣壯地碎嘴:誰再說我坐井觀天?
說這話的哲學家,大概就因為出門後遇上煩惱,有感而發;他忽然兩行鼻涕裙腳仔那樣想起家。家裡如果沒有一個多敗兒的慈母或者嫌丈夫沒出息的惡妻,本來就是一切煩惱的避難所。外面,空氣混濁,人多車多,真可怕呵。然後,一無例外,他把自己的問題哲學性地放大。他固然不可能一下子就遇上一切的煩惱,何況離家後,每個人類的煩惱,不可能盡同。一位小說家的小說,開章明義就指出: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戶戶相異。他不過寫了兩三戶人家的煩惱,已經厚得像過去的電話簿。
但問題是:乖乖地貓在家裡是否就沒有煩惱?揭穿了,無非是人類持續地生產的廢話之一。出門是遠慮,在家是近憂。沒有煩惱,還是人類嗎?你以為變成田裡的百合花,就可以豁免煩惱?你可知道,那麼漂亮溫柔,好像與世無爭的百合花,連上帝都不吝讚美,實則病質厭厭,有軟腐病、腐敗病、鱗莖腐爛病、花葉病、萊姆病、炭疽病;蟲害有根壁虱、蠐螬。誰能保證沒有登革熱病,伊波拉病、愛滋病?你以為,家裡的貓就沒有煩惱?牠絕少出門,寧死不出門,牠天生是宅貓,但六歲後牠從室內欖球不得不改玩地毯滾球;八歲,終於告別球壇;十歲,牠變成一樽閉上眼的瓷磚。
旅行,必須審察外在環境,遠方有戰爭、地震、疫症流行,你當自己是Indiana Jones?更要看人內在的心境、人的精神狀態、人的健康狀況。若干年前,路上碰上一位四十年前的舊友,聊上兩句,他看來有病,而且是重病,卻計劃坐飛機到十萬八千里外,因為有甚麼人甚麼機構要給他一個禮物。危險啊,我說,不,不是禮物危險,禮物充其量是雞肋,而是不宜坐長途飛機,飛機起降時艙內壓力變化,會影響身體功能。病人,其實不宜旅行,遑論遠行。他當然不聽我的,哈哈大笑。之後,再沒有看見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