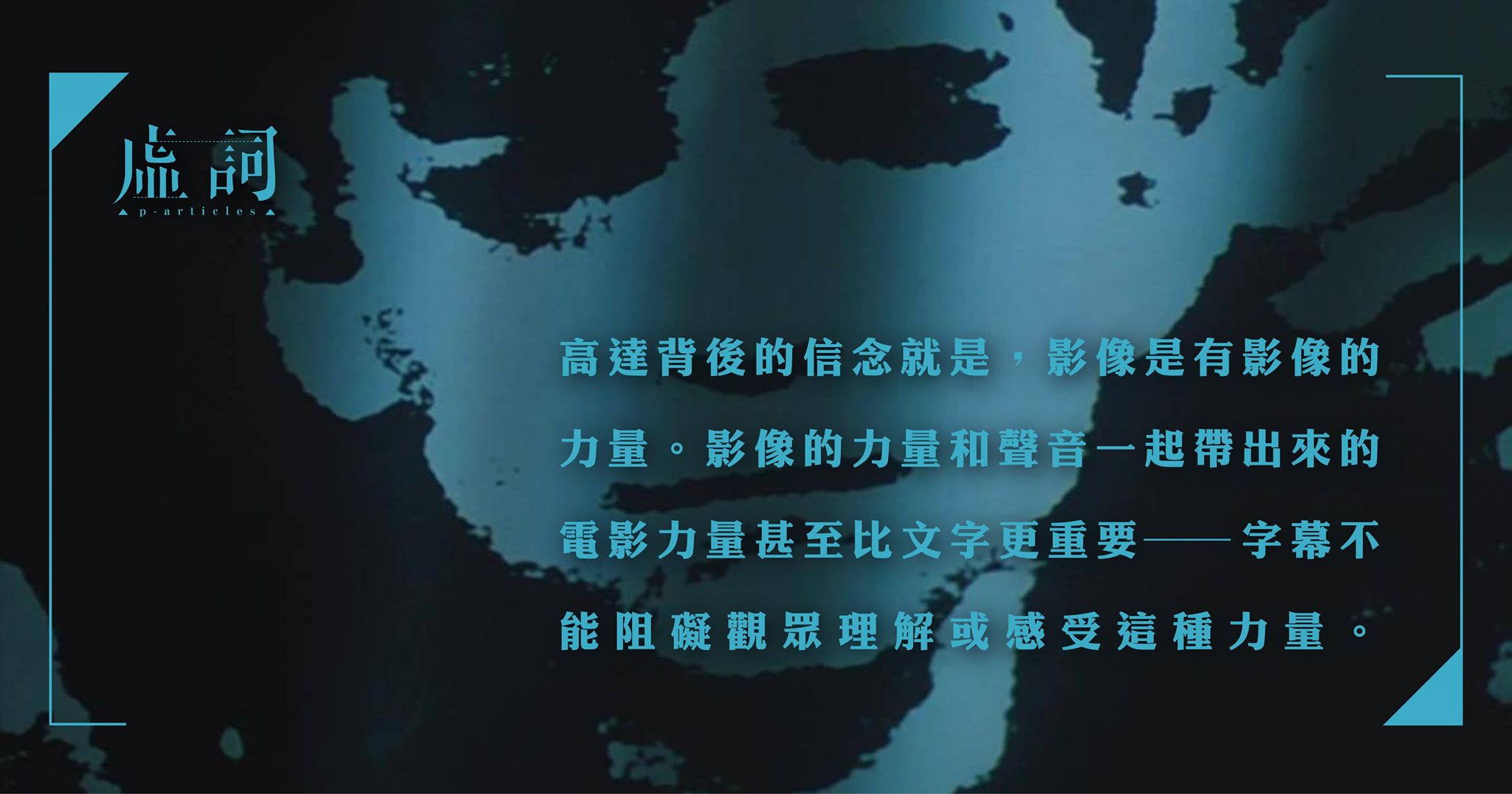究竟,我們為甚麼還要看高達?以晚年高達的作品為重心的「高達.電影.歷史」課程剛圓滿結束,第二部分預計將於今年年尾面世。《虛詞》訪問了負責籌備及執行該次課程的香港國際電影節藝術總監王勛先生以及資深影評人朗天先生,嘗試好好地回答這道重要的問題。放開懷抱感受影像的力量,是欣賞晚期高達的首要條件,而這亦是課程的重點之一。 (閱讀更多)
白雙全《噩夢牆紙》新書發佈專訪:打破輿論世界 找抗爭與藝術之間的平衡
白雙全的新書《噩夢牆紙》,雜亂和檔案式的呈現相互交錯,秩序若隱若現,就如創作者本身的精神狀態一樣。經過多年掙扎,他現在已非常清楚自己藝術的價值。面對將社運相關的藝術視為「消費」的這種聲音,白雙全並不置可否。那是他對自己的創作的自信,也是他對整體社會的信心。 (閱讀更多)
香港絕種——訪葉曉文《隱山之人 In situ》
「我開始寫這本小說時,就決定要寫香港已消失的物種。」以本地自然生態為主題出版短篇小說集《隱山之人 In situ》,葉曉文(Human)透過文人角度欣賞大自然,理性之餘亦多了份感性。創作建基於親身經歷的感覺,Human重視的是如何「在地」研究生態,並對大自然懷有恭敬和謙虛之心。 (閱讀更多)
城市研究者黃宇軒:沒有欄杆的街道或者更好?
「我自己也有幾次這樣的經驗--『咦,為何街道好像變得好走了那麼多?』,原來是因為沒有了欄杆。」城市研究者黃宇軒(Sampson)說。早前有民間規劃組織建議政府考慮不要重裝圍欄,藉此重新審視路面空間的規劃,Sampson也認同,現在是一個機會,讓我們重新思考本來習已為常的「規矩」。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叛侶》專訪:離場後你的選擇是?
專訪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12-20
在整個戲劇觀賞過程中,劇場不會主動告訴觀眾答案,亦從未批判「偷情」,而是在於觀眾當下經歷到些甚麼、作出怎樣的選擇。兩對情侶兩段經歷,同時存在於舞台上,一對有出軌,另一對卻沒有,導演陳敢權於是追問,「你會選擇哪一邊?」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