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訪孟浪:共同面對我們無法避讓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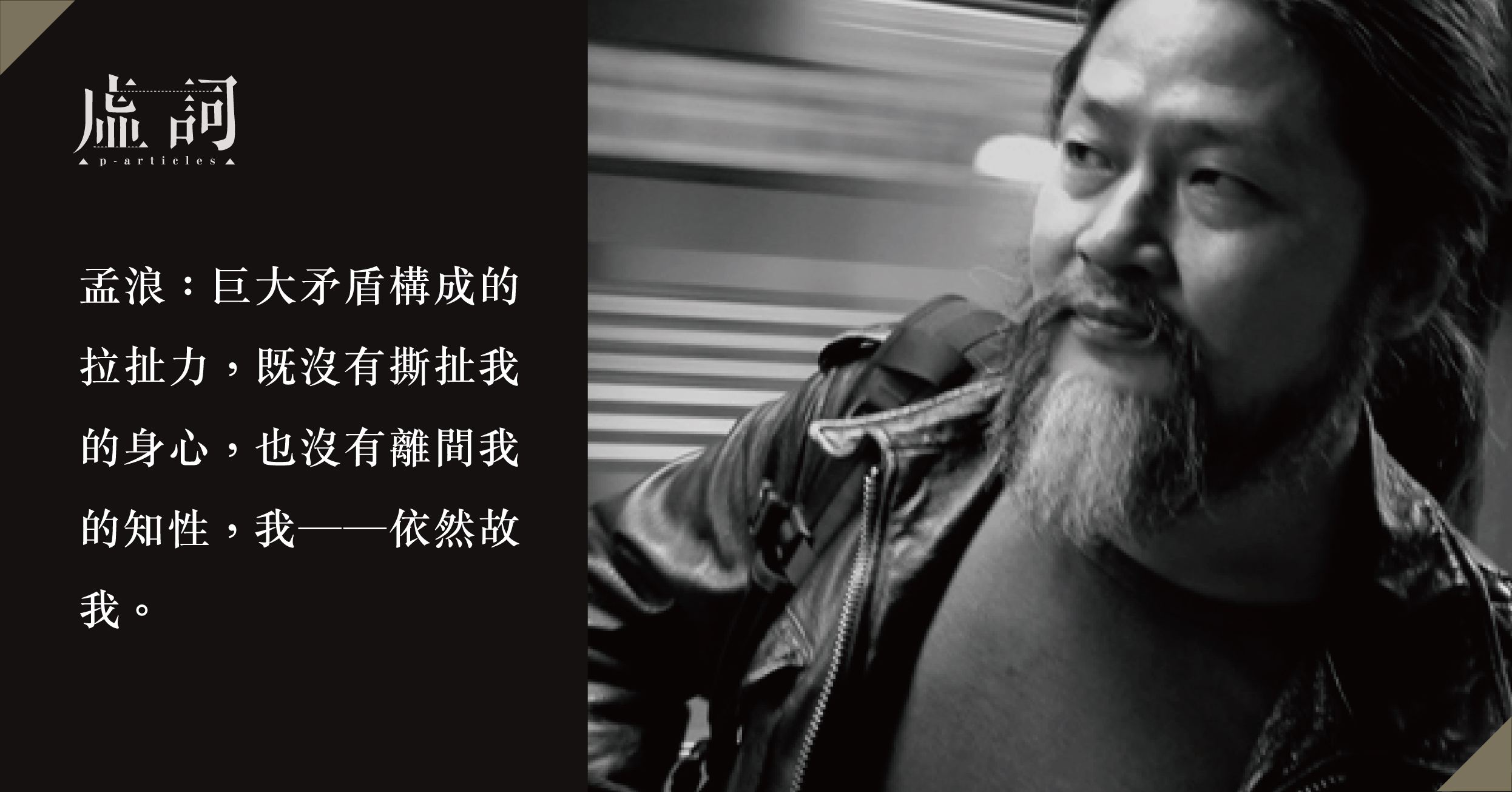
孟浪-04.jpg
【編按:2018年12月12日,詩人孟浪先生因病離世。2016年,作者因一份功課訪問孟浪,從而促成了這次筆談。這篇紀錄,也是孟浪對於離散身份、在異地寫作的貫徹思考。】
2016年,選讀「離散文學」課程時,有份功課要求我們訪問一位離鄉人,我立即想到在香港、美國、台灣來回奔走的上海孟浪,於是撰寫了一些簡單問題寄給他。彼時在美國的孟浪竟很著緊於我這小小學生的一份功課(也是他一貫的認真作風),來往電郵數次,巨細靡遺地回答了每一個問題,又發來許許多多參考資料,生怕還不夠,也令一開始沒有做足準備的我既慚愧、又感念。
在這幾個小問題間,孟浪闡釋了作為永遠的異鄉人,如何在故土情結、國族問題、身份矛盾與認同中自在遊走——正是不間斷的、形而上的思考與寫作使他自由。身兼作家與編輯兩個身份,孟浪曾略帶自嘲地說,在創作中自己是命定的「探險者」與偶然的「受難者」;而做編輯時,卻又充滿了包容與同情。這些難以調和的個性特質,到了他身上,卻都又「服服帖帖」地與生命合成一體,凝結成與每個人滔滔不絕地談天前、那一句孟浪式的問候:「怎麼樣?最近還可以嗎?」
問:促使你離開中國大陸的原因是甚麼?之後又去了哪些地方?
孟:離開中國大陸是1995年9月,當時我應美國布朗大學的邀請前往該校,任在英語系設立的一個自由寫作項目的駐校詩人,這是直接的原因。潛在的背景性原因則是,我已不耐於、深倦於在中國的作為一個自由詩人所不得不迎擊的制度性窒息和壓迫,一半是自覺、一半是被迫,我選擇了離開。
我在位於美國羅德島州首府普羅維登斯的布朗大學待了一年半多。因自1993年以來我一直在參與執編《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出於編務工作的需要,在駐校項目結束後,我就搬到了雜誌編輯部所在城市——波士頓。我在大波士頓的幾個不同城市地區都居住過,直到2002年,自那一年起,有四年時間,我開始在波士頓和香港之間來回駐留,還由於尚未取得香港長期居留許可的原因,不得不經常在香港、澳門、台灣之間騰挪。自2006年年底開始,我主要在香港居住;2015年夏天起又遷居到台灣住下。
我回答你問題的這個時間,距離我離開中國正好差不多二十年零六個月。
問: 那麼對你而言,「離鄉」或者「故土」還是一種情結嗎?四處遊走之間,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又是如何的呢?
孟:曾經有過「離鄉」或「故土」之類的情結(哪一個「流放者」、「離散者」沒有呢?)但在目擊中國(和中國「價值」)千禧年前後及至今「紅霧」般的崛起和彌散(「我被嗆到了!」)之後,我對那一片「故土」已經產生巨大的離異感和不適感——它是物理性、病理性、心理性三者兼具的。
最近幾次我與朋友們聊天時說,我是一個中國詩人,也是一個香港詩人,現在我正在「學習」成為一個台灣詩人。
你覺得我對自己四處遊走間的身份認同看得很重嗎?【黃按:孟浪式俏皮反問,我們總是記得。】
問:有沒有什麼人事、物件觸發你想起故鄉?
答:少年時光。
【黃按:孟浪還在電郵中附上2009年刊登於《今天》雜誌的文章——〈上海徘徊:失去了過去的未來〉。在這篇文中他對自己的年少生活、上海身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自述。以下為選段摘錄。】
「我分明記得,大約是1973年,12歲的我在農村外祖母家的灶間熊熊燃燒的爐膛口,緊挨著我的一位表親舅舅,看他一邊熟練地添弄著柴火,一邊與來自四公里外縣城的我闊談我們那個縣城(當時屬上海市寶山縣)所處與黃浦江出海口交彙的長江口岸(我們當地俗稱『海塘』)的未來。當年他是當地人民公社屬下一個生產大隊的民兵營長,25歲上下,意氣風發,見識也算不少,他告訴我,聽說離縣城僅一箭之遙的長江岸邊將興建國際客運超級碼頭,他興奮地展望寶山的巨變。這可能是我的記憶裡,上海的『國際化』前景直接觸碰我視野中地理性存在的第一次悸動。距今35年過去了,那個曾令我的少年有所遐想的國際客運超級碼頭的藍圖並未在那裡實現(是否有過這樣的藍圖,對我至今是謎)。」
「我自小長大並在那裡接受中小學教育的縣城——寶山(今上海市寶山區),在上海市區的北翼,黃浦江口(吳淞口)與長江口的交匯處的西側,距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路程約25公里。記得小時候,我們那裡的大人小孩從來都說『到上海去』,指的就是從我們縣城出發去上海市內的“征程』……『外地人』和『鄉下人』因『大上海』都市身份的缺失,而被視作『低人一等』。我常常憶及一種心理性的窒息感,於是,『我的上海』的誕生,與幻滅,此時就成了同義反复的毫無意義!多年以來面對『你是不是上海人』的提問時,我常常答道:我不是上海人,我是上海鄉下人。此刻,這不是上海的光榮,而只是我——一個與『上海』不合作者——作為『不是上海人』的光榮。」
——〈上海徘徊:失去了過去的未來〉
原載《今天》雜誌2009年春季號。該文的意大利文譯本,2008年11月發表於《Dialoghi Internazionali》第8期。
問:城市對於外來者總有著自己的「接受度」——是否在意過這一點?有沒有文化差異等問題曾經產生過?
答:我去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我會喜歡遊蕩於由土地、街道和人構成的有機人文場域,而對所謂自然風光常常感動在後,或「無動於衷」。我覺得我並不在乎一個城市對自己的「接受度」,更介懷的是我對它的「接受度」。我常說在我數十年的詩創作中極少、極少看到具體地理城市的名號和痕印。我一方面很願意感受「在地」、經驗「在地」、甚至成為「在地」的一份子,另一方面,卻很多年以來「拒絕」刻意地書寫「在地」、再現「在地」,而有一種認知上的傾向就是超越「在地」。文化差異或者種族問題,因著我一以貫之的「世界主義」(或「普世主義」)視角和觸角,在我倒通常不作驚詫而狀似「絕緣」。
大中華沙文主義的「國族認同」觀在我們的成長經歷中曾嚴重傷害了我們本應正常持有的認知。談論世界上一些城市與城市(旅行和休閒)趣味上、意態上的異同變得文雅而安全,那是在中國,於中國而外的我,則更多的是無視「城市」、無視「國家」,而關切人作為大地上的一種存在,他(她) /他(她)們的共同面對的無法避讓的命運。
問:您曾說在選詩時特意看看有沒有粵語成份的詩,對於您來說,會投入一個地方的時下詩歌流派,還是會選擇與其保持距離?
對你最後的提問,我用我在六年前的一個講談中一段話來回答:作為詩人,作為作者,同時作為編輯——一方面,作者的我,可能從來是美學上的絕對主義者、極端主義者,文學觀念和創作實驗的命定的「探險者」與偶然的「受難者」;另一方面,編者的我,必須具有高度自主的、獨特的文學鑒賞力、判斷力,卻同時又對各類作者作品的風格與趣味(不管我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持有足夠的包容心和同情心。
問:在異地,不同的語言或文化環境,對您的創作以及思考方式帶來怎樣的影響?
答:在異地,當然你所指的一定還包括異國或異域。在我身上發生的一個非常「反動」的事實是,至今我只是使用所謂「國語」在進行文學寫作和閱讀活動。不同語言或文化環境對我的影響只是一個大地上的「漂流人」的世俗感受或衝擊;我的形而上的思考和寫作,一部分「靈感」激發來源和在中國時期大陸一樣,仍然主要來自於極少數精粹的、卓越的漢語作品和其他語言文學、思想等翻譯作品。
而越來越顯豁的事實還是,我的生活與寫作樂於學習落地深耕的同時,也在更義無反顧地離地千里,這樣的一種巨大矛盾構成的拉扯力,既沒有撕扯我的身心,也沒有離間我的知性,我——依然故我。
後記:
孟浪逝世後,旅美評論家李劼重刊一篇詩評〈舉石拋羽的詩歌搖滾——簡評孟浪詩集《南京路上,兩匹奔馬》〉。或許由於兩人有著相似的離散背景,李劼也將關注點放在了孟浪的流浪背景上:「沒有在美國流浪過的人,很難想像流浪是一種甚麼樣的生活……有關孟浪的流浪,幾年前,我只聽他在電話裡這麼說過一句:在美國過了八年,一言難盡。」從流浪中的繁瑣事情與難以想像挫折中艱難生長,才有了我們現在認識的開豁、通達的孟浪;同時這一種(生理的、心理的)流浪,也是一整代人的命運。
這篇文章還引用了孟浪的一首詩,名為〈我們身體裡的……〉,也可視之為一幅「自畫像」:
歷史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生命。
生命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光榮。
光榮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鮮血。
鮮血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那就是我們的道路。
道路在我們的身體裡旅行
旅行就在我們的身體裡結束。
在我們身體裡的
只是(他們潔白的骨頭)不屈
只是(他們圓睜的眼睛)希翼。
在文學和他鄉跋涉,節奏必須急促而有力。這場浩大的旅行最終回歸進身體,卻絕不是最終——我們相信有一種循環往復的變化,正在這些詩歌裡積蓄能量。
孟浪簡介:
原名孟俊良,1961年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紹興。1982年畢業於上海機械學院,於大學時期開始文學創作。係《海上》、《大陸》、《北回歸線》、《現代漢詩》等多份民刊的主要創辦人之一,為1980年代中國現代詩群「海上」的代表性詩人。1992年獲第一屆現代漢詩獎。1995年赴美,應布朗大學之邀任駐校詩人(1995-1998)。曾任《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執行主編(1995-2000)。2001年在美國參與創辦獨立中文筆會。現居美國和香港兩地。著有詩集《本世紀的一個生者》、《連朝霞也是陳腐的》、《一個孩子在天上》、《南京路上,兩匹奔馬》、《教育詩篇 二十五首》等。合編《中國現代主義詩群大觀1986-1988》、《詩與坦克》;主編《六四詩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