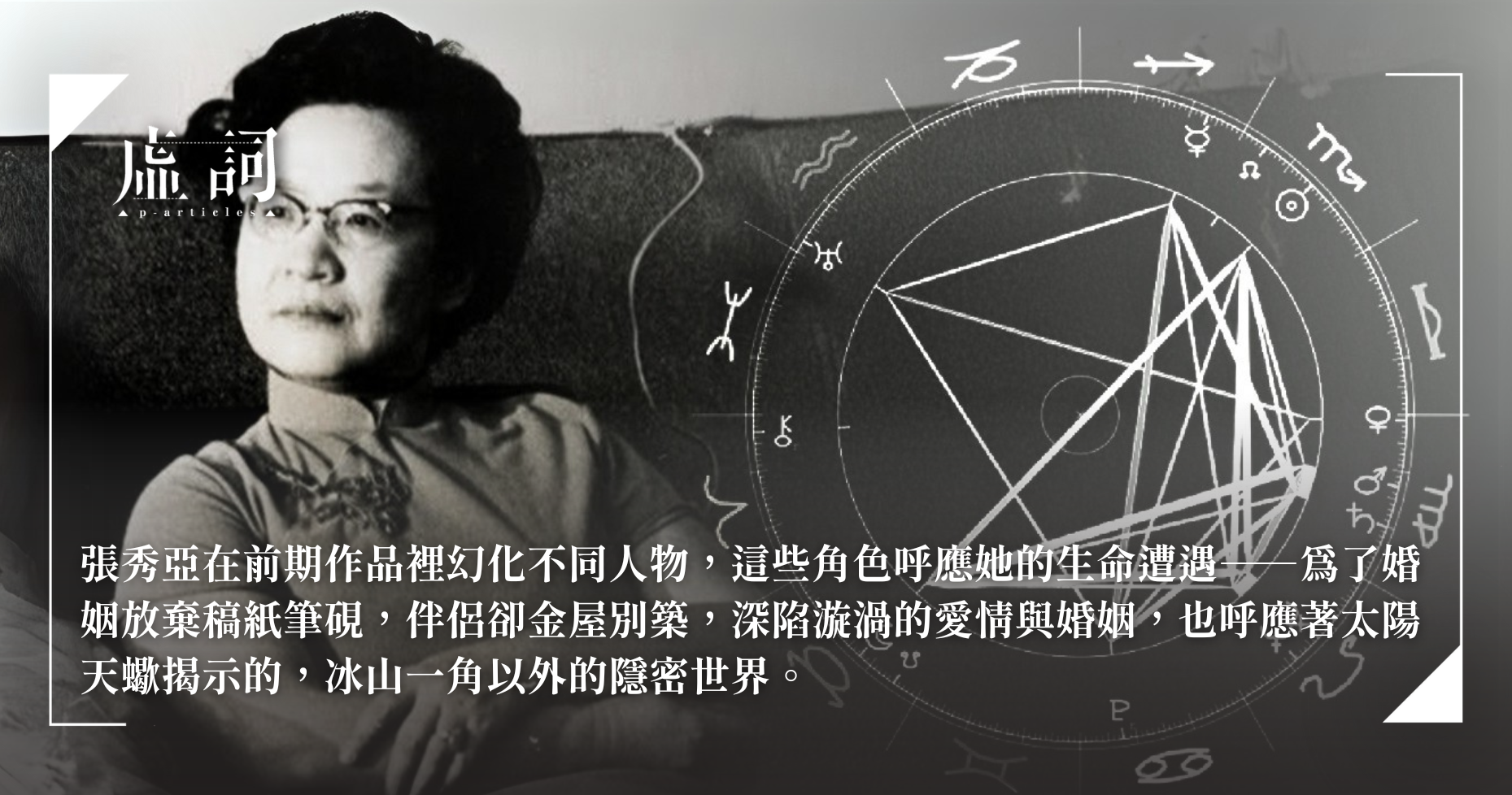淺談《富士山下》與《在青木原的第三天》歌詞中的生死修行
其他 | by Cléo | 2025-05-21
Cléo傳來歌詞評論,認為陳奕迅主唱、林夕填的《富士山下》與吳青峰給何韻詩填詞的《在青木原的第三天》,兩首看似無關的歌曲,均在歌詞中暗藏對「生死修行」的叩問。前者,林名仿佛化身觀音陪伴傷心人在絕望中放下執念;後者則以隱晦意象勾勒出生死邊緣的徘徊,從回憶的微光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兩首歌雖風格迥異,卻都指向同一個核心——音樂如何成為痛苦中的一線生機。 (閱讀更多)
從《殺人回憶》到《米奇17號》:奉俊昊鏡頭下的階級困境與救贖辯證 ft.《不安擴張:論奉俊昊》
其他 | by 黃于真 | 2025-05-02
奉俊昊新作《米奇17號》在台上映前夕,北美韓國電影學者田鍾琄的《不安擴張:論奉俊昊》繁體版率先面市。黃于真指出書中透過細緻的影像解讀與理論框架,精確指出奉俊昊對韓國乃至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階級矛盾的深刻關照。因此黃循照《不安擴張》的批判視角出發,來探討奉俊昊最新作品《米奇17號》與過往創作哲學的異同。 (閱讀更多)
為什麼綠色是電影裡最孤獨的顏色?
其他 | by 一只 | 2025-04-09
綠色作為我們日常生活裡最常見的顏色,一只認為當其出現於電影當中,便會有著特殊的含意,更將其稱為電影裡最孤獨的顏色。一只例舉出不同的電影作品,包括《德州巴黎》、《花樣年華》、《22世紀殺人網絡》等,解釋導演如何透過綠色營造出虛幻、疏離、空虛等曖昧效果。 (閱讀更多)
我們忘不了的盧國沾 黃志華X陳智德X朗天細味名作金句
其他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03-31
被譽為「詞壇聖手」、香港早期「三大詞人」之一的盧國沾於3月19日傳出離世消息,享年76歲。盧國沾自1975年開始填詞生涯,創作了眾多電視劇的主題曲歌詞;盧國沾的題材相當廣泛,涵蓋武俠、家國情懷、抒發鄉愁、人生無常等,成為幾代人的經典。為紀錄盧國沾對香港樂壇的貢獻,《虛詞》編輯部邀請了藝文界知名的評論人黃志華、朗天、陳智德,分享他們印象深刻的盧國沾歌詞,細味詞作與人生交織之境。 (閱讀更多)
唯一的大同
方大同逝世的消失,相信眾多歌迷都仍未消化。林喜兒傳來懷緬方大同的文章。方大同對上一張專輯已是2016 年的「JTW 西遊記」,原本計劃在2020再推出新專輯,因為COVID,也因為個人健康問題,最終在八年後《夢想家》才面世。很多人對這張專輯作事後解讀,說是告別生命。其實透過音樂串流平台的介紹,方大同已告訴我們,在對抗疾病的過程中,繼續他的創作與夢想。「I wanted to turn my weakness into strength and create an album I could be proud of」。與其說是告別,不如說是久別重逢,記錄了他在這段日子的心路歷程。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