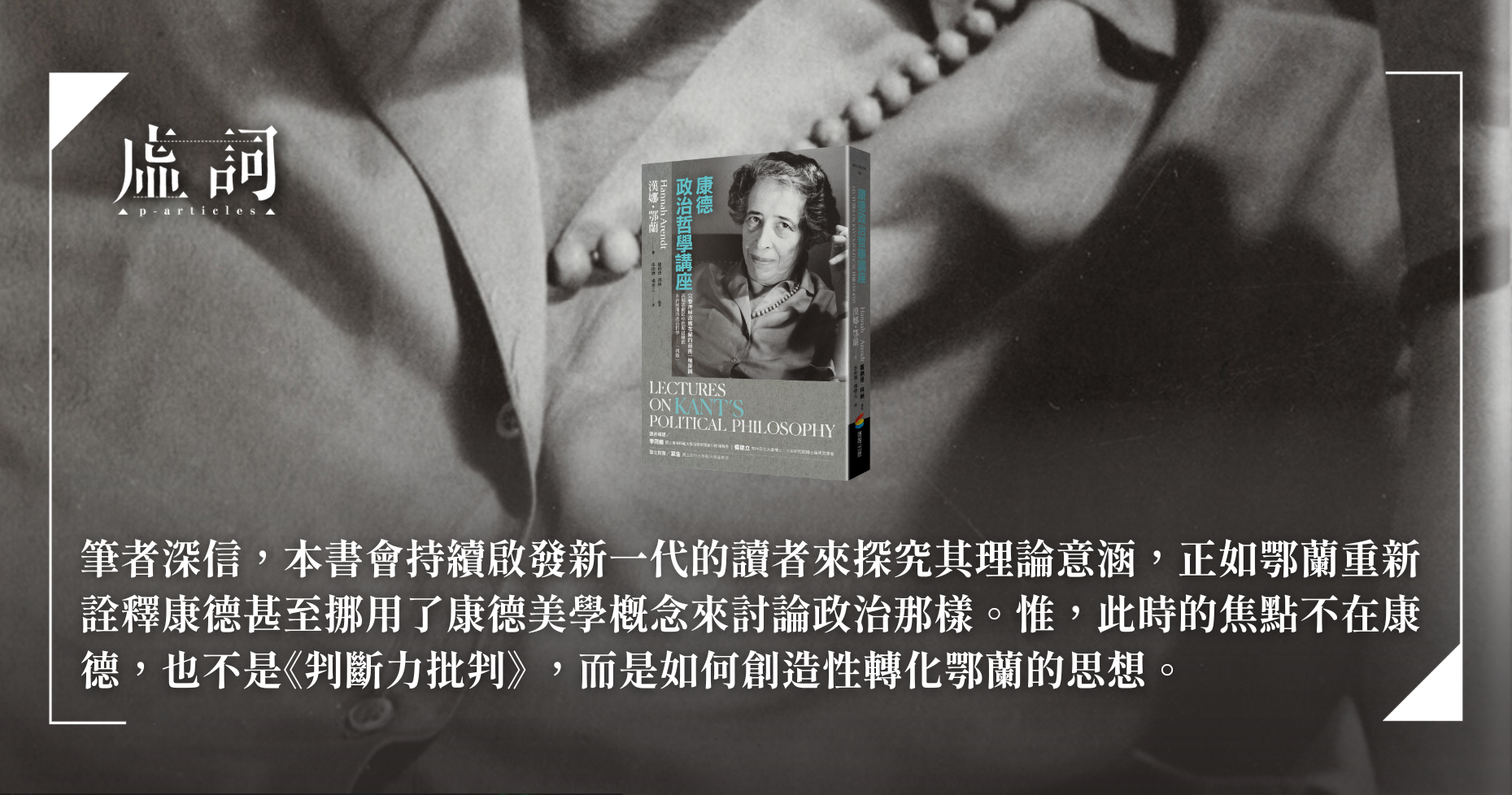其他 | by 葉浩 | 2025-02-17
本書始於《心智生命》下卷的附錄。鄂蘭在完成以「思考」(thinking)為主題的上卷之後,計畫於下卷處理「意志」(willing)和「判斷」(judging)這兩種心智能力,但最後決定讓後者單獨成冊,惟她在尚未進入正文之前即心臟病發離世,僅留下了兩段引文作為開端。因為鄂蘭此前曾在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開過一門「康德政治哲學」課程且聚焦於判斷,該書編輯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擷取了該課程的部分講稿作為附錄,讓不熟悉鄂蘭在其他著作如何談論判斷的讀者能對她可能如何撰寫該議題有初步的概念。《康德政治哲學講座》則是加拿大政治哲學學者羅納德.拜納(Ronald Beiner)在力排眾議之下,從鄂蘭的講稿及學生課堂筆記所編輯而成。職是之故,這並非一本論證嚴謹的著作,而是一份頗能反映鄂蘭授課時偶有頓挫又靈光乍現的講稿。 (閱讀更多)
從星盤讀陳秀喜 射手座》多情的一隅侘寂:恆星的合相
其他 | by 曾彥晏 | 2025-02-17
歌曲〈美麗島〉誕生於70年代,當時飄搖於國際局勢的島嶼臺灣,人們深陷自我身世的思辨之海。這首由梁景峰改編陳秀喜詩作填詞、李雙澤譜曲的歌謠,於意外身亡的李雙澤喪禮首次登場,由楊祖珺演唱,雖旋即被列為禁歌,依然成為主張「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名曲之一。〈美麗島〉的創作者,世人大多將目光聚焦於驟然消逝的民歌新星李雙澤,至於同樣列名其上、寫出原作〈臺灣〉的陳秀喜,我們可能聽聞她是位詩人,但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寫了哪些作品?這次我們一起來讀詩,聽聽陳秀喜的星盤故事吧。 (閱讀更多)
從姚海軍被查回顧成都「雨果獎」亂象, 兼及新一代科幻寫作者的方向(下)
其他 | by 楊在 | 2025-01-24
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的雨果獎從提名階段開始就陷入到了幾乎在國際範圍內引起軒然大波的DQ爭議中。 (閱讀更多)
從姚海軍被查回顧成都「雨果獎」亂象, 兼及新一代科幻寫作者的方向(上)
其他 | by 楊在 | 2025-01-24
姚海軍,對於香港讀者來說可能是個較為陌生的名字,即使是香港的科幻迷也未必例外。然而對於內地科幻迷來講,這卻是個如雷貫耳的名字。同時,相較於這個名字本身,更讓人熟悉且津津樂道的無疑是他作為《三體》的編輯這個身份。 了解《三體》的香港讀者都知道,它是亞洲第一部獲得「雨果獎」(Hugo Award)的長篇科幻小說。 (閱讀更多)
以《金閣寺》和《完美物質》論美的追求
其他 | by | 2025-01-09
何為美,美是主觀還是客觀的?美是永恆的還是稍縱即逝的?美是被創造還是被發現的?我們對美一無所知卻都痴迷於它,我們甚至不知爲何要追求它,或許人就是被設計成追求美的存在。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