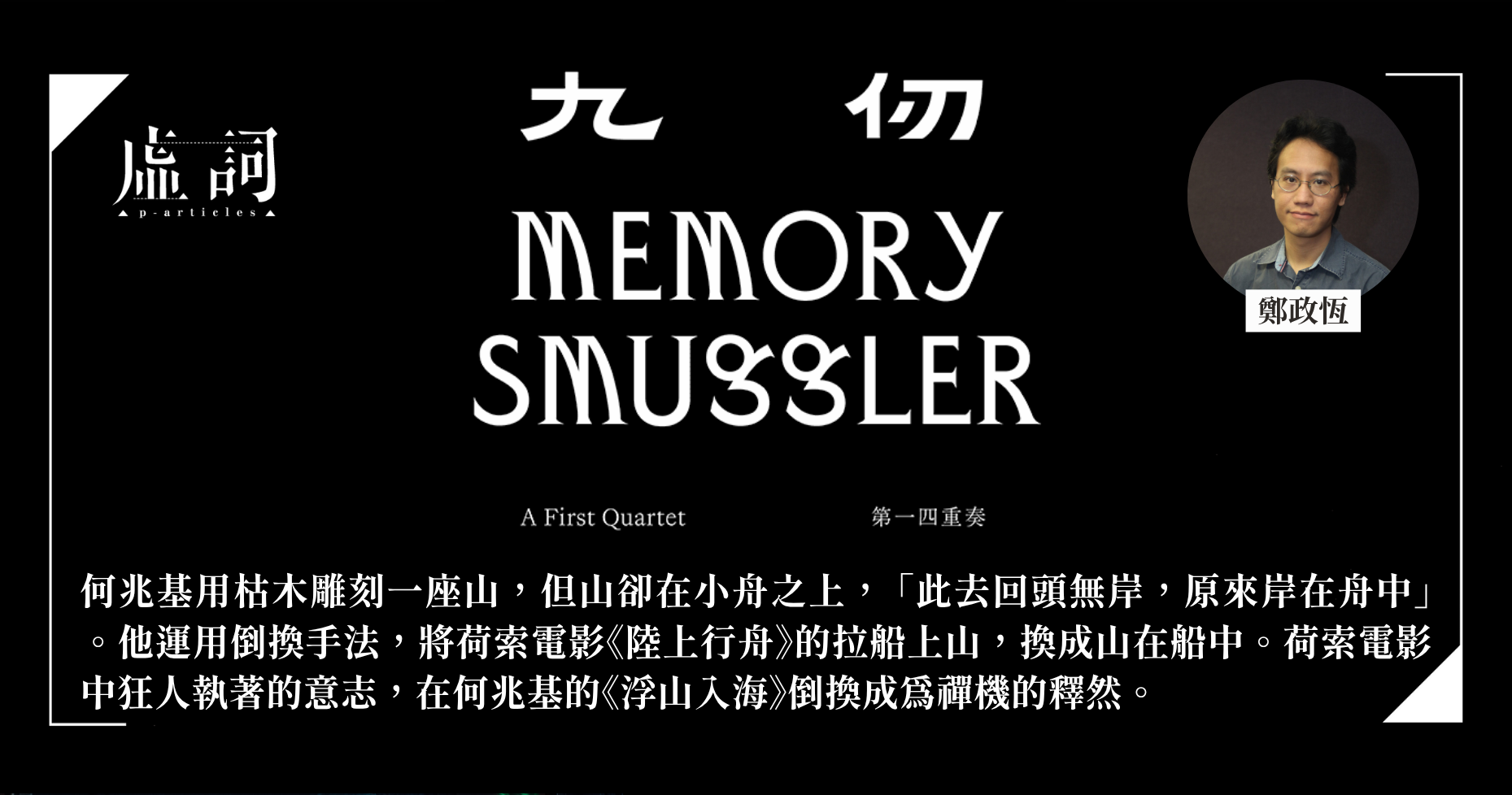鄭政恆傳來「九仞」展覽藝評,「九仞」匯聚朱樂庭、何兆基、劉家俊及李寧四位藝術家的獨特視野。他們以多元的藝術風格,詮釋火炭與山的深層意涵:朱樂庭追溯逝去的痕跡,劉家俊紀錄當下的變遷,李寧勾勒虛幻的未來,何兆基則窮盡山的哲思。鄭政恆指出展覽使用了艾略特《四重奏四首》的詩句巧妙串聯起四位藝術家的作品,從「在我的起點就是我的終點」到「旅人前行」,讓作品得以對話,交織成一場關於火炭與山的四重奏。 (閱讀更多)
舞蹈隨筆|《Jessica And Me》 舞蹈劇場的構作意識
「何謂舞蹈?」這是每個舞蹈家家在創作旅程中必須面對的叩問。林關關近月觀畢舞作節目《Jessica and Me》後傳來觀後感,其為舞者Cristiana Morganti離開Pina Bausch舞蹈劇場後的首部個人作品,於2014年誕生。她透過與虛構「他者」Jessica的對話,反思舞蹈的本質、身體與年齡的交織,以及傳統與創新的拉鋸。作品以幽默與自省交融,挑戰觀眾對舞蹈的固有認知,從技藝展示轉向對「為何而動」的探究。Morganti以強烈的劇場構作意識,檢視自我與藝術形式,敞開疑問與自我懷疑的空間,超越形式限制,觸及藝術與人性的核心。 (閱讀更多)
楊秀卓「病有我」:以情感力量聯繫疾病的隱喻
張煒森傳來楊秀卓個展「病有我」的評論。楊秀卓最近的個展以情緒病為主題,觀察到近年越來越多人有情緒病,因此想透過展覽創作回應。展覽以「病有我」為題,跟我們慣常說「我有病」不一樣,我有病」以我作為主體及疾病的載體,而我的世界只有病,相反,「病有我」則將病換成主體,我只有從屬於疾病之中,我(人類)之於病(不正常的狀態)中,實際是相當脆弱渺小,也去除了病以人作為唯一載體的想像。他提及,展覽以情緒病為題,議題在文化層面中被解讀,也是創作無法迴避的問題。疾病在社會層面中,往往會變成隱喻(metaphor),隱喻是以一種事物喻指另一種事物。這種隱喻與符號,正是楊秀卓創作時直接以感性的表達,讓觀眾不由自主地進入藝術家訂立的異質的、擾亂正常秩序的藝術視角,將情緒病的主題成為大眾的「共同語」,成為一種隱喻,藉此聯繫社會的關係。 (閱讀更多)
緩慢移動著的情感裝置——寫鄧廣燊走近第十年的創作迴旋
藝評 | by 馬琼珠 | 2024-09-19
香港90後藝術家鄧廣燊近日於gdm 爍樂畫廊設個展《砧木》,這亦是他在畫廊的首次個展。藝術家馬琼珠(Ivy)作為他曾經的指導老師,特此撰文仔細回顧他十年來的不同作品,指出他一直為紙品作品做特別設計的框架,框架有時成為畫面的平面(層疊)部份,有時形成窗口中的窗口,她也憶述他如何以鉛芯筆造成她教學生涯裏的小小迷思。說到鉛芯筆,馬琼珠想起比利時畫家Luc Tuymans早期只用一支畫筆畫畫,而這種對工具的選擇、物料運用的步驟和物質性效果的要求,是反映了藝術家的克制,但在鄧廣燊身上,她看見的還有固執和堅定。 (閱讀更多)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副學士畢業展:是,但, yes, but
本月初舉行的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副學士畢業展以「是,但…」為主題,聚合不同同學的想法,結合繪畫、攝影、混合媒介等,透過藝術而彼此提問及對話:「在學習與創作過程中,總會遇上各種雞蛋的畫法,在作出選擇的過程中產生自我懷疑,yes完又but,but完又yes,在橢圓上徘徊。」馮曉彤一邊遊走於展內,觀乎各個作品而發想,一邊思考如何在重複的日常生活裡,提煉美學藝術。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