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暴力,各自論述——評「表演社會︰性別的暴力」
藝評 | by Kobe Ko | 2019-04-14

Julia Philips的作品呈現了對權力關係的思考。 
Oliver Laric的作品Untitled重新繪製了各種會變身的動畫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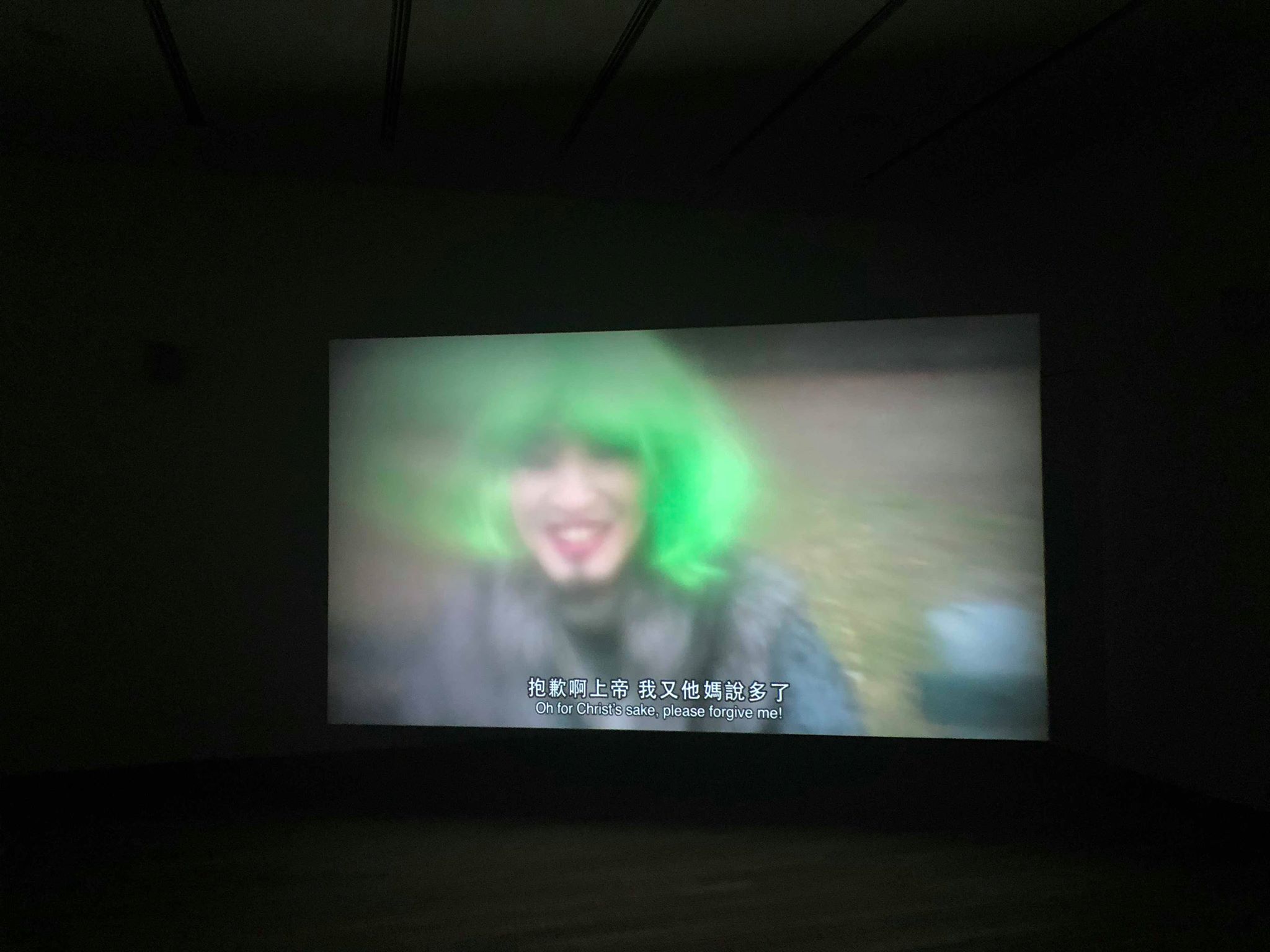
劉野夫的York News暴露了在非男即女的性別框架下,跨性別者或變裝者的邊緣狀況。 
黃炳的《你要熱烈地親親嗲哋》。 
馬秋莎的《定是美人》。 
董金玲的《董金玲2-1》非常有力。
大館當代美術館目前正在展出《表演社會:性別的暴力》,題目對香港人來說聽起來十分聳動,策展人Susanne Pfeffer在概述裡表明這個展覽要探討的,是結構的暴力。談性別的暴力好像離不開女性主義思潮,籠統地說,女性主義至少經歷了三波轉折,同志運動和酷兒理論亦不斷發展,故此,即便是性別論述也能有多種立場和切入點,慶幸的是,從藝術品中不難看出藝術家各自的定位和觀點。
甫入展場就被前方影片的聲音吸引,The Udder的奇幻風格讓我難以移開視線,Marianna
Simnett以後人類甚至是超人類主義的觀點,結合英國的傳說故事(修道院院長為了免於被維京人強暴而切掉了自己的鼻子),撰寫了全新的劇本。後人類主義將人類視為賽伯格(cyborg),即機械與生物的混種,例如動過心臟搭橋手術的人就是混入了機器的生物,甚至可推至現代人的生活已經不能沒有手機等電子產品,手機備忘錄成為了腦容量的延伸,機械已經成為了身體的一部份。當混種身體模糊了人與動物、機器和物件之間的界線時,人類已無法再被稱為「純人類」,因此,後人類更著重不同物種之間的平等,正如影片The Udder中,藝術家透過奶牛工業中的乳牛與社會體制中的少女作對比,探討體制的壓迫與剝削。影片中,媽媽一直告誡女兒「外面很危險」,爸爸一直強調「貞潔」的力量,然而女孩卻問道:「我是否真的太漂亮,不適合到外頭玩耍?」如果不能到外面的原因是太漂亮,那,把鼻子切掉是不是就可以了呢?故事內容與拍攝風格有一絲詭異的氣氛,但內容卻很符合社會現實,當發生性侵案件的時候,常常將錯誤歸咎在被強暴的女孩身上,穿得太少啦、太有性吸引力啦等等,但等一下,難道錯的不是施暴者嗎?為甚麼會變成是受害人的錯了?社會要求女性要保持貞潔,強調貞潔的力量,箝制了身體自主和享受性歡愉的自由,就像牛隻只能被困在牛房,一直為人類提供牛奶一樣。
Marianna Simnett的The Udder的奇幻風格讓人難以移開視線。
旁邊的小房間擺放的都是Julia Philips的作品,Exoticizer(Josephine
Baker's Belt)所批判的是種族的階級,Josephine
Baker是在白人世界炙手可熱的非裔女明星,她之所以大紅大紫,是由於白人對異國風情的嚮往,然而,同為非裔的藝術家無法忽視自身的種族歷史,認為消費黑人價值是一種異化。Position解作姿勢,亦可理解為位置,Positioner展示的是一個提供口交的人和另一個正在享受服務的人,標示了性交過程中的權力位置。而這份作品另一個有趣的地方在於,藝術家並未明確指出提供和接受服務的人是甚麼性別,這點還有待觀眾去想像。而Intruder和Expanded VIII都在指控強暴及強暴文化,不禁令人聯想到軍妓、雛妓等議題,強制性交的不安及恐怖。即便幾件作品所指涉的內容並不相同,卻可看出藝術家對權力關係非常敏銳,不論是種族上或性別上,都提出了強而有力的批判,卻不局限在「男性一定是加害者,女性一定是受害者」的狹隘說法中。
繼續往前,是劉野夫的York News,藝術家化身扮裝皇后,坐在公園長椅上冷眼看待跑步的途人,旁白的女聲用粗鄙藐視的態度控訴著上流社會的假惺惺,拆穿華麗表象下的醜惡慾望,非常直接地對後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提出控訴。影片後半段剪接了McDonalds、M&M's、Pepsi等巨頭的商標、性愛派對、藏人自焚、恐怖襲擊、馬戲團動物噬咬人類等畫面,揭示了現今恐怖主義與美國帝國主義的因果關係,在影片的最後還配上鐵達尼號的音樂作結,彷彿在戲謔人們依舊活在資本主義的虛幻美夢當中。這份作品以酷兒的視野出發,不但宏觀地分析了後資本主義的結構暴力,亦暴露了在非男即女的性別框架下,跨性別者或變裝者的邊緣狀況。
馬秋莎的風格非常鮮明,兩份作品的表現方式就是簡單、直接、粗暴。《定是美人》透過直接食用護膚品這種看似荒謬的行為,來批判社會對「美」的單一標準和要求。《從平淵里4號到天橋北里4號》中,藝術家以平穩的語氣述說著自己的成長經歷,父母如何用心栽培自己,但父母投放在自己身上的期望亦為她帶來巨大的壓力。她的自白在筆者聽來並不陌生,簡直是香港學童的日常寫照,而最震撼的是,她平靜地把自白講完,緩緩地從口中取出一張刀片,接著,出現「獻給我最敬愛的爸爸和媽媽」的字幕,看完之後用了好些時間心情才能平伏。為了讓子女成為一個「優秀的人」,為了向上流動,父母在子女身上施加了太多壓力,甚至把孩子迫上絕路。然而,這些家庭結構中的暴力,或社會結構中難以言喻的制度暴力並不容易察覺,孩子很容易被歸咎成抗逆能力低,被批評為「廢青」、「草莓族」等等,馬秋莎透過自殘的方式,直接地將暴力具象化,是擺在枱面上、活生生的、無法視而不見的控訴。
馬秋莎的《從平淵里4號到天橋北里4號》直接地將暴力具象化。
同樣都是談母職(motherhood)、身體議題,董金玲的一張照片《董金玲2-1》就已經非常有力量,因為選擇把一邊的乳房留給自己,只用另一邊的乳房餵哺小孩,所以導致兩邊的乳房大小明顯地不同,藝術家直接用身體和自身作為母親的經驗,直接作出身體自主的實踐。相對地,Raphaela Vogel的Uterusland則顯得大而無當,藝術家意圖論述的議題與其表達手法之間的拿捏略嫌未夠精準。
而在黃炳的《你要熱烈地親親嗲哋》中,那段父子關係更多的是暗喻中港關係,甚至多於場刊中所寫的父權與男子氣概。黃炳的作品一貫都會出現各種性器官,但畫面上出現性器官甚至性交場面,述說的也不一定是性別議題。雖然作為香港人,非常樂見這個展覽有本地藝術家的參與,但在藝術家的選擇上,令人禁不住懷疑策展人是否對香港藝術家的認知並不夠深入,才會選出一份不太切題的作品。
這次展覽,不少作品都令我留下深刻印象,Oliver Laric的作品Untitled重新繪製了各種會變身的動畫角色,例如阿基拉、狼的孩子雨和雪,不斷的變身模糊了男與女、人與獸之間的界線。看得出是策展人的心思,刻意把這份作品放在最後,彷彿在觀賞完十多份信息量很大的作品後,為觀眾打開二元對立以外的觀看和閱讀方式。如前所述,性別論述的分野既廣且多,或許不是每件作品都值得加許,但就整體來說,能在香港看到一個認真探討性別議題的藝術展實在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