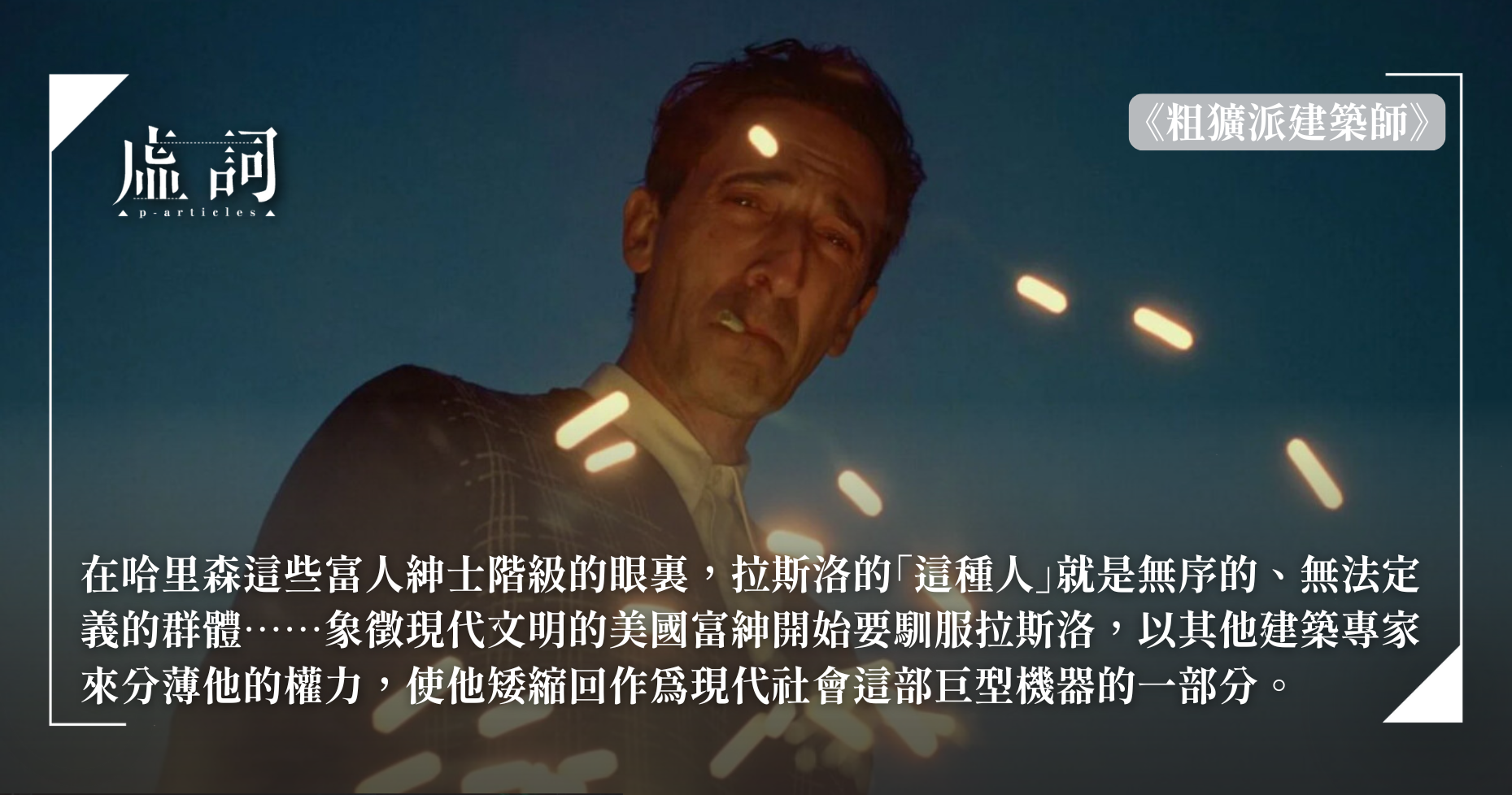《粗獷派建築師》:由斷裂的敘事結構到現代性與大屠殺
影評 | by 姚金佑 | 2025-04-01
在2025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安德林·布洛迪(Adrian Brody)憑《粗獷派建築師》再度獲得最佳男主角獎,無疑使香港觀衆極期待3月6號上映的這部佳作,在戲院裏一睹影帝的演技。該電影分爲三個章節:「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美學的堅實核心」(The Hardcore of Beauty)以及「謝幕的尾聲」(Epilogue)。觀看過後的觀衆,不知會否與筆者同樣感受到第二章與第三章之間的滑坡,以至電影的結束略為突兀。
斷裂的敘事結構?
第二章有別於交代建築師拉斯洛到美國後由一無所有到獲得賞析的第一章,它是表現拉斯洛對建築美學的執著、過程中經受的創傷與陰影,而第二章的尾聲,拉斯洛的妻子得知丈夫被他的富豪雇主哈里森性侵後,來到正進行晚宴的哈里森家宅討理,在那之後緊接的是哈里森當晚的失蹤,然後就是第三章的展開——老態扶輪的拉斯洛出席「建築雙年展」,他過去多年傑出的建築作品(包括為哈里森所建造的范布倫中心)受表揚和肯定。此時他的妻子已逝,如此畫面想必使人感到滄海桑田;可在這滄海桑田之中,電影沒有交代在那不歡而散的夜晚以後,拉斯洛是否繼續為哈里森完成那些建築,以及往後的發展,次章章末出現的夜晚引起懸疑似的漣漪,電影卻在第三章的一番致辭後便戛然而止,充其量再度重現電影伊始拉斯洛的外甥女索菲亞被盤問的畫面,作爲呼應。
歷史傷痛的輪回
起初筆者看畢以後,也感到茫然;但後面想到如此的結構安排,其實也有它的道理所在——歷史傷痛的輪回。第二章與第三章之間的滑坡,這樣的突兀,事實上在電影之初早已出現,只是我們太熟悉,太熟悉納粹德國、集中營的那段黑暗歷史,於是,儘管電影以拉斯洛移民到美國為展開,並無展現納粹德國的殘酷,作爲觀衆的我們也會預設並腦補。出於這種熟悉和預設,我們反而不會對電影一來就要我們理解拉斯洛的那種離散的痛苦感到突兀。
我們不但自以爲自然地理解了拉斯洛的那種痛苦,而且會充滿期待地認爲他即將在異鄉以他的天才大展拳脚,追逐他的美國夢。這一切看起來早已遠離了歷史的傷痛,而迎來了和平與文明的現代社。然而,故事的發展,仿佛將他抛往另一種的歷史傷痛。在那裏,他的代名詞是「你們這種人」,他背負這樣的稱呼在種族、異教這些標籤之間掙扎和生存,當他為理想而偏執,妻子不理解他時,他大聲疾呼是「這裏的人」不歡迎他們,乃至於哈里森在夜裏趁他醉時強暴他,以示主導權從來不在他「這種人」身上。非常諷刺的是,當時美國對猶太人與移民群體的這種區隔與歧視,與納粹德國又有多大的差別?更諷刺的是,拉斯洛至少沒有在集中營裏受到過強暴。
儘管如此,他依然要繼續為哈里森完成那座范布倫中心(這在建築雙年展中可印證),這一切使得他妻子那晚上與哈里森家人的對質,顯得像宴會裏發生的小衝撞,過後宴會依然如故,這個唯利是圖的社會依然紛喧如故。這些是第二章滑落到第三章之間沒有交代的,但是,這也吻合了第一章的起首,電影沒有交代拉斯洛經受了何種殘酷,一下就展現他與妻甥天各一方的無盡孤獨,以及受盡異鄉當地人的另類目光,而這些畫面,與第三章他突然而現的風燭殘年,以及不在人間的愛妻,兩種痛又有甚麼差別?無論納粹德國抑或移民美國,都是歷史傷痛的輪回。電影中的滑坡,與其説是突兀,不如說是一記耳光,是當我們以爲脫離歷史傷痛時,迎面而來的一記耳光。
納粹大屠殺與美國社會的現代性
進一步來説,與這樣獨特的結構相應的,是背後帶出對現代性的批判。正因爲歷史傷痛既發生在納粹德國之下,也發生在美國社會裏,於是,它所指向的,是一種超越國界的現代性,而這是著名的英國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所警惕的現代性。他曾寫過一本名為《現代性與大屠殺》的著作談論大屠殺不是反猶主義的結果,也不是極端的社會現象;相反,它是現代文明社會裏的現代性的體現——現代性的雄心是追求美麗、潔净與秩序,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設法消滅醜陋、骯髒與無序(例如無法定義的猶太人群體),而現代社會的官僚體系、專業分工與理性效率,便為大屠殺的操作程序提供了無盡的便利。大屠殺的誕生,未必僅僅是希特勒的作品,更多可能是一個現代社會具備了適當的條件、應運而生。
電影中,在哈里森這些富人紳士階級的眼裏,拉斯洛的「這種人」就是無序的、無法定義的群體,如同他們以爲「這種人」就只有猶太人(但其實還包括黑人或其他種族的移民群體)。本來渾身骯髒的地盤工人拉斯洛之所以避免「消滅」,能躋身哈里森的富人社交圈,是因爲他的才華,而不是出於甚麼平等。這些富人階級儼然形成一種秩序,而這一切的建築計劃,指向的是對哈里森母親的紀念、新教以及費城,而不是拉斯洛的美學理念、猶太教和移民群體。
可是,拉斯洛就是想締造出人與人之間沒有阻隔、交流融洽的空間,那是屬於移民群體乃至不同種族的,具開放性的,一如戰後的粗獷主義有別於以前的包浩斯風格,是更爲沉重而狂野,材料外露,不加修飾,極具原始感和重量感。在這些西裝革履、象徵現代文明的美國富紳眼裏,那無疑是無序無以歸納的一種存在,也是他們不習慣且難以接受的一種美學。於是,這群現代性的化身,便開始要馴服拉斯洛,以其他建築專家來分薄他的權力,使他矮縮回作爲現代社會這部巨型機器的一部分,一旦工程出現事故需要終止,他也必須服從哈里森的決定,乃至後來被強暴,都是一再提醒他要服從這現代性的秩序。
結語
當電影的序幕掀開,拉斯洛的妻子伊莎白曾在寄給他的信中引述歌德的一句話:「自以爲自由的人,比任何奴役還不自由」。這句話固然也是整個故事的伏筆——爲了躲避納粹大屠殺的拉斯洛移民到自由的美國,卻困入了另一種牢籠。他在牢籠裏獲得一次比一次更多的自由,使觀衆仿佛也與他一同忘了納粹統治下的奴役是長甚麽樣。而電影的第二章到第三章的滑落,給了觀衆一記耳光,看著功成名就卻孤命若懸的拉斯洛,不禁使人想起他妻子在他因建築計劃而歇斯底裏時問過的一句話:「可憐的拉斯洛,他們究竟在你身上奪去了甚麼?」納粹的大屠殺奪取了無數人的性命,堂皇得體的現代社會,又奪取了我們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