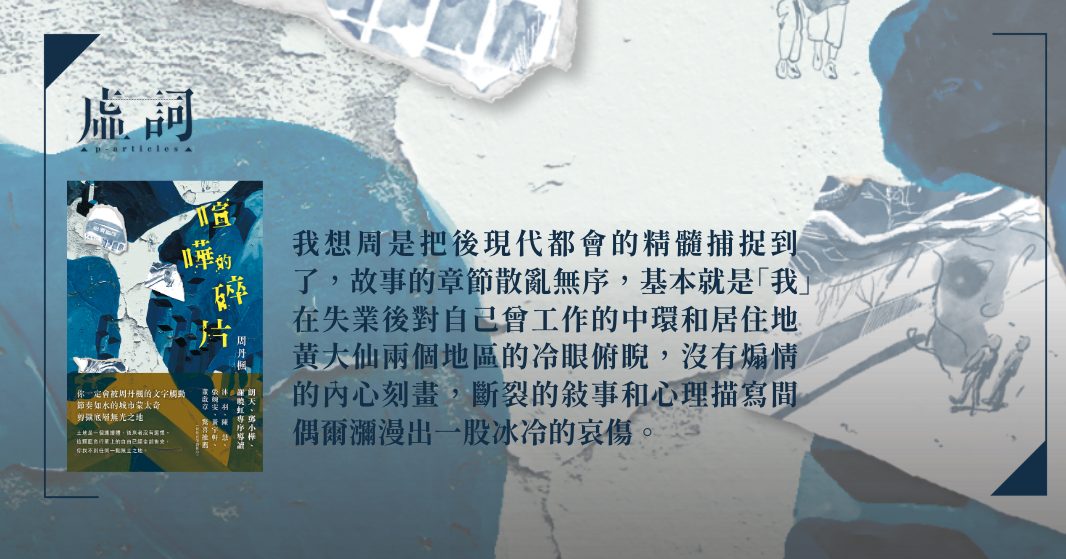無業卡夫卡:《喧嘩的碎片》中的自chur文化和過剩現象
書評 | by 鄧皓天 | 2024-04-30
老實說,我讀完《喧嘩的碎片》(下稱《喧》)後,腦海中不禁把周丹楓和卡夫卡的樣貌自然聯繫起來。周描寫的雖然是21世紀的香港,故事裡無處不在的疏離感和陌異化的都市輪廓只讓我想到了《城堡》裡的K穿梭過的一條條蜿蜒幽道,不寒而慄。我想周是把後現代都會的精髓捕捉到了,故事的章節散亂無序,基本就是「我」在失業後對自己曾工作的中環和居住地黃大仙兩個地區的冷眼俯睨,沒有煽情的內心刻畫,斷裂的敘事和心理描寫間偶爾瀰漫出一股冰冷的哀傷,在營營役役宛如暗流般流動的都會眾生相中,周的筆觸點到即止,勾畫出一張張身分標籤各異的無臉面孔。在《喧》的世界裡,人們似乎只是一件件被粘上身分標籤的商品,在市場的無形巨手的操控下遊走於貧賤或高貴之間,唯一雷同的是那張面孔後幽邃無明的空洞心靈。
《喧》的世界主要分為黃大仙和中環兩區,前者聚集著的是遭唾棄的社會草根和形形色色的奇人異士(例如白卡),後者則是精英雲集人比天上星星還閃亮的香港地標。周卻在故事開首把兩者的共同點濃萃到一起:
我發覺這些精英跟我的母親一樣,雙眼永遠只盯著某個前方,對視線之外的事物置若罔聞,彷彿從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們的身體就受命於一條偉大的航道,而航行者,必然忘記內在的巨大轟鳴。
在這裡,精英和做校工的母親似乎沒太大分別,大家都是被資本主義的宏大敘事逼著前進的貨物,每天朝著俗世的「成功人生」邁進腳步。這幅panorama讓我想到韓炳哲的《倦怠社會》(Burnout Society,我偏好更貼地的叫「自chur文化」),韓指出當代社會的高度資本化和自由化的經濟政策讓人們自覺信奉「勞者多得」的說法,而人們的成就感和競爭力也從物理層面轉移至精神層面,轉而以「精神最優化」(mental optimization)的生活方式鞭策自己。換言之,當人們發現政府並不過多干預經濟時,你的成就和收入完全取決於自身努力與否。而抱著「敢搏就會贏」的心態,人們會自然而然地chur爆自己去達成不同成就,把無止境的工作和拼搏目標填滿日常生活,最終弄得心力交瘁,成了「倦怠社會」的一員。
故事中,「我」和同事@Jackyontheride吹噓自己中學時已開始研究股市知識,@Jackyontheride也很自豪地分享他在差不多時期用三個月把一百萬翻倍的事蹟。先不理情節是否屬實(現實往往意想不到),但兩個中學生在課餘時間炒股在香港人眼裡似乎是件值得褒獎的行為。就像中學的「我」看到電視上的大人物犯了錯,和母親討論起「公義」時,母親只會冷言回道:「這個世界從來就唔公平,你想點?」母親和故事裡大部分的角色似乎都未曾思考生活和人的本質,而是麻木地把不同目標、成就和工作塞進本應悠閒的日常,填飽、填吐「人」這個載體。要不是「我」失業後時間充裕,恐怕「我」也不會有空去反思這一切光鮮亮麗背後無止境的自chur是否正常。
自chur文化最致命的一點,在於這種成就型社會(achievement society)從不以壓榨的方式控制人們,而是透過「你值得更好」、「探索自我」、「激發潛能」、「多勞多得」等潛移默化誘引出生物本能的鬥心。在這種良性競爭成就感的大環境下,「我」為了跟上同事的腳步和富二代兼KOL的@FoodXhunt不斷嘗遍城市各處的米芝蓮餐廳,期盼透過光顧米芝蓮餐廳的行為在同事間營造出「中環菁英」的對等形象,而@FoodXhunt也不會放過把每間知名餐廳打卡post上Instagram的機會。這也是成就型社會中很有趣的一點,人們只會把正面成功的一面對外展示,而悲觀頹廢的另一面則藏得愈深愈好。如同@Jackyontheride那雙總是充滿自信如櫥櫃中的鑽石閃爍的雙瞳,正向價值觀要不是成了人們貼在身上的標籤,就化為心靈雞湯或成功故事成了茶餘飯後向人們推廣自己的談資。
那這樣的人還是人嗎?抑或只是一件件自我經營的商品?這就不得不提起居伊・德波(Guy Debord)著名的理論「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在高速資本化的時代巨輪中,所有事物皆可商品化已成了人們致富的潛規則。商人絞盡腦汁設計出奪人眼目的商品,而人們都會被它們光鮮亮麗的表面吸引,慢慢遺忘了這些商品原本的被製造出來的意義。當人們在消費式社會的薰陶下,也沒有考慮自己的需求,便下意識地把身體當成衣褂盡可能地掛上這些商品,最終理所當然地失去自我,迷失在絢麗奪目的表意中,自願成為了被商品奴役的囚犯。毋容置疑《喧》正是把如此的社會現象描得繪聲繪色,無論是「我」和同事們正能量的talk shit還是母親呢喃如囈語的「成功人士奮鬥記」,其實都是掛在我們身上,用以展示自身價值的表證,本質上和「我」路過看見樂富地鐵站時看見的箍牙、美容、整容廣告無差,只是些讓我們外表變得完美的策略,亦呼應了基斯頓比爾在《美國精神病人》中的一句台詞:「But inside doesn’t matter」。
《喧》對超現代化(supermodernity)的宏大敘事不止於精妙的人物側面描寫,更在於對過剩現象和個性扁癟的商業大廈的紀錄。超現代化本質上指的是「過剩」的都市現象,而馬克·歐傑(Marc Augé)在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中提出了三個方面的「過剩」現象,其中兩個分別是:1)事件過剩(factual overabundance)、2)空間過剩(spatial overabundance)。事件過剩指的是資訊爆炸的現實中目不暇給的新聞和events,常見例子就是社交軟件上疲勞轟炸我們的reels和廣告;而空間過剩則是人們為了節省時間而壓縮空間的種種行徑,例如愈來愈短的通勤時間抑或讓我們足不出戶亦可知天下事的互聯網。在《喧》中,則有一段關於過剩現象的精萃描寫:
我MSN的簽名一直是「Per aspera ad astra」——「循此苦旅,以達星辰」。但,城市燈火已經淹沒了星光。我們躲進用石與鋼堆砌在的牆,用貨架上窮盡一生都吃不完的薯片,用細小螢幕裡永遠滑不完的reels,來填飽眼皮和肚子。在熱量過剩的當下,我們的身體變得愈來愈沉重,無日無之的「發炎」並不能帶我們起飛,而是像承載「Per aspera ad astra」這一句的拉丁語一樣。將我們變成一具屍體。
在「我」的想像中,我們總有一天會足不出戶以便利的科技取締眼睛去見證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吃著原先為了方便才吃的垃圾食物,把注意力壓縮到只有十秒的reels裡,一段接一段餵食自己的大腦直到作嘔。而這樣充斥著各式各樣「過剩」的未來,不僅沒讓人類更加集中於追尋內在價值,反而讓我們淪為一具具行屍走肉的屍體。
而歐傑也進而指出「過剩」現象一般與非場所(non-place)掛鉤。在歐傑「場所」與「非場所」的二分法中,「場所」意指有個性、歷史價值、集體回憶,或有益於人文交流的地方,如歷史遺跡或文創景點;而「非場所」則指個性乾癟,具實際功能性,只供人類短暫停留的單一化建築,如機場或商業大廈。弔詭的是,《喧》中對於香港的城市刻畫幾乎只充斥著「非場所」,在「我」宛如鬼魅般地遁行於十八區的異聞錄裡,無論是位於秀茂坪宛如墓碑的方形公屋群,還是如獵刀般冷光閃爍的中銀大廈,都只是一座座複製貼上,除了實用性外毫無生命力的建築。而進出或居住其中的人們彷彿也被同化似抹去面孔,只剩下一個@tag或易記的外號,蒙太奇式潺潺流過「我」的身旁。隨著《喧》的故事進展,周的描寫到了後半部已然魔幻,宛如超現實電影的錯置效果,巨大如囚牢般的都市彷彿擁有了生命,無聲中不斷吞噬無臉孔的人們,而居住其中的我們,只能像營養物般排隊被消化。
幸好,「我」被裁員了,成為「正常人」眼中的異類,才能像《變形記》的薩姆莎一樣檢視自我。不過不同於最後乾枯死去的巨蟲,「我」在他人眼光的審判中透過回顧記憶尋找過去在成長中賦予自己個性的點點滴滴。縱使那都是些不甚愉悅的回憶,父親負債,母親離婚,校園霸凌,但「我」似乎意識到那顆早已風化成石頭的心正蠢蠢欲動。當「我」站在富豪東方酒店旁那條斷裂的廢棄大橋上,看著下方狂潮一般的車流時,終於意識到悲傷總比麻木好。儘管那都是些不堪入目的過去,至少證明了自己的過去並不空白,而是由一幕幕微小而零碎的片段拼湊而成。末尾襲港的颱風「山竹」把城市颳得七零八落,卻也把淹淹塵世洗了個乾淨。「我」忽然湧現出探索颱風後的城市的好奇心。由於植樹時樹苗紛紛會安置在「盒子」裡,它們的根無法自然生長,無法抓實泥土,因此家附近的大樹紛紛被連根拔起,只有一旁的小樹苗依然安然無恙。「我」忽然意識到這個城市也是一片很大的森林,「根」卻很淺。不過哪又如何?大樹倒了,小樹依舊茁壯成長,生生不息。
或許這才是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