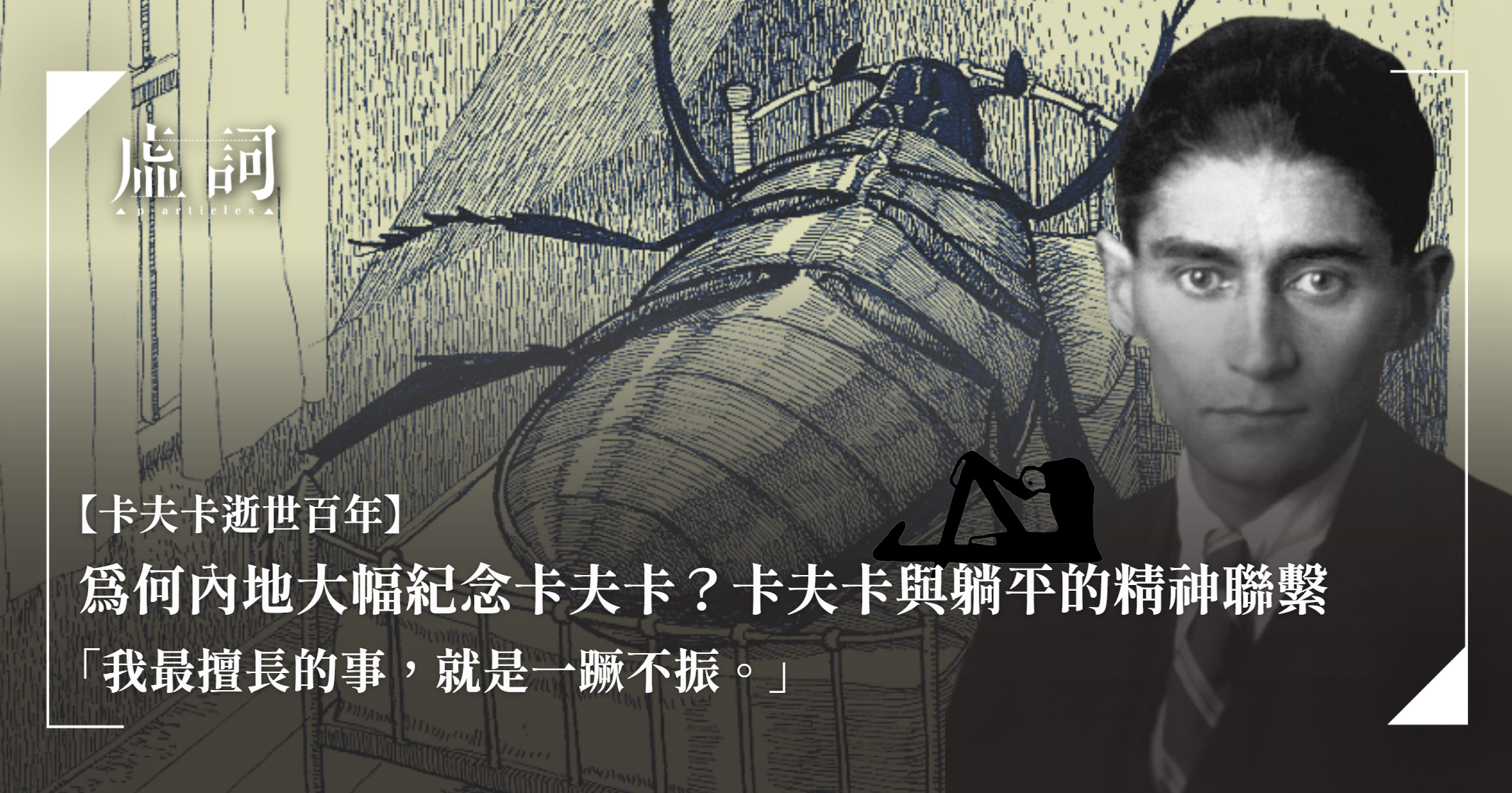【卡夫卡逝世百年】為何內地大幅紀念卡夫卡?卡夫卡與躺平的精神聯繫「我最擅長的事,就是一蹶不振。」
現象 | by 默言 | 2024-05-26
西方的現代主義小說先驅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轉眼已逝世百年,幸得他的好友布羅德 (Max Brod) 沒有如實遵從他的遺囑,把所有作品全數焚毀,我們才沒有錯過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這位「弱的天才」去世後才受到世人矚目,相信他本人也沒料到自己的頹廢美影響至遙遠的中國,一句「我無法朝著未來前進, 卻能面對未來,裹足不前。我最擅長的事,就是一蹶不振」荼毒不少青年,成為「躺平主義」的楷模。
內地大幅紀念卡夫卡
卡夫卡逝世百年,中國內地可謂隆重其事大幅紀念,彷彿到處都能看見卡夫卡的慶典,卡夫卡的名字甚至在新生代的社交平台流行起來,《金融時報》刊出的文章《我們對卡夫卡持久的迷戀》,就提到現在TikTok上的 #kafka標籤的瀏覽量已超過1.4億。
從策劃活動,到出版書籍,說明了中國讀者對卡夫卡的擁戴。據《搜狐新聞》,5月21日清照詩歌藝術節聯合奧地利駐華大使館文化處,於山東的明水古城,舉辦了「卡夫卡逝世100週年紀念活動」,活動以卡夫卡的文學語言為核心,邀請中國當代藝術家董大為以《變形記》為題設視覺藝術展,將書中的文字轉換成視覺符號,亦邀請奧地利藝術組合「卡夫卡之舞」,以聲音和身體的視聽創作,來詮釋卡夫卡的文學語言。
「春潮」工作室以「抵抗遺忘」為題,舉辦持續一百天的紀念展覽,透過卡夫卡的手稿、書信和照片等等,深入還原他的生活場景和創作環境,展出《變形記》、《審判》、《卡夫卡的卡夫卡》等不同譯本,並邀請到藝術家根據卡夫卡的作品創作。
內地出版界亦相繼出版卡夫卡的研究書籍,如浙江傳媒學院出版中心推出葉哲遠的《一本書讀懂弗蘭茨卡夫卡》,在選編、摘錄文學作品的同時,也選取名家、專家對於作品的解讀與詮釋;中信出版社展示卡夫卡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畫家身分,推出《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畫作手稿》,書中包含迄今最完整,且在中文世界首次獨立出版的卡夫卡畫作手稿,又將於7月推出由艾莉·史密斯(Ali Smith)、李翊雲、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海倫.奧耶米(Helen Oyeyemi)等英美作家致敬卡夫卡的短篇小說集《一隻籠子,在尋找一隻鳥》。
卡夫卡式新文化運動?
內地大幅紀念卡夫卡,除了出於其卓越的文學成就,或是因為卡夫卡的精神面貌暗地裡與中國現代青年的躺平現象有所契合。據《美國之音》報導,三年前「躺平主義」在中國興起,主要是因為八九十後的青年一代面臨巨大的生活壓力和社會不公,高房價、就業壓力、職場「996」工作制(每天工作12小時,每週工作6天)等問題,使得許多年輕人感到無力改變現狀,而中國輿論也在誘導年輕人多消費、多享樂,他們便選擇「躺平」作為一種自我保護和消極反抗,追求低欲望的生活,對抗社會「內捲化」的方式繼而被稱之為「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中國一百年之後的「新青年新文化運動」。
一百年前,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一百年後,新文化運動是卡夫卡式的,中國的現代青年不再信奉魯迅的戰鬥性,在網路發文抱怨工作難找,薪資下降,高學歷被迫低就,連孔乙己也被重新解讀,發現「年少不懂孔乙己,讀懂已是書中人。」
面對去年興起的「孔乙己文學」,據《中央社》報導,官媒央視網和共青團中央發表評論,指稱青年不願意找工作,並呼籲全社會應該協同發力,協助他們走出困境,卻引來大量留言怒轟官媒根本搞不清「脫不下的孔乙己長衫」是甚麼,強調是就業形勢太差,沒有好的工作。
在這情況下,難道中國青年還會在本來沒有路的地上,走出新的道路嗎?面對世上崎嶇的道路,他們並非全然逃避現實,他們相信卡夫卡的說法:「我們稱之為路的,其實不過是彷徨」、「一切障礙都能摧毀我。」生來就瘦弱多病,且總對自己的身材表現出困擾的卡夫卡,給人一種矮小、生活不健康甚至頹廢的印象,或許正是中國青年所著迷的地方。
「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人」
卡夫卡與中國的聯繫並沒我們想像般遙遠,他對中國文化深感興趣,並富有研究,又在寫給菲莉絲的情信中設想「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人」,並引用清代詩人袁枚的〈寒夜〉,又曾出版小說集《萬里長城建造時》。
與躺平學最大關聯的是,卡夫卡研讀過老子學說,「我深入地、長時間地然讀過道家學說,只要有譯本,我都看了。耶那的迪得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這方面的所有德文譯本我差不多都有」,這些譯本包括老子的《道德經》《列子》和莊子的《華南經》。卡夫卡曾有一段箴言:「無需走出家門,呆在自己的桌子旁邊仔細聽著吧。甚至不要聽,等著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呆著別動,一個人呆著,世界就會把它自己亮給你看,它不可能不這樣。」這就如老子的「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彷彿卡夫卡早已深悟無為之道。
我們都記得,《變形記》裡孤獨的格里高爾,就是從躺著去理解自身。格里高爾最初對恥辱有著明顯的感知,他會為自己無法工作而感到恥辱,這正是源於社會對他的期望,男性在社會被定型為家庭的經濟支柱,又或可理解成社會對年輕一代的期望。後來隨著家人轉變態度,格里高爾逐漸放棄再做些甚麼,他就順著自己的「本性」,像一隻甲蟲吃東西。
中國青年們發現,卡夫卡早就認清職場與生活的現實。早在1907年,他就給自己訂了一個原則:工作不能與文學有任何關係。於他而言,前者是為了維繫生計,而後者則事關生命的真正尊嚴。卡夫卡一生都在寫作,他曾說:「我們都擁有屬於自己地底世界逃脫出來的方式,我是透過寫作。那是我唯一還能保持前進的方式,而不是透過休息與睡眠。實際上,我是透過寫作來獲得心靈的平靜,而非在寧靜中寫作。」於是,卡夫卡選擇從事保險公司職員,儘管那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痛苦,但他仍舊保持著業餘作家的身份,在職場的疏離感和對生活的無力感之間游移,這與「躺平」世代對「狗屁工作」的抱怨和對生活的無奈有相似之處。
躺平以後,側臥進睡
《遠見雜誌》指出,當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2023年4月至6月的青年失業率超過20%,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新高之後,那些本想以躺平告別煩囂社會的年輕人,發明了一個新名詞——「側臥」。側臥式打工人,介於躺平和奮鬥之間的狀態,對工作對事業,有時想拼卻又沒有鬥志,對事業有野心卻又不想那麼累。從躺平到側臥,反映出當下大陸普遍的社會現象,以及打工一族面對的是愈來愈競爭的職場,無可奈何又無法逃避的工作壓力。
側臥式打工人掀起一種「職場發瘋文學」,隨即風靡中國網絡,「人之初性本善,不想上班怎麼辦」、「月薪一千五,命比咖啡苦」、「上輩子作惡多端,這輩子早起上班」、「上班真的很有意思,有意思到讓你覺得活著沒意思」等,反映了中國青年在職場上的厭倦和無望。而《三聯生活週刊》更發現這種文學,在上個世紀的《變形記》就已問世,當中高壓的工作環境,冷漠的職場關係,失去工作的可能,就如現時的中國青年,被這些社會環境和人際關係壓抑著而異化。卡夫卡曾說過:「一個籠子在尋找一隻鳥。你是做為一個籠子還是一隻鳥,有時決定權並不在你手中」,亦被認為正是書寫了現代人的困境。
生於香港,長於中國的作家王璞稱卡夫卡為「說夢者」,說的是「我們這一代人的集體夢囈」,又或是說了躺平世代、側臥式打工人的夢囈。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則認為卡夫卡是「寓言的創造者」,他筆下的生存困境竟在一個世紀後應驗,當中的無力感、對社會制度的質疑和反抗,與現代中國青年產生共鳴,引起他們反思在龐大社會機器面前的自我價值,證明卡夫卡的作品至今仍深具啟發意義——格里高爾忍受百年孤獨過後,有了許多躺平的同伴。

「負離貼紙」購買連結:https://www.hkliteraturehouse.org/shop/stic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