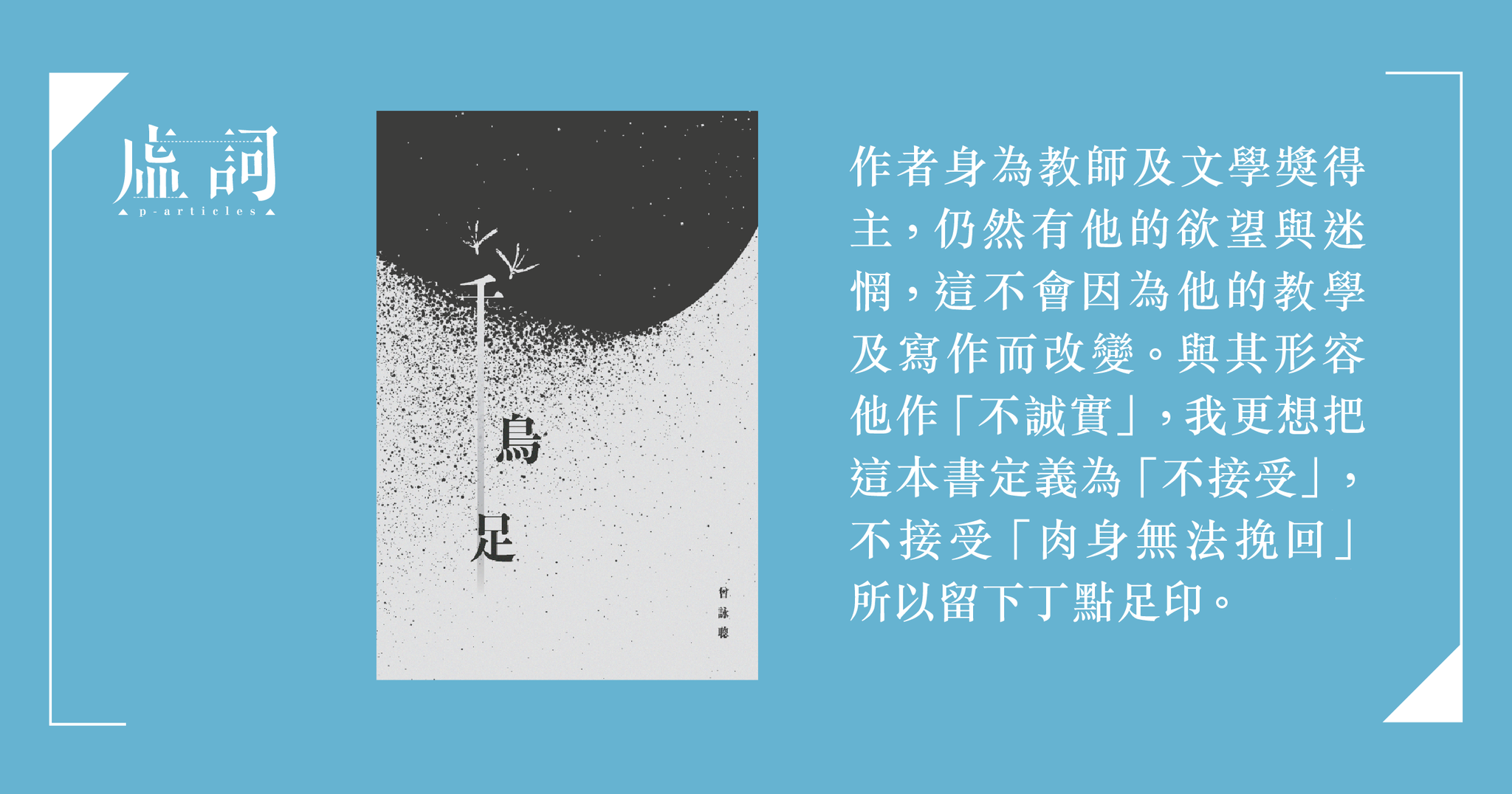碎步與探戈——讀過《千鳥足》
書評 | by 翟彥君 | 2023-02-20
大學時悄悄讀過曾詠聰的blog,頗佩服他的產量,印象中某篇文章寫他在監考時作詩。到我出來教書,朋友都發現我不太發表作品。其實吧,我代課時也喜歡拿紙筆寫詩;乘車時也會寫寫。可是我這人缺根筋(兼且好用紙筆),總丟三落四,只好安慰自己:草稿太垃圾了,遺失是天意。新年假期,我在書房及客廳翻找了一整過下午,把年廿九整理好的電費單又倒出來,生怕錯過了甚麼,直至黑白斑紋的貓從夢中起來抗議,牠瞇起眼似乎鄙視我的堅持。這次我可能傻更更掉了書評的草稿,而寫給未婚夫的詩又剛好夾在一起。生活像我的草稿,忙碌時被冷落,有閑餘打字時才醒覺那些念頭已然消失。我很是滿意書評及那首詩,現在這兩個又該被放棄。
一,先導
如若給中三那班女孩看,寫篇先導或許比書評好。有本筆記難得被我珍而重之,裏面都是我第一年教書的錯事、反思,空白頁還有很多,我把感想寫在上頭,這次定不會不見。
二,末日如斯
中學時流行2012年未日預言,同學討論既然末日還該不該準備DSE。慶幸我現在存活了下來,我考過DSE,並且如今戴著口罩講書。局促的感受是共通的,曾詠聰寫「輸入、登出、連結,這就是我們之問好和道別」,我們的觸碰卡在4G的網絡裏,網課那回,我只能夠讓學生多給我個Emoji,奢求多一點溫度。現在已復課,戴口罩的我會更集中看學生的眼睛,捕捉她們的情緒。中學那會我也喜歡上堂偷喝豆奶,有時嚇得Miss嘩嘩叫,現在我命學生收起飲料,實在是天道輪迴。
「風扇依然不情願地轉動,兒時我會幻想它砸下來割掉師生的腦袋。」我的確也有這種共同想像。溫度上升時,學生要求開風扇。十年前還是現在,男孩還是女孩,每班總有個特別怕冷、怕熱的人,這個人在眾人要求開啟時反對、要求關熄時去啪電制。怕麻煩的我會給自由,學生決定而不用問我,有結論時派個代表示意,我會讓代表出來開、關。發現給些「自由」並無不妥,沒有人情願張牙舞爪。不過,關於風扇,我肯定學生不會有「砸下來割掉腦袋」的幻想,因為吊扇不太流行了,學生更怕中暑、凍僵。教室裏的危險,會不會是集體潛意識?比起吊扇,口罩更讓我窒息,而我盯著那些透明隔板,想著她們的共同想像也會隨年代變更。只有「挫折和苦悶」是不變的。
三,鬥魚
鬥魚小小的、尾巴色彩斑爛,隨時展開的尾巴像一匹空中浮動的白紗,帶銀色反光的魚鱗正是女孩口中重新流行的Y2K風格。這種魚像人,華麗的形象下好勇鬥狠,人類自小已學習互相傷害。幼稚園誰沒搶過玩具呢?小學誰沒向老師打過小報告?學生時期多喜歡說些老師的八卦啊。
文中送鬥魚的人寄望美麗的魚兒伴對方渡過低潮,收到鬥魚的人卻哭笑不得。這種矛盾充斥着成長的各個階段,渴望得到理解、實情難被理解。作者在此篇說出自己的壓力,壓力讓他患上失眠。講台上的成年人不是完美的結晶,他們也有卡關的時候。我和學生聊天時,有些學生會板起面孔,覺得我不甚明白她們的苦楚,笑話我只會趁她們考試的時候去迪士尼。長大後的改變是「有苦自己知」,朋友、伴侶少了共鳴和耐性,多長篇的不適最後迎來像「多喝熱水」這種能醫百病的安慰,誰都捉摸不了對方的痛點。
成年後,世界仍是個大魚缸。我們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緒,回家望望天花板想想自己的帳單。雖然有點慘,實際上生活的恆常是「苦中作樂」。文字濃縮了情感,生活如是前進,我們實際上也不太像鬥魚,想通了,又回到魚群當中,樂意彼此親近。有時我收到隨筆,會發現嘻嘻哈哈的學生們都有顆細膩的心,當脫離文字、回到課上,便又是幼稚的每一個。成人相反,面對自己時,永遠能像一個無助的孩子。
四,千鳥足(ちどりあし)
「千鳥足」是日文,意指醉後腳步搖晃的狀態,我們也是步履蹣跚,迷惘的每一瞬都是醉酒。作者算是吐真言式道出自己的無奈及不愉快(也有悲痛),儘管被評道「不太誠實」,於我也已夠真——教師這一工種是不會下班的,哈哈。誰叫我們長成了這模樣?
書中說連母親也不知道〈回家〉這首詩在說甚麼,我總讀到深深的孤獨。我的那個他是商科生,解不透文字中的深意。此刻想來,寫給他的詩既然讀不懂,掉失了也好。倘若談及自己的陰暗部分,我會說:接受生活不單只有「詩和遠方」。我喜歡文字,他喜歡海和數字。對於他,我也許是個連EXCEL都不太會的呆子。文友曾訝異我沉迷迪士尼,問怎麼現在不太去書店了,彷彿我不能向往成為「公主」、以及我與物欲無關。嘴饞的我還寫過食評,到不同餐廳吃「霸王餐」。大學有段時間投入寫作,那時被「沉鬱」、「叛逆」包裹,有時被同學說有些「不可一世」;與其形容作「不可一世」,我更想將這種狀態定義為「陷入迷惘而對外界置之不理」。曾詠聰在我唸大學時已有名氣,我特意去他的詩會,詩會有圍讀環節,很多同學都交上自己的作品,他說只抽一兩首點評,幸運地,我的作品便是其一。他的點評當時被我置之不理,如今卻常被回憶起。現在的我已漸趨溫馴。
作者身為教師及文學獎得主,仍然有他的欲望與迷惘,這不會因為他的教學及寫作而改變。與其形容他作「不誠實」,我更想把這本書定義為「不接受」,不接受「肉身無法挽回」所以留下丁點足印。
學生總覺得寫作很困難,我常言非常容易,因為學生正值「多事」的年紀,對人、對事物有各樣的聯想,只是不知道如何寫出來。我的工作是引導,我很高興她們喜歡上寫隨筆,興趣變成讓學生發表作品,所以沒關係呀,那些丟失的草稿。學生有自己的人生碎步,不論是快是慢,我希望她們學會書寫。中三班上有幾個女孩常說自己想修文學科,這方面,心裏有少許慚愧,在文學推廣上,我理應做得更好。幸得上司首肯,我邀請曾詠聰到學校談談《千鳥足》,他今年開了文學科,剛好讓那些好奇的孩子看看一位文學老師的樣子。